
李敬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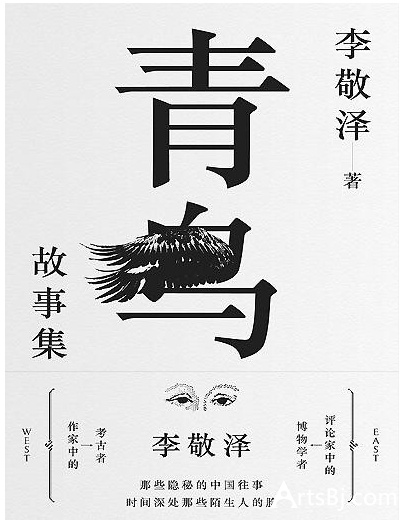
采访者:蒋蓝
被访者:李敬泽
李敬泽在《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跋语里讲到新作《青鸟故事集》的来龙去脉:“感谢布罗代尔。在他的书之后,我写了这本书。1994年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凭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走进住宅,呼吸着15世纪特有的气味,察看餐桌上的面包、米饭,有没有肉?有什么菜?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洋,我们看到500年前的人们在艰难地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布罗代尔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在这无数温暖的细节中暗自运行。但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
李敬泽的这一写作背景,使人不能不想到历史学家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他显然触及到了峡谷的陡岩与一些暗礁,他渴望在文学的视域里,以绝大的勇气与才学,将他心目中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传统与现代化、虚构与非虚构的复杂关系,来一次厘定和呈现。
“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
蒋蓝:你已经出版了二三十部著作,这本由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青鸟故事集》为什么显得特别重要?
李敬泽:我算是鲁迅的信徒。从小读大先生的书长大,我发现他是特立独行的,连书名也是,一字不能易,《呐喊》《彷徨》等等,戛金断玉。即使不断再版,他也不会另取一个书名,对此我一直是谨从的。而且我也学习大先生另外一个德性,那就是新书里不收录别的版本里的文章,货真价实,以示童叟无欺。但是,出版《青鸟故事集》却是一个“例外”。
蒋蓝:此话怎么讲?
李敬泽:在我看来,一本书是否值得再版,要看它的思想、观点是否过时。我至今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没有过时,而且对当下如何思考现实与历史、本土与西方、文学和思想等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何况,《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至今满16年了。当下中国变化之巨大、思想更替之迅猛,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6年回首,我就有一种充分自信:两千年来,国人从未想到用这种言路来演绎历史。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16年弹指而过,你会发现有很多作者也按照这本书的言路在写作历史了。这本书对于我而言,不但是一个具有生命刻痕的纪念,而且是时间对我探索性写作的一个褒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不悔“少作”。
2016年译林出版社找我,决定新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我思考良久同意了。在原稿基础上,我修订了百分之二十的篇幅,主要是去掉了一些抒情过分的段落,另外补充了一些观点和少量新作。
蒋蓝:这就是《青鸟故事集》的由来。这本书在国外有译本吗?
李敬泽:2003年,法国一家出版社决定出法文版。委托给法兰西学院的一位翻译家。不料这位年事已高的翻译家突然病故。出版社又请来一位双语翻译高人,商定一年半交稿。哪知道这位高人“突然失踪”了,全世界都找不到他了。这只能叫“祸不单行”。出版社只得委托第三位翻译家再接再厉。我只能祈祷,事不过三嘛。谢天谢地,这位翻译家终于完成了。这是13年的马拉松啊。看起来“福有双至”,《青鸟故事集》的法文版将与译林出版社的中文版于11月同步上市。呵呵,世界真奇妙。
蒋蓝:《青鸟故事集》的命名,你自然有考虑。
李敬泽:我当了多年编辑,书名命名自有“机巧”。开始本拟使用“飞鸟”,考虑到已经被人糟蹋,白白毁了这个好词,只好另辟途径。李商隐名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我的“青鸟”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意思,反而是大师梅特林克的最著名代表作——六幕梦幻剧《青鸟》,在我的故事集里留下了它巨大的鸟影。
蒋蓝:梅特林克的《青鸟》是欧洲戏剧史上融神奇、梦幻、象征于一炉的杰作。写兄妹迪迪和麦迪去寻找青鸟的故事。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夜宫的五道大门,恐怖的墓地之路,难以置信的青孩子的身世,以及幸福家园的见闻。种种经历都是为了让兄妹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
李敬泽:我在《青鸟故事集》里展示的我进入历史迷宫的历险。我们不应该再采用教科书的态度进入历史,而是自由地探索历史真谛: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记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
“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
蒋蓝:在《沉水、龙涎与玫瑰》一章里,你展示了一种“博物学”式的旺盛趣味,考据了这些事物、植物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引用、考据、想象、思考穿插其间,其碎片拼接之书天衣无缝。尤其是你对玫瑰与蔷薇的考据,引人深思……东方人之于蔷薇,西方人之于玫瑰,各自的文化围绕花朵之杯倾注了完全不同的酒。
李敬泽:这恰恰就是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历史叙事里我最为看重的事物细节和事物在生活方式里的悲欢荣辱,花开花落。钱穆说过,要用“温情与敬意”去诠释历史,我尽力这么做了。有时,“掉书袋”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枯燥、且无节制的引用,而又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蒋蓝:你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
李敬泽:我父母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所以我的童年玩耍的地点,基本上是在一些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十分艰辛,父亲一年也不容易回一次家。我当时就想,历史、考古自然是高大上的,是宏大叙事,与寻常百姓根本没有关系。这种想法伴随自己阅历的增加,我最后彻底否定了这些看法。我从布罗代尔的著作里。看到了西方的平民历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心目中可信的历史。在我看来,记载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远不及一部《红楼梦》伟大。
蒋蓝:你是以平民历史观来演绎、展开你的历史视域。也可以这样说,《青鸟故事集》也是一种文学的“微观史”。
李敬泽:要害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每一代人的境遇、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回望我们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也扩展了对自身、对当下的理解。所以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否则只有一部《二十四史》不就够了?在重写中人们会不断有新的发现,达到对我们民族历史更为真切、更为宽阔的认识。
蒋蓝:我印象里,你至少三次前瞻性地提出观点引起世人关注:一是2000年针对历史的平民史观写作;二是2008年你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力推“非虚构写作”;三是你对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文学性想象的对比。
李敬泽:承蒙夸奖。我曾经说,人类一定是相互想象的,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文学作品。想象会有偏差,但偏差不能阻挡我们的相互想象和交流。比如对郑成功的认识,我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他早期的抗清和后来的收复台湾,其实郑成功的业绩和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郑氏父子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其实在明代禁海之后,民间的海上活动就非常活跃,这种活跃某种程度上是15、16世纪世界贸易发展的结果,所谓“白银时代”,明朝政府不让出去,大量的民间商人出去,在正史叙述中这些人都是“海盗”,都是坏人。但现在看,当时的这些民间海商活动具有长时段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为后来我们的海上疆界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这是被正史遮蔽的大规模的历史活动,从中涌现出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从日本到菲律宾,从东海到南海,我们的先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冒着巨大的压力、风险、困难,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还占了上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真当得起波诡云谲、波澜壮阔。
“我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元典的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不是文体学问题。”
蒋蓝: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由跨文体构成的“超级写作”吗?
李敬泽:从写作方法上我基本认可“超级写作”,但我未必是跨文体。准确说,我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元典的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不是文体学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问题,在《左传》里均可以找到踪迹。那是民族的元典,如此有力,展示出强有力的语言与强有力的精神。可惜的是,春秋时代斩钉截铁的问题,被当代人搞得非常复杂和暧昧。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没有从元典里吸取滋养,它后来因为各种训令形成的价值观就是可疑的。
如果说柏拉图的《会饮篇》展示了人类的基本问题,并且得到了可贵的延续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元典并没有得到一流头脑的诠释,既然如此,弘扬与继承就更无从谈起了。《青鸟故事集》是对异质经验的涉入与旁出,其现实意义可能要高于16年之前。尤其是在一个面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汉唐作为伟大帝国的高标,它如何与西方发生关系?
蒋蓝: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吟唱?
李敬泽:我不大相信口述实录。一个人口才再好,笔头很烂,这两者没有关系。但吟唱不同。走在天地之中,心中有歌要唱。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荷马,这就是元典精神,这就是鲍勃·迪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不断返回元写作。
蒋蓝:你目前工作如此繁忙,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写作?
李敬泽:2000年前后,我的写作十分流畅。后来写作时间就不够用了。这也没有办法,我只好采取冲刺性写作。近年我在《收获》《十月》开设了个人专栏,让专栏编辑挥舞鞭子赶着走。有时太忙竟然忘记了交稿,干脆最后一天交稿。这也好,一年也完成不少作品。
蒋蓝:你说过,一个作家要让傻瓜与天才都能服气很难。
李敬泽:是的。首先是反省自己:在价值向度上,我必须知道好与坏。然后,在文本上等着别人来挑毛病。对此,我又有把握地说,我有“吊花腔”的本事。书,好看!
蒋蓝:你是非常敬重才华的。
李敬泽:一个有才华的人需要得到最大敬重。才华是一种气息。才华在任何正常时代都是珍稀资源。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