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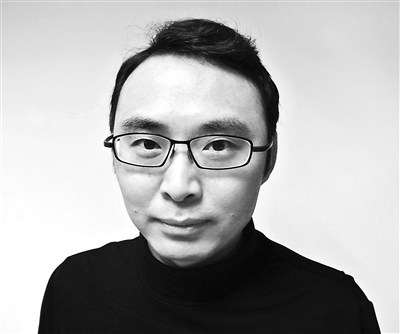


话剧《结伴关系》剧照
采访者:刘雅麒
受访者:顾雷
时间:2018年8月12日
简历
顾雷,中国当代剧作者、导演。顾雷的戏剧作品,冷暗的格调中,融汇了轻灵的黑色幽默,在写意的空间造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气质,兼具平民气息和知识分子思辨的韵味,并保持着一贯的高水准,注重观赏性和艺术美感的平衡。主要代表作品有《告别无羁的长夜》《十个人的夜晚》《顾不上》《人生不适情》等。
1你导演的《结伴关系》将于9月14日-16日在隆福剧场演出,这部戏今年重演相比去年9月份的首演有怎样的调整变化?
《结伴关系》进行了微调,但不大。我觉得是这一年我们社会情境的变化比戏的变化大。国家放开二胎了,一两年反馈的效果却没有那么理想;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呼喊声越来越大了;2017年登记结婚的有1000万,离婚的却有470万。在这样的情境下,看《结伴关系》里的人物和争论,意味更多了吧。
2你的戏剧启蒙来自于?
我从小就对舞台感兴趣。从小学、中学开始,就在组织学校文艺方面的演出。大学里,戏剧和唱歌是能上台的两种方式,因为我不会唱歌,就选择了戏剧。比较而言,戏剧更有文学性,更有诗意。我读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加入了学院、学校的剧社,进行演出。
1998年3月,当时大一,刚上大学半年,我们有一个小品演得不错,学院剧社的社长请我们看话剧,买了在首都剧场演出的大导林兆华的《三姊妹·等待戈多》,主演有濮存昕、陈建斌、龚丽君等。我穿着我最好的一双皮鞋,穿着中山装就去看这部戏了。看戏的时候心潮澎湃,如醉如痴。过去在老家石家庄也看过话剧演出,但是完全没法跟这部戏比。后来我见到大导的时候跟他讲过这是我在北京看的第一部戏,当时童道明先生就在边上坐着,他说,你在北京看的第一部戏是林兆华导演的《三姊妹·等待戈多》啊,你是多幸运啊。
我当时十八九岁的年纪,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在一个外地青年心中,北京这座城市有无数的想象力可以在夜里释放出来。而这部戏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想象力。一片水面中,三姊妹被困在孤岛上,她们在外省回忆自己的童年、青年,想象着莫斯科的美好,想象有一天能够回到莫斯科。濮存昕和陈建斌演的弗拉季米尔和艾斯特拉冈,踏着水跑过来,看着一棵地上的小树枝,在等待着他们等不到的人。记得当时是吴文光老师作为朗读者把契诃夫《三姊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两部戏给串起来。他把一块表扔进了水里,就像时间被投掷在水中。水花四溅,地上的水,倒映在舞台的顶部。几个人在这个地方等待着,惆怅着,孤独着,呐喊着。对我这样一个十八九岁、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青年来说,这是一次精神之旅。后来我坐在电车上回学校,感觉几乎要融化在春天北京的夜里。那次看戏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剧启蒙。
3听说你从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时并没有想要从事戏剧行业,后来是怎么改变主意的?
《沃依采克》是我和学校的太阳剧社合作的一部戏,也是我大学本科阶段的最后一部戏。那年我大四,22岁,快毕业了,工作已经基本定下来了,即将回到石家庄一个制药企业做研发。当时从北京要回石家庄,也有自己情感上的纠结,感觉很憋屈,这部戏是我当时心情的一种表达。
这部戏后来有机会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演出一场后,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我决定留在北京,第二年又考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当时也没有想要靠排戏来生活,只是想留在北京,觉得在北京的这个状态是舒服的,回到石家庄有点憋屈和压抑。在当时的我心中,北京和石家庄是两个不同世界。后一个世界很现实,但前一个世界好像可以做做梦。
我非常幸运,读研究生没多长时间,就得到机会去林兆华导演的工作室,在大导身边学习和工作了。林兆华导演看了我的《拉斯科尼科夫》和《瞎子和瘸子》,觉得还不错,就留我在他那儿打杂。大导对我真不错,给我提供了资金和北京人艺这样的平台,提供指导,还给开工资。从2003年到2005年,两年多的时间,我相当于跟着大导读了个研究生。当时林兆华导演应该说是创作最高峰的时候,我算林兆华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等他排戏的时候可能做一些助理的工作。大导还请来了其他的著名导演、老师,给同学们办工作坊,我就在旁边观摩学习。大导不是那种给你具体指点各种技术的老师。他说他跟戏剧学院学生上课时候,也是没什么可讲的,你们提问吧。他没有具体跟我说过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大导对我的评价是:顾雷,他行。我理解这是大导对年轻人的鼓励。后来我研究生毕业,需要自己找工作了,才从大导那儿离开。这段学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也阴差阳错地推我上了路。
4你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生物化学专业的,你学的专业对你的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生物学专业给我提供了不同的看问题的视角吧,让我可以把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放在戏里。我这两年新写了一个戏叫《进化》,里面有很多生物学的想法和观点。现在这个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做。我写的剧本,其他导演来排。
(问: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进化》这部戏吗?为什么没有自己导演?)
《进化》是讲一对年轻的北漂夫妻想要美漂的事。他们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处处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终于有个机会,他们想通过变成美漂,超越他们身边的一等公民。他们为这个机会努力,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像动物,他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像动物生活的丛林。
《进化》排的时候,我在排《结伴关系》,没有时间去排这个戏,就把剧本拜托给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吕睿导演。另一个考虑就是我写的戏,过去都是自己导,该放手让它去找其他导演了。果然,这个口一开,过去写的三个戏,分别在英国和罗马尼亚找到了它们的养父母。
另外一方面的困扰就是,生物学让我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倾向于保守和悲观。之前总觉得个人的意志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人有的时候是扛不住他的自然属性的。世界很复杂,人很难认清本质,但往往把它简单化了。有的时候我有些想法和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是相背离的,我现在还不敢把这些想法都写入自己的戏里。
5戏剧创作遇到瓶颈时通常会怎样处理?
我有很多剧本起了个头,写不下去就放在那儿了,想着放一段时间有了想法再写,但后来发现自己对这个戏没兴趣了,觉得不值得再弄,就扔在那儿了。大概放弃了有十来个这样的剧本。我的剧本都是多年的积累,《顾不上》准备了很多年,在2015年终于结出果来了;《人生不适情》的剧本也是在电脑文件夹里放了好多年,在2016年完善了一下又拿出来了。
6你如何评价和定位自己的剧作风格?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我的风格就是一个石家庄青年来到北京的风格。从一个小地方来到北京,带有很杂糅的气质和色彩。我觉得这种杂糅是个好事,很多东西都是杂糅的。是玩闹和所谓“戏剧”的杂糅,是粗野和诗意的杂糅,是带着石家庄的乡土气的我和北京、图书馆里更广阔世界的杂糅。
我20多岁的戏都是一个调子,比较闹腾,有某种宣泄和叫嚣的成分在里面,不是很现实。后来,戏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平静了,我现在不那么较劲了。现在再像前些年那样较劲的话,觉得自己的身体吃不消了。
过去,在我心里,石家庄和北京是两个世界,今年40岁,我现在觉得北京和石家庄已经没有区别了,两地来回也很方便。在北京我已经安家生子,生活稳定,有了小孩了。北京也不像过去那么神秘,那么有趣了。如果说过去的我是一个杂糅的状态,再往后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正常了,和在北京生活的差不多这个年纪的人的生活差不多一样,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波动,见识也少了。
7你挑选演员有怎样的标准?你似乎不看重科班出身,喜欢与非职业演员合作?
没有什么特定标准,只要适合剧本角色。职业演员的优势就在于技术、控制、稳定性能做到很好,但有的时候缺少了那么一点光彩。有的时候职业演员用七八分的情感和投入就够用了,观众看不出来,我看了很多遍,我是能看出来的。这和完全沉浸在戏里是不同的,当然,他也不可能一年300场场场完全浸入,那他受不了,非疯不可。非职业的演员可能技术上没有那么成熟,但如果与角色特别契合,就能演得特别好。2016年,排的《人生不适情》十四五个演员,几乎都是非职业演员,单独或少数几个人的排练连缀起来,一半的内容都比较私人,演员们多数投入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和状态中,这个戏在小剧场里看,是比较舒服的,演员全身心投入后自己内心的力量和活力是最动人的。这是非科班演员的优势。
8你比较欣赏的戏剧导演?
林兆华导演。大导自己发展出了一种很舒展、很诗意,有传统审美意味,又很现代的舞台美学,比如《赵氏孤儿》《风月无边》。但很可惜,我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发展。20年前田沁鑫导演展示出来的个人舞台风格,也是非常令人惊艳的。比如《生死场》,在我看来,可以算是十年一遇的经典。法国的戏剧导演阿里亚娜·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可以算是我的偶像了。她想象和重新创造了东方的艺术,在精神上继承了很多东方艺术的很美的东西。比如,《最后的驿站》中,以覆盖舞台的水布表现海,演员在水布里演海上的偷渡者,演划船、落水、挣扎、被救起等这些行动,很现实的移民题材和水布这样的假定手段,在舞台上有一种奇妙的落差和美妙。再比如,《洪水中的鼓手》以全部真人演员演日本净琉璃,创造了视觉上的种种奇观,表里都是东西方的水乳交融。
9你在不同阶段对书籍的选择和偏爱有什么变化?
我在读大学、研究生阶段读了不少戏剧方面的经典名著,毕业后就读得比较少了。那个时候不谙世事,很多经典虽然是读了,但是读不懂。现在看很多戏,发现自己其实当时根本没看懂。
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他也是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作家。契诃夫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含混的世界,他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也几乎没有确定的去评价什么。他一边在拿这个人开玩笑,一边在同情这个人,诉说人们的难过、失望、孤独、希望。去年,我有幸随团去契诃夫的故居参观。他的故居现在也是他的一个纪念馆。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床很窄很小,想象着他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写作,有那样的思虑和心思,理解了他为什么会死于肺病,这是玩笑。
我现在文学的书读得少,读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书比较多。最近在关注的一本书是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的《为什么佛学是真实的》(Why Buddhism is True)。可惜现在还没有中文翻译版。我听喜马拉雅上的书评,对这类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书非常感兴趣,我的兴趣在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比戏剧探讨强太多了。
10你在文学方面的偶像是?
高中我读的是我们那儿的一个重点中学,学习很苦,压力很大,我就找到了一个安慰自己的办法——读诗,现代诗。也读,也写,也在广播里听。晚上十一二点石家庄电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子夜诗会》栏目,介绍了很多国外的诗人,其中有一位我非常喜欢——智利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直到现在她也是我的偶像。那时候,十七八岁嘛,听她的爱情诗《死的十四行》《母亲的诗》,真能感受到爱的疼痛和绝望,后来看了传记,更理解了这个一生爱情不如意,却写了最美爱情诗的人。
11你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戏曲,怎么培养的这个爱好?你欣赏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小时候夏天乘凉,小孩子胡闹,我爸说,别跑了,我教你们唱戏,就教我和我姐唱戏。小孩子引导,上了路,就好走了,高中之前,我很喜欢,浸淫在里面。高中大学,有了更有趣的诗和话剧,嗓音也变了,京剧就先放下了。后来排戏演戏,别人发现,我排的戏有戏曲的味儿,我才意识到京剧在我身上留下的东西,让我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似乎成了特色。足见,不同的背景,对个人的创作有多重要。我是一视同仁地看待所有我接触的艺术的,一圈下来之后,觉得戏曲是很有价值和我们自己特色的。大导也是吃透了传统戏曲的好处,他们30年前提出全能戏剧嘛,各种艺术,都可为我所用。
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把他那把胡琴拿到了北京。小时候练过,现在没事拉一拉,聊作安慰,确实救了我,又引我重回了对京戏的喜好,是我自己的新阶段吧。
不同的阶段喜欢的艺术家流派也不同,小时候喜欢梅、杨、余,后来喜欢程、麒,现在喜欢赵燕侠,想想这都是人生难预料,小时喜欢完美,后来喜欢特色,现在喜欢根本。现在经常去看演出,戏曲演出性价比比话剧高多了。
12成为父亲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对孩子有怎样的期望和要求?
孩子是生命的一种安慰和延续。孩子表现出来的很多东西,让我越来越理解生命,也让我的人生观变得完整。
我爸爸性格很好,从来没有打过我、责备过我,总是带着我玩,比如钓鱼啊、听戏啊。他是我很好的玩伴和老师。他很温和,没见他和谁吵过架、打过架。父亲是我的榜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他一样的父亲。
我也希望孩子能在工作之外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像排戏对我而言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取悦自己的纯粹的享受。我想让孩子也学一学昆曲,这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精华,我觉得中国传统戏曲中精华的部分在世界戏剧范围内看也是最优秀的。可能只有西方的芭蕾能和中国的昆曲的美相比。
13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我想和三观比较保守、比较一致的人交朋友,但很难得。反而和三观不一致的朋友经常探讨事情,成了很亲密的朋友。
14对你有启发的电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色戒》《钢琴师》。
15你喜欢的运动方式?
跑步。在家练哑铃,到了该增加肌肉的年纪。
16你是个球迷吗?
我喜欢看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中的德甲,硬件条件好,看拜仁慕尼黑这样的球队踢比赛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德国队原本的风格是很硬朗的,但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德国队太软了,缺乏力量,而“软”的核心代表就是近期宣布离开国家队的厄齐尔。
(问:看球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比赛的输赢、绿草地上鲜明的颜色和球员。现场看球有点像看戏,身临其境,感受现场气氛。人们可以在看球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获胜的满足感。这是对我而言看球最大的乐趣。
17请描述几个你生活中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刻或场景。
周末的早晨儿子来床上捣乱,一家三口在一起赖床、说笑;看自己的戏在舞台上演出,坐在观众席里替舞台上的演员着急,都是很好的时刻。
18当下比较关注的社会话题?
最近我比较关注狗咬人和人毒狗的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不好站队。我的观点是,人永远比狗重要,这一点不能混淆。我能理解狗被毒死了对狗的主人来说是个很伤心的事,但我觉得避免此类事情发生比较好的方法是养狗的人管好自己的狗,拴个链子,套个嘴套。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