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杨逢彬教授的《论语新注新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月就已再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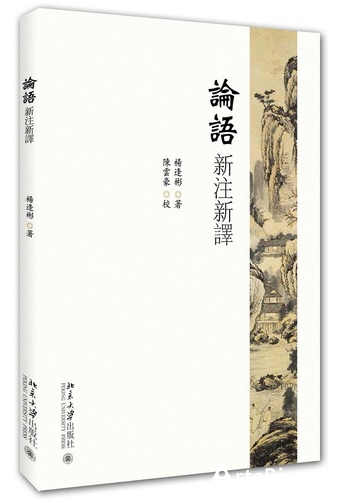
被访者:杨逢彬
采访者:臧继贤
杨逢彬的祖父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其堂伯父为语言学家杨伯峻,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已累计印刷200万册。在杨逢彬看来,杨树达整理古籍之所以精湛绝伦(代表作如《汉书窥管》)在于他自觉地将训诂和语法相结合,而杨伯峻也是身兼语法学家和古籍整理专家两重身份。“但遗憾的是二人都未能见到计算机技术普及的这一天。”而《论语新注新译》“正是我较为全面地运用现代语言学,加上计算机检索技术,然后坐冷板凳十几年的成果。”
在杨逢彬看来,“杨伯峻先生、杨树达先生也运用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法学。虽然只是零星运用,但已经使得他们高出侪辈。而《论语新注新译》是全面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注释中国古籍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给《论语》提供了一个在词句注释方面最精准的注本,在词句注释的可靠性准确性方面较大幅度地超过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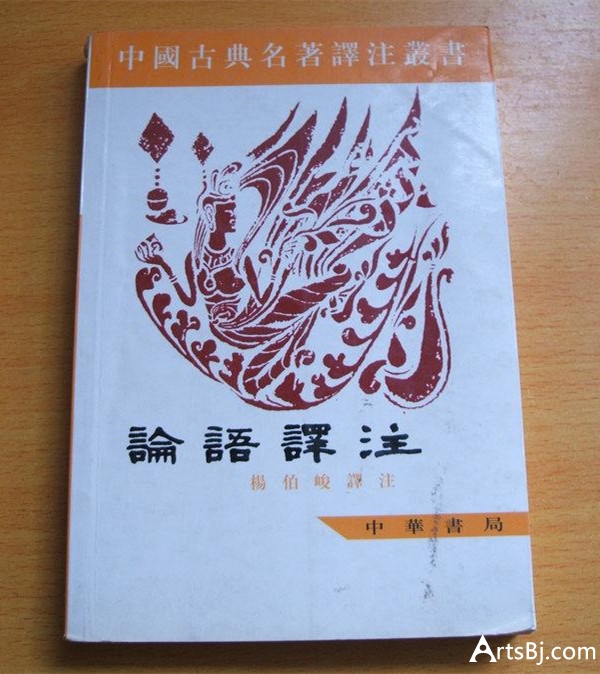
“我坚信我的《论语新注新译》一书中的许多考证将来都会成为训诂著作和语法著作的范例。只是我自己做注释,它达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最清楚,别人不做这个,就对它的认识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自己说的话,往往别人也不大相信,那只有等时间去检验了。”
在被问及家学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时,杨逢彬讲道,最大的影响就是爱学问、做学问已深入到骨子里,只想一心做学术,对于学术之外的荣誉并不是十分在意。同时他也讲道,即使撇开家学的影响,自己的同龄人也是很爱读书的,包括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就读的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氛围也非常浓厚。可相比之下,杨逢彬现在见到有的中文系学生,即使临近本科毕业,连一本课外书可能都没有看过。
近日,杨逢彬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题为“E时代我们如何读古书“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澎湃新闻(www.thepaer.cn)就互联网时代注古书的注意事项、他所受到的家学影响以及武汉大学国学班的有关问题专访了杨逢彬。

“E时代我们如何读古书”讲座现场(大今文化“行走的文化中国大讲堂第3期”)左为主持人今波,右为杨逢彬。
家学的影响
澎湃新闻:家学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杨逢彬:我20多岁的时候,我女朋友要我去她家过年,我就发现她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不同。她的家庭里兄弟姐妹、父母和老外婆之间的亲情很浓烈。而我总是和祖母以及保姆待在一起,父母在外地,兄弟姐妹也不在一起,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不上别人家那种自然而然的融洽。刚开始我很羡慕别人的家庭,我看小说《青春之歌》,描写林道静所在的那种大家庭,我当时觉得就有点共鸣 ,好像觉得我自己有点儿不幸似的。你看我现在在这里,人家说我是杨树达的孙子,又是出生于一个花园洋房,小时候还有保姆帮忙洗脸、喂饭。实际上,和自己的父母团聚在一起了,就感到没有别人的家庭那么温暖。
但是开始做学问以后,发现这种家庭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它使得我爱好学问,不是我为了做学问而去做,而是想做学问爱做学问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比如说我为什么读古书,就是因为停课闹革命,学校都废了。我和祖母待在家里,父母也不在身边。我祖母年纪大,也不可能事事管我。我白天闲极无聊,有时候爬窗进我姑妈的房间找书看,我的姑妈、姑父都是老师,还有祖父、伯伯和两个姑妈的藏书。开始当然是看白话的小说,然后看戏曲集,包括《莫里哀全集》等等,好像是王了一(力)先生翻译的,他送给我祖父的,上面有他老的题字。这些看完了,就剩下古书了。那怎么办呢?要么就每天干坐着,外面还在整日武斗,打枪打炮的;要么就看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读古书,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电影看。一开始还看有故事情节的古书,如《聊斋志异》和《子不语》等等,后来也看古代散文,如读到《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特别兴奋,摇头晃脑地读。当然许多字读错了。表哥就笑话我,然后查字典,这样就认识了许多生僻字。就这样长年累月地读,已经上瘾了;一没书读,就浑身不对劲。上厕所也带本书或杂志——杨家其他人也这样,如祖母就坐马桶上读书;伯父拿本书上厕所,一呆一小时,姑妈送他一外号“老挝”(老屙)。
就像《论语》中所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就是痴迷某种东西了。我就是痴迷于学问,所以一心只想着它。在学校里也不大在意教授的级别以及各种称号,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道理上来讲这两者应该是吻合的,谁学问做得越好,这些荣誉就应该授予谁。现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获得荣誉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朝那个方向努力,要大量牺牲做学问的时间。我就是爱好学问,不是很爱好其他东西。我坚信我的《论语新注新译》一书中的许多考证将来都会成为训诂著作和语法著作的范例。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已经看过几十个古人所做的古籍词句考证的经典范例,最好的也就是王念孙的“终风且暴”了,我这本书里像“终风且暴”这样的考证20个是有的。现在没有这样的成果,只是我自己做注释,它达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最清楚,别人不做这个,就对它的认识差一点。但是自己说的话,往往别人也不大相信的,只有等时间去检验了。反正我也马上60岁了,那些虚名的东西我全都不在乎了,剩下的时间做出一点“干货”和好东西,能够流传下去。其实我也是有点自私的目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就短暂的几十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就想做点好书。因为我们家里有榜样在,杨树达先生去世60年了,就是我出生的那年他去世的。他人虽然不在了,但他的书还一直在印,人家还不断提到他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在人们的心里。杨伯峻先生也是如此,他也去世24年了,但是他的《论语译注》已经印了200万册了,大家都还在读他的书。所以正像李白的诗:“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的词赋像日月高悬,楚王的亭台楼阁就在荒芜中长满了草。所谓古人讲的“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和“立功”我不行,只能“立言”。古代的皇帝追求长生不老但做不到,只能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还活着,自己给自己造几座丰碑。丰碑就是著作,死后还会不断印刷,也就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没死。
我读中学的时候,年终鉴定里说我有很多优点,但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浓厚。不过我做研究就是朝一个目标奔着,年轻的时候目标不明确,模模糊糊有这么个想法,后来慢慢研究进去,专业思想已经确立以后,理想就越来越具体了。
如果说我是受哪本书的影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人生在世岂能如腐草流萤?那时我11岁,这句话对我的震撼非常大。那么如果不是我这种家庭,就没有这么多书看。“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的伯父把毛主席写的信拍成照片,放在镜框里,这样就没抄成家,所以我才能读到这么多书。要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家被抄,书都被拿走了,那就没书可读了。
澎湃新闻:现在年轻学者如果没有家学传统,那么从事文史哲方面的研究的话,会影响他们将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吗?
杨逢彬:就撇开我这种家庭不说,1980、1990年代的中文系和现在的中文系已经很不同了。1980年代末我到武汉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本科生都可以进书库借书。老师上完课以后,学生就到书库里借十几本书,在下周上这门课之前全部都要读完。不光有这一门课,另外的课老师也会布置读书,也都要看完。所以1980年代末,武大中文系本科生英语四级的通过率不是很高,大家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
我刚到上海大学任教的时候,那时上大印了一本很厚的图书目录,里面是中文系本科生四年需要阅读的图书,至少有几百种。上大前两年做了改革,学生大一的时候不分专业,只有到大二的时候才分。这样学生进专业读书的时间缩短了,督促中文系学生读书的那本目录也不发给他们了。结果中文系的学生除了教材以外就不看书了,老师上课的时候把重点划下来,然后背熟就行了。
上课时说到俞樾,他们不晓得,我说就是俞平伯的祖父。俞平伯是谁,依然不知道。丰子恺也没听说过。中文系的学生不看课外书了!不用和我那个年代比,和1980、1990年代中文系的学生都比不了。我们小时候都在看课外书,读初中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发现一本书大家就会轮着读。那天有个推免(推荐免试)研究生来面试,问她小学到现在,除了课本以后,看过几本书?她报了一个个位数。她说读过《复活》,我就问他聂赫留朵夫是谁,她说不知道,显然是没看过。从小学到大学快要毕业了,读的还是中文系,一本课外书没有看过,你说可怕不可怕?
如果让我谈有什么对策,我建议还是要给学生发阅读目录,督促他们读书。读书都是从没兴趣到有兴趣。我小学的时候就迷恋上看书了,现在让他们至少要大学一二年级迷恋上看书。这和是不是我这种家庭没有关系。现在的教育制度使劲灌输,使学生都产生逆反心理了。
关于武汉大学国学班
澎湃新闻:您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是否曾给国学班的同学授课?
杨逢彬:我也勉强算是武大国学班的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个创始人是邹恒甫教授和郭齐勇教授。当时身为人文学院院长的郭齐勇先生指定我来设计国学班的培养方案。我在上大的一个同事郑妞就是武大国学班第二届的学生,我的儿子是武大国学班第四届的学生,然后跟郭齐勇先生读硕士和博士,博士读了5年,今年8月毕业,现在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中国哲学。
当时历史系的覃启勋教授是国学班的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他主外,我主内,负责一些文件的起草。武汉大学国学班在上海还有一个微信群,我们还经常和学生聚会吃饭。国学班每届就15到18、19个学生,配备的是最好的老师。

2002年,武大国学班招生面试现场。
澎湃新闻:那您还记得当时您制定的培养计划吗?
杨逢彬:我当然记得了。当时郭老师提出一个粗略的设想,课程包括经学、史学、小学和文学四大类,经学就对应哲学系的中哲,史学对应历史系,小学对应中文系的语言学,文学对应中文系的文学,根据这四类来设计主干课。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以读原典为主,这和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实验班不同,后者是把文史哲的主干课捆在一起。在武大国学班之前,北大以前也有一个号称“国学班”的实验班,办了一段时间就停办了。其实北大的那个不是国学班,而是相当于武大的人文科学实验班。而国学班是把文史哲各个学科偏古的课程捆在一起,而且还加了原典课程,比如“论孟”是一门课,“老庄”是一门课,“《史记》、《汉书》”是一门课,这是国学班的特点。
然后我自己又对应小学、文学、史学和经学四类课程加入了西方的和现代的课程,有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世界历史和西方哲学。我离开武大后,这个培养计划是不是做了调整,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语言学概论是没有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这门课砍掉。
当时我设计好这个培养计划之后,郭齐勇老师就召集了几个老师开会,对培养方案进行修补,不过没有修补太多,80%-90%还是我原来的方案。过了几年因为课程太多,学生吃不消,又调整了一下,减少的课程作为研究生的课程。我还和郭齐勇老师一起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的会议。实际上武汉大学是最早开办国学班的,只是我们不声张,埋头苦干,不像人大那边直接成立国学院,声势浩大。武汉大学2001年开办国学班,而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设计培养方案了。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武大国学班的培养效果如何?
杨逢彬:这个要比较之后才好说,我现在欠缺的就是比较。应该还是可以的,好像出路都挺好的。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去国学班上课,后来他成了国学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后他去南昌大学创办了一个国学院,他就是南昌大学国学院的院长程水金。应该说武大的国学班办得是比较早的,我们最早是入学后全校的爱好者自愿报名,所以那时他们在国学班的学习只有三年半,第一个学期是在各自原本的专业学习。包括我儿子原来也是在人文科学实验班,后来才考入国学班。我离开武大后,学生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报考国学班了。这样做效果好一些还是差一些我也不清楚,但至少学习时间延长了。
澎湃新闻:那从学生成才的角度来讲呢?
杨逢彬:我以上大的同事郑妞为例,她是第二届国学班的学生。开始我不知道谁学得比较好,因为我负责管理国学班,包括程水金老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告诉我说有一个叫做郑妞的学生很不错。她国学班毕业之后,就去读武大古籍所骆瑞鹤先生的硕士,后来又去做北大孙玉文先生的博士生,然后毕业到上大来工作。天天做学问,生了小孩还没有多久,就天天去办公室做学问,那完全是学问已经深入骨髓了,如果让她不做,别提多难受了。这样的学生每届都有好几个。
互联网时代的古书译注
澎湃新闻: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需要遍阅群书。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再具有老先生所具有的私塾功底,那么计算机的古籍检索技术可以弥补这一点吗?
杨逢彬:检索的方式可以把要求降低一些,但不能降得太多。读古书还是必要的前提,古书都不通,如何去一一辨析例句?但是以前的学者太相信语感,就把我们考察分布必不可少的“审句例”步骤就给减免了。其实语感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因为前人读古代汉语是把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书“一锅端”,形成了泛时的语感,而不是共时的语感。比如我祖父语感极佳,《汉书》都能背诵;《孟子》中有“盖自是台无愧矣”,说的是鲁缪公屡次派“台”——小官吏去馈赠子思吃的,子思受不了,很不礼貌地让小吏滚蛋,所以从此小吏不来馈赠了。我祖父却读“台”为“始”,理由是“无馈事属缪公,不当以舆台贱隶言之”,即应该说馈赠曾子的鲁缪公,不该说小吏——这是依据情理。其实“自是+名词+动词”当时很常见,如《左传》的“自是晋无公族”,而“始无”古书中虽不少,却出现很晚,如《南齐书》的“民始无惊恐”。可见泛时的语感有时是靠不住的。
但是语感又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如果要注释古书的话,熟读古书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切免谈。我现在就要求我的学生——包括一个来自朝鲜的进修生多读多背。
澎湃新闻:那读古书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学生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杨逢彬:至少用学习英语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功夫和时间。
澎湃新闻:从您的经验来说,用检索古籍的方式来辅助古书的注释有没有可能遇到问题?
杨逢彬:检索的对象应该是比较高频的词。如果是高频词,我们考察《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就行了,它们基本上是同时代文献,而且所记录语言都是山东半岛的。如果是低频的字词,在同时代的文献中检索不到几个,但也有其他的弥补办法。第一,把检索的时段拉长。比如“未知,焉得仁”的“知”是如字读“知”还是读若“智”,我们考察了11部古籍。如果还是书证不够,那也有其他办法。低频词总有自己所属的小类,我们就可以考察同一小类。小类的分布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分布很接近。所以我们考察词性词义相差较大的字词,就考察它们各自小类的分布特征。
如果这样做还行不通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在汉朝人和清朝人所做的结论之间,一般来说汉代人所说较之清代人所说,其准确性可靠性要高出许多。王力先生就这样讲的。我在研究中一开始是没有倾向性的,但后来统计考察的结果,往往是汉朝人说得对,清朝人说得不对。王念孙“终风且暴”的例子是极个别的例外,绝大部分是汉代人说得对。李零先生批评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采用清人的研究过少,其实采纳得越多,错得越多。但为什么李零先生会得出这种结论呢?因为以前对清人的估计过高。清人和汉人不同,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汉人就说是什么意思,没有说为什么,但清朝人会说出缘由,当然有些是语言外的证据,也有语言内部的证据,但又没有围绕分布来。就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试论注古书不能轻易推翻汉儒成说》,我也引用了王力先生《训诂学》中讲到的不能轻易推翻故训,故训就是汉朝人的东西。特别是当清人从语言系统外找证据去推翻汉儒的时候,100%会错误。所以没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汉人的。当然这样的话,可靠性就会降低,危险性就大一些,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
还有就是我们用了一些概率论的知识,比如说我找了一个语言学内部的证据,也是考察分布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证据有80%的可靠性,也就是有20%的例外可能性,找到另外一个证据也有80%的可靠性,那么两个证据一起用的时候,不可靠性就变成了4%,也就是可靠的概率提高到了96%。如果再找到一个可靠性有80%的证据,那么不可靠性就变成了0.8%,那么可靠性就变成99%以上了。我曾经考察一段话是如何句读的,就是《论语·宪问篇》的“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我主张读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我列了六点,并不是每一点都是一个证据,但至少有四个证据,那完全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了,都用的是考察分布的办法。这篇发表在《中国语文》今年第四期。
再比如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有两种解读:1.老百姓需要仁更甚于需要水火;2.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厉害。截然相反的两种解读,我考察后发现,“甚”常常是和不好的东西在一起用,很少和好的东西一起用,比如“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做不好的事情,一次就过分了,还可以两次吗?特别是用“甚于”进行比较的时候,经常是比较两个东西哪个更不好。但是因为有例外,就有危险性。我再考察《论语》时代的“水火”,常常和毒药这些对人会造成伤害的东西一起用——但是也有例外,是讲烹调里的水火。两个证据都有例外,但是一起用,就比较倾向于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厉害”这种解读。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文章中说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甲骨文的研究都是以整理注录刻辞、考释文字、服务于古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甲骨文是较晚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挖掘和研究的领域。”那服务于古史研究的甲骨文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甲骨文研究区别在何处?
杨逢彬:甲骨文的语言学研究,最早的可能是胡小石的《甲骨文辞例研究》,但辞例研究还不能说完全走上了科学轨道。1953年管燮初先生有《殷墟甲骨卜辞语法研究》一书,1958年陈梦家有《殷墟卜辞综述》,内有《文法》一章,这一章其实篇幅较管书为大。陈书较管书有进步,但错误仍多。如认为“雨不雨”是反复问句。其实第一字为占辞,后二字为验辞。意为“下雨吗?”“没有下雨。”新时期有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严谨扎实,可惜只限于语序。有一些作者语言学根柢欠佳,许多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一是缺乏历史观,后世为介词者,甲骨文中也一定是介词;而对其表现的动词特征视而不见。二是凡作状语者,必认为副词,其实可作状语者决不限于副词。类似错误不胜枚举。导师郭锡良先生忧之,故命我作甲骨文语法研究,总算大体上能令先生满意。

甲骨文的语法研究,是甲骨文语言研究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还有徐朝华甲骨文词汇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和以往考察字形——即认字的研究有所不同。一为文字研究,一为语言研究。至于与用于古史考辨的甲骨文研究的差别,就更大了。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