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臧继贤
受访者:残雪

作家残雪。2015年,对于作家残雪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她同时获得了两个国际文学奖的提名: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和英国伦敦的独立外国小说奖,另外还与她的翻译安娜莉丝共同获得了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
面对获奖的喜讯,残雪很高兴她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她看来,自己能够得奖,是因为学会了西方的思维工具,又将中国文化的特质很好地融入进去,让西方人觉得很新奇。
但在国内文坛,残雪却似乎没有得到如此的理解和认同,而她自己也不愿意和中国文坛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甚至不愿意再作出评价。“我早就说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也懒得评价了。因为我搞这一套,他们不欣赏我,我也不欣赏他们那一套。”
在残雪看来,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固步自封,只知道守住和回归传统。但她认为仅仅这样做是不能够恢复传统的,因为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相对于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但需要比较、学习和融合,只有再创造才能守住传统。”
但其实1980年代的西学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再次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残雪也是那批受影响的作家之一。不过在她看来,其他人已经放弃谦虚地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劲头,还是觉得自己的传统文化好。
残雪最近五年在研读西方哲学家的经典作品,并且她还在写一部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品,叫做《物质的崛起》。“文学与哲学探讨的是相同的问题。只不过最近几十年,文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哲学。”
她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最终指向的虚无,“现代人已经解决了吃饭穿衣的这些问题了,但他们面临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人际关系和感情等问题。”
“不过中国现在还没有解决吃饭穿衣这些问题,所以后面这些问题在中国暂时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残雪试图在自己新出版的小说《黑暗地母的礼物》里描述一个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她说,这是一本欲望之书,也是在写爱情。“就像瑞典的评论家夏谷所讲的,我的几本写欲望的书描写的都是人类社会的乌托邦,在探讨什么样的关系是最理想的关系,什么样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我的探讨是超前一点,但也不是超前得那么不得了,因为已经出现了这种问题。”在残雪看来,《黑暗地母的礼物》的读者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可惜目前这种人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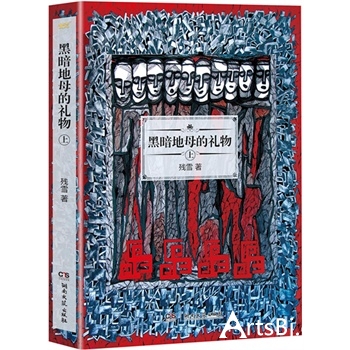
臧继贤:您自己觉得您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主要因为我的作品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方面,我应该是在中国作家里面做得最好的。所以国外的读者能够把我的作品作为文学来接受,我觉得这是很少有的,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的工作。然后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要不然那么多外国人都没有得奖,而为什么我的作品能被选中呢?如果我的作品类似他们曾经诞生的那些文学风格,比如卡夫卡、但丁、塞万提斯等,那他们就没什么新奇感了。
臧继贤:在之前的访谈里面,您提到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比如说“自我意识”,那您是不是除了对西方的文学比较感兴趣之外,还对西方的哲学比较感兴趣?
残雪:是,我最近五年里一直在攻读西方哲学。我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而我这么多年一直看西方哲学那些前辈的作品,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我们这种实验文学和哲学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探讨的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界,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取得的成就比哲学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以我就想把哲学最根本的问题重新探讨一下,也是我的野心。因此我一直每天坚持用四个小时读西方哲学,已经坚持了有四五年了,黑格尔、康德和尼采这些哲学家的作品我都读过。
我最近在写一本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书,现在已经在扫尾了,主体部分和导言都写好了,需要继续再检查几遍,可能有60多万字吧。但我不是“文革”那种大批判。萨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的大哲学家。对照他的观点,我把我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我的这个体验。因为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我和萨特等人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但作为中国人,我有我不同的体验和想法。萨特不是自己也写过文学嘛,当然他写得不是太好,也算不错了。所以我和萨特在这个方面特别有共同点。
但是我作为中国人,同萨特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图型。我的那套生命的图型跟他的存在图型是两码事。我这本书既是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也涉及了西方的其他经典,主要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早期手稿等。一方面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这些观点,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民族以前并没有这种系统的哲学,这些逻辑系统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另外一方面我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觉得我有优势,可以用我这本书和他们抗衡一下。所以我在大概四年以前就开始写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完成,最后还差一点,不过也快了。
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觉得激动人心。因为我的观点都是从我的文学创作中来的。“文学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哲学前面的探险队。”我一直这样说,我在国际上跟那些外国人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文学比起西方的经典哲学,已经走到它们的前面去了,文学现在更厉害了。
我是怎样做的呢?通过学习西方,然后进行反思,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就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实际上就改造和再造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继承传统只能通过再造或者重新创造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才是传统,因为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你说你是传统,他说他是传统,谁是传统啊?怎么能够肯定呢?这很难说的,过去了的就是过去了的,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那种环境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你还说就只能是那样搞,不创造,就是被动地去继承一下,那是不行的。要恢复传统必须要创造,而文学在创造性方面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我们搞文学就叫做创造,通过创造把我们古老的文化再重新化腐朽为神奇,重新把它发扬。这是我的思路,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家一般讲的那一套继承的思路不同。
臧继贤: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是受父母的影响吗?
残雪:有吧。因为我父亲以前攻读马克思主义,家里都有《资本论》那些哲学书,所以小的时候就看过,就激起兴趣了。我记得我十四岁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把《资本论》都通读过一遍,那个时候也给了我好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所以我后来搞的那种文学就是跟谁都不一样了,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是那种本色演员,搞几下子就没有了。所以还是从小有这种氛围的,有积累,到一定时候它就以文学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臧继贤:您和您的兄长邓晓芒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人选择做文学,而另一个人选择哲学?
残雪:我跟他还是不同,他是那种比较冷静的气质,我可能更加现代一些,就是那种容易冲动的气质。因为家里到处、包括朋友和邻居有那些书,包括俄罗斯和西方的文学,所以很快我就融入了文学的氛围里面,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十几岁的时候是有几年看过哲学书,后来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觉得文学更能够吸引我。因为我看过的这些文学就是哲学嘛,它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方式——以物质的方式来表达精神的东西,一种情感的精神,其实和哲学就是一回事。
只不过因为气质的差别,我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搞了30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我搞的这个东西确实有点优势,就是在这些大师的指引之下,从但丁、莎士比亚开始,还有《圣经》,一直到后来的这些现代派,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有这个深厚的基础的。
臧继贤:您所讲的“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是指什么?
残雪:我是一个二元论者,我所指的物质就是精神,精神和物质二者是分不开的。西方把精神的那一维已经搞到了顶点,但是物质这一维还没有起步,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了,就是我们古老的文化在这个历史关头面临了机遇。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可以把物质这一维开发出来,就是物质和精神的一种抗衡。
我认为世界最高的终极设定就是精神和物质的抗衡,就是“有”和“无”的抗衡。我是一个二元论者。西方是一元论,认为精神至上。它的唯物主义的那种物质至上也不是真正的物质至上,因为它的物质没有精神化。而我所讲的这种“物质”是有形的精神,有质量的精神,所以这和黑格尔、康德都不同了。我的“图型”也是有质量的,不是那种空灵的图型了,而且更有力量,是从大地那里面生发出来的。
臧继贤:那您和您的兄长会讨论哲学问题吗?
残雪:讨论啊。之前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于天上看见深渊》,就是鲁迅的那句话了。在网络上卖得还可以,我看到印了一万多册吧,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今年一定要推出第二本,叫做《旋转与升腾》,可能有70万字吧,之前拖得太久了,现在得到了资助,所以一定要推出。内容还是我跟他的谈话,第一本也是谈话录,谈的是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既谈哲学又谈文学。第二本哲学谈得更多,基本上就谈哲学问题和抽象问题了。
好多人都在盼望这本书,尤其是那些学哲学的,想从这里面找到一些新东西。我跟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共通的地方,另外他的哲学根基非常深厚,在这个方面可以指导我往前奔了,像探险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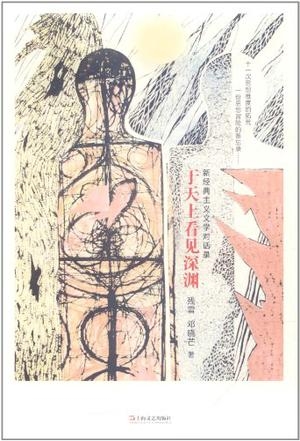
臧继贤:在您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西学热对于文学的创作有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
残雪:当然有积极的影响了,我就是这一批里面出来的。当时出过不少好东西,包括最突出的像余华早期的创作,还有一个叫张小波的,我给他写过几篇评论,他写了三篇中篇小说。梁小斌是后来居上,这些都算是一流的作品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小说散文,就是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拿得出手的一流作品。但是可惜后来就不再学习了,说还是中国的好,还是我们自己的更有东西可学,“自己的东西都没学完,还去学人家”,都是这样一种腔调了。
臧继贤:您之前在采访中也谈到,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缺乏一种自我意识,您能具体谈谈吗?
残雪:就是不善于分析自己,只是大家这样做我就跟着做了,一窝蜂。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要成堆,“个性”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遥远的事情,包括我的作品读者量也还可以,但是比起他们那种主流的传统文学,销量就少得多了。可能还是少数不满意现实的年轻人来买我的书。当然能够卖一万多册也不错了,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也算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一窝蜂,一窝蜂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最大的特点,没有自我意识。要看别人怎么做的,买房买车和赚钱,不都是看别人吗?就像那个学者说的一样,“要看自己,就难于上青天。”
臧继贤:这也是造成中国文学缺乏内省和自我批判的原因吗?
残雪:对,缺乏精神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的确是西方搞到顶峰去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把物质的这一维搞到顶峰去。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也面临最大的机会和挑战。
臧继贤:您曾经说过《红楼梦》也有缺憾,比如缺少性心理的描写。
残雪:《红楼梦》是一个奇葩,它独独作为文学,就已经超越了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文学的特点。因为曹雪芹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有的时候它就超出自己的文化了,走到自己的文化前面去了。虽然曹雪芹口口声声说,自己好像比较提倡佛教,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描写,一点都不佛教,都是非常入世的,都是非常认真地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直追求到死。一个个都是那样的人,哪里有佛教?
这就是纯粹艺术家的特点。《红楼梦》远远地走在其他那些所谓的经典的前面,而且高出一个很大的档次,达到了精神描写的层次。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说艺术是探险队。哪怕你的文化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没有描写精神的文学作品,除了《红楼梦》以外就很少了,有的有一点点,像《金瓶梅》什么的,哪里像《红楼梦》这么全面。因为曹雪芹是纯粹的艺术家,他穷困潦倒,专门去追求精神的发展,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
臧继贤:如果中国文学再有伟大的作品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再重复曹雪芹的这种方式?
残雪:那不可能了,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需要在曹雪芹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不能创造的话就别搞文学,守成当然也可以搞点通俗的东西,但不创造的话就无法传承传统。文学就是一个硬东西,是试金石。别的东西还可以说不创造,比如手工业等等,但是文学如果不创造,就不能够守成,就会把以前所有的好东西都丢失掉。
臧继贤:有评论说,曹雪芹最在乎的是《红楼梦》里的诗词,希望能够流传下来。
残雪:那肯定流传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看吗?连我以前对《红楼梦》都迷的不得了。
臧继贤: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丢掉了旧体诗。
残雪:用新的形式把它复活嘛,我现在写的小说别人就有说像诗歌的。那种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怎么会丢呢?不可能丢的,但要继续创造它才能够发扬。
臧继贤:那您如何评价现在中国文坛的现状?
残雪:我早就说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也懒得评价了。
臧继贤:那您平时和其他的作家交流多吗?
残雪:没有交流。

1993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首次出版,2004年余华因这部小说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臧继贤:为什么会这样?
残雪:因为我搞的这一套,他们也不欣赏我,我也不欣赏他们那一套。我就写过对几个作家的评论:余华、张小波、梁小斌,就他们几个是我欣赏的,当然他们有的也不再重视文学写作,也出不来更好的作品了。
余华是早期的作家,但他后来转向了。他们后来也写不下去了,就没写。那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任的,但是和大的氛围也有关系嘛,对创新没有任何支持,有时还要打压。
而且那个梁小斌那么苦,大家都为他募捐。你看这个社会都没人管这些人了,所以他没有条件进行创作,社会没有保护他,他就感觉自己的境遇非常惨。连纯文学都不要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
臧继贤:您之前说过中国文坛的氛围不好,讲究“混圈子”,大家都在彼此唱赞歌,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没有这种好的文学批评吗?
残雪:大家都要守旧,不和他们一起被动地回归传统,你就不是他们一伙的。异己就要受到排挤和冷落,然后就没人管,像梁小斌这样的情况就根本没人管。
臧继贤:您为什么说自己的作品是为二三十年后的未来写作的?
残雪:就是为现在的年轻人而写的,过二三十年他们不就老成了吗?就是为这些人写的,还包括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但因为有现代精神的这些人还不太多,我就没有提。
臧继贤:为什么寄希望于年轻人?
残雪:现在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数量比较少,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人,也就是现在20多岁的,再过20年可能就碰到精神上的问题了,物质不能够再满足他们了之后,就会有可能看我的书的,因为我的写作是给人力量,使人独立,塑造人的素质。我这本新书《黑暗地母的礼物》最重视的描写就是人的素质。人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大地上站立起来,他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素质?我做了一些预测,他们说我讲的是乌托邦,但其实也是相当现实的。
臧继贤: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残雪:我现在还没写完手头上的书,所以还在读《存在与虚无》和法国的梅洛·庞蒂,一直在读大哲学家的东西。文学方面在读现在在欧洲比较走红的那个奥地利大作家,叫做罗伯特·穆齐尔。现在我们刚刚翻译了他的作品,在网上有卖。他们翻译成《没有个性的人》,当然我不太同意这个翻译。这是一本很长很长的书,他一直写到死还没写完的书,可能有一千万字吧。我还比较欣赏这本书的上部,它跟我能够合得上,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觉得还不够满足,对人性的描述还可以更进一步。

《没有个性的人》登上了豆瓣“2015年度再版高分图书”榜。
臧继贤:那能不能请您给年轻的读者推荐一些西方文学的作品?
残雪:就是刚才说的那本《没有个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看的是英文的,年轻大学生最好是看英文原文,因为那个翻译我看了几章,我不喜欢,最好是看英文,因为他们都学了英文的嘛,为什么不能看呢?
这本书里面有一点乌托邦的性质,对未来也做了一些预测,他是1940年代才死的。不过还没有像我搞的这样的,就是完全跟现实结合起来。那个年代比我早嘛,现在现实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了:怎么处理你同家里人的关系?你跟你老婆的问题怎么处理?或者你跟女朋友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是很紧迫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交流。交流是一个核心词,新时代的核心词,交流其实就意味着爱,当然也意味着斗争。我这本小说就是专门写这些问题的:什么样的关系能够达到真正的交流。我一方面提出问题,另一方面我也尝试做了一些预测,就是解决问题的预测,所以我这本是实验小说,那里面提出的东西都是实验性的,而且很幽默,跟现实结合得很紧。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