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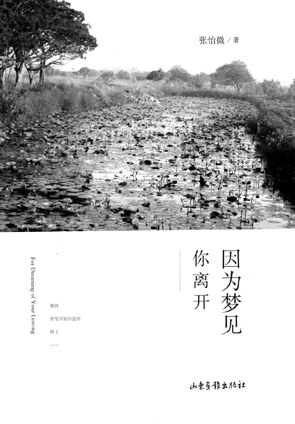
采访者:丁杨
受访者:张怡微
《都是遗风在醉人》里比较多写身边的人。取材是一回事,经验是另一回事。没有什么素材吃紧的问题,类似于画画的人,总能找到取景框,只要世界还在。
在 记录自己赴台湾学习生活见闻、体验、感触的《都是遗风在醉人》出版之前,未及而立的作家张怡微已写作多年,出过好几本书。可是,这本有些“无心插柳”意 味、关于台湾的散文随笔集令张怡微一下子为更多读者关注,这也是她迄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虽然她称该书销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与不少80后作家类似,张怡微的写作之路亦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正式起步。十多年来,她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从上海到台北,她 的写作始终以不紧不慢的从容姿态呈现。《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北文学奖散文首 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是对她写作水准的肯定,不过,她的写作方向与心态没怎么因此波动,甚至认为她 的作品“在台湾并没有读者”。
张怡微在小说里编织着那些发生在上海的、台北的人物身上的故事,沉静、沧桑、与年龄不 太相符的成熟,他们的生活、情感、悲喜看似日常流水般平缓,实则有暗波涌动;另一面的她则属于不时见诸MOOK杂志书、大陆或台湾报刊的有些小清新风范的 专栏,写人或是记事,也有对作家等艺文人士的采访,轻松、文艺、外向。难说哪一面更能代表她,就如同她可以在微博上如邻家姐姐或同窗好友似的与读者互动, 也会在新书《因为梦见你离开》里写下“我是这个城市里的微小糟粕,是地球癌细胞中的一员”、“我原以为台北是我人生里的一鳞半爪,后来才觉醒我对台北来说 连一鳞半爪都不是”这样带有淡淡理性忧伤的句子。很多读者对她写台湾的文章反响强烈,但她更希望能好好写写上海,写写这个自己出生、成长于此的城市,写自 己经历的或父辈、家族的故事。
记者:你的散文随笔基于你的经历、见闻、感悟,而小说也有浓厚的“本色出演”意味,短篇小说集《因为梦见你离开》中大陆赴台年轻人、交换生等人物俨然有你自己的影子,这是你写作的某种优势?
张怡微:写作一定是有自己的经历作为虚构基础,毕竟经验素材都是从中取得。我自认为没什么优势,在城市里的写作者都会面对写作资源匮乏的问题。
记者:读你的文字,偶尔错觉你就是台湾作家,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张怡微:可能只有《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一篇比较像台湾的表达方式,其他其实真的非常大陆。我参加比赛,也常常被一眼认出来是大陆的来稿。地景的确是台湾的。
记者:你写台湾实际上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但这距离感在缩短。几年生活下来,也许你对台湾的熟悉会慢慢大过飞速变化的上海?
张怡微:那不太可能,上海是家,在台湾我只是千万留学生之一。了解的台湾文化也只是皮毛。
记者:《试验》一书收入你两篇写曾经的上海市井生活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这恰恰是两篇非本色写作,人物的身份、生活乃至故事发生的年代都不是你自己的,你如何把握这样的写作,今后会在这样的写作上多着力吗?
张 怡微:在我看来,《试验》是我“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做这个集子很偶然,被抽出来两篇。这应该是一个很大整体,关于我所理解的上海的家庭。我 已经写了十几万字,陆陆续续在发。或者说我一直以来写的都是上海,我写了八本关于上海的书,去了台湾以后才有了两本关于台湾的小集子。
记者:在《因为梦见你离开》里,你把此前已经在很多文字中流露的那种伤感、理性继续发扬光大,你觉得散文随笔里的你和小说背后的你,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你?
张怡微:我写散文,是迫于学费压力。我自己非常不愿意写。以至于现在也写得很少。但台湾实在给了我非常多契机,因缘际会让我写了一些之前很少写的东西。我肯定更喜欢写小说,这是无疑的,虽然也未必写的很好。
记者:“再近的留学,也是一种伦理上的逃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当初去台湾,你觉得你在逃逸什么?
张怡微:去台湾就是因为正好招生,就去了。我是第一批赴台中文博士,同行只有两个人。没有什么主观意图,都是偶然。伦理上的逃逸,无非是家庭里的种种伦理要求。譬如这个年纪应该结婚生子,别人也在结婚生子。我是个掉队的人。
记者:你在《因为梦见你离开》后记里曾经说过,你的很多经历,包括在台湾的师友,都曾被作为素材写进你的作品里,那么遇到过写作素材吃紧的状况吗?怎么解决?
张怡微:《都是遗风在醉人》里比较多写身边的人,现在尽量回避吧。取材是一回事,经验是另一回事。没有什么素材吃紧的问题,类似于画画的人,总能找到取景框,只要世界还在。
记者:和那些浮光掠影写台湾的大陆作者相比,你无论是自身经历还是呈现出来的文字,对于台湾的书写都更加深入、理性,随着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长,对那里的认识越来越多,是否有过以此为题材写作方面的惶惑?
张怡微:我希望少写一写我不了解的事,让了解的人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东西,会比较好。与其说我在写台湾,不如说我是在写在台湾短暂生活过的自己而已。我不肩负写作台湾的任何责任,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
记者:随着《都是遗风在醉人》的出版,越来越多大陆读者开始熟悉你,进而成为你的忠实读者,而近来你接连出版了三本书。就写作这件事而言,应该进入到一个或者说第一个丰收季(成熟季)了?
张 怡微:并没有,我以为“家族试验”系列会成为我的代表作,但现在零零散散发掉了,也很可惜,我只能重起炉灶继续补充新的故事,丰富这个计划。出书的事很偶 然,有时也很无奈。我并没想到《都是遗风在醉人》会成为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只是我的书中最好,都是因缘际会。
记者:去台湾读书之前,那里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来自哪里?你关于台湾的间接了解和想象,与此后实地接触,有怎样的重叠或反差?
张怡微:做交换生时,生活上比较无忧无虑,台湾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读学位比较辛苦,其实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的东西,读书就是读书,就是上课下课写论文发论文。诗情画意都是文字游戏,我住在山里,这是事实,那一定和住在水边的人看到的世界不同,但也仅此而已。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台湾文学对大陆读者的影响一直存在,近些年这种情形尤甚,张大春、朱天文、骆以军等台湾作家在大陆读者特别是文艺青年中颇受认同,而 如舒国治、九把刀等不同年龄层不同写作方向的作者在大陆也不乏知音,于是坊间另一种声音是,大陆出版界和读者对于台湾文学及其作家的认同或追捧有些过热, 对此你怎么看?
张怡微:我觉得文学作品看“眼缘”,写得好的,自然人家就记住了。硬要以区域区隔其实也很粗糙。大陆 人心中的“台湾文学”和台湾人所说的“台湾文学”并不是一件事。很多我们觉得是台湾文学的东西,台湾并不以为属于这个学科。总的来说,台湾文学热只是营销 上的一个现象。
记者:你结识、采访过很多台湾作家,但似乎只说过你是蒋晓云的“一生推”(注:一生对此表示支持、推荐,强调热爱和推崇的程度),她的书虽已在大陆出过两本,但我还是觉得她的知名度和作品水准不成正比,你说说她的小说好在哪里?
张怡微:蒋晓云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这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总的来说我很喜欢她的小说。但有趣的是,台湾人并不以为她是台湾作家。这就是之前所说的学科意识。她是被忽略的、非常有才华的写作者。
记者:在台湾这些年,你以散文随笔或小说来记录、呈现台湾和台湾人的情感与生活,也得了不少奖,甚至吴念真先生曾以你的努力和成绩去勉励台湾年轻作者,你 在《我自己的陌生人》那本书里也有《小说比赛有窍门吗》这样的文章,你是懂得参加文学奖的那类作家吗?你怎么看待吴念真先生对你的称许?
张怡微:我已经没有再参加比赛了。有一年成绩比较好,但评审其实就那么几位,口味也很单一,拿不到奖也不代表什么。我自己对拿奖非常警惕。吴念真是我的老师,给我非常多帮助,也是我很喜欢的导演。
记者:你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也是80后作家群中一员,但这两个曾被广泛用在很多你和同龄作家身上的标签如今似乎不大用了,这或许意味着包括你在内的一批作家的写作随着年龄递增、作品水准渐趋成熟,更加富有个人化气质,无法归类或泛泛地相提并论?
张怡微:“新概念”获奖给我非常大的信心,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写东西。后来开始发表小说,以至于很年轻的时候就出书。但是持续性写作是很艰难的事,这个对每个写作者都差不多。我们还在写作的都在克服,虽然每个人情况很不一样。
记者:和很多同龄作家比,你的文字更理性、从容,对情感有些克制,写生活、写爱情也没那么波澜起伏、荡气回肠,是细水长流的另一重含义上的文艺,能够将之视为你的风格吗?这种风格缘何而来?
张怡微:我也有很华丽的时候,现在不喜欢了,可能就是口味变了吧。写作归根结底是对阅读的模仿,不同时期一定有不同风格,变化也在不知觉中形成。
记者:说说你目前的学习、写作状态吧?考虑过以后的计划吗?
张怡微:有条件的话,就希望一直读读书,写写小说。希望少写一些不想写的东西,完成自己想完成的写作计划。我一直记得普鲁斯特说的,才华好比记忆力,这种东西,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的,所以要争分夺秒的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