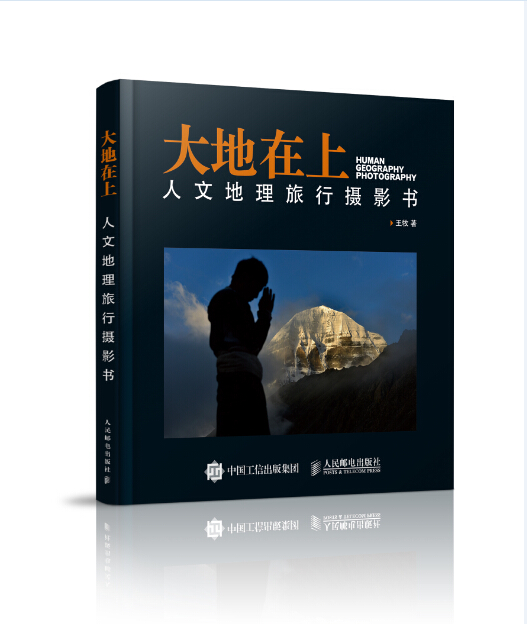采访者:代亚杰
受访者:王牧
‘人文负责情怀,地理负责视野’
记者:您好,您之前曾经说过:“人文是我摄影的底色,地理是我摄影的内容选择。”一句话就概括了一位摄影师的态度,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聊一下人文地理摄影具体是拍摄哪些方面?
人文地理属于人类学的一支,如果把人文和地理分开来看,人文就是负责你深度(情怀),地理负责你的视野。但是让大家说出人文地理摄影的具体概念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个看似狭窄的摄影门类实际上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摄影类别,举凡你能想到的诸如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静物摄影等等门类都可以归入人文地理摄影的范畴。这么解释可能更好:人文地理摄影就像人类学一样综合和包罗万象,拍摄方法上就像是考古或者是田野调查。在观察角度上主要是关注人,人的状态、人的故事,人和历史以及未来,人和自然、土地的关系。
记者:纪实摄影也是以人类学为蓝本,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民族、地理等各种信息体现,那纪实摄影和人文地理摄影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马格南图片社”的那些摄影师虽然到各地去拍照片,但他们照片的人文情怀要强于地理的因素。而以“地理杂志”为代表的人文地理摄影,就要淡化个人情感的投入,具有科普性,把信息传达清楚。
所谓人文情怀,并不是说照片要多么悲天悯人,可能跟你刚开始接触到摄影时受哪位摄影师的影响比较重要。我刚开始受到的影响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马格南图片社”的那些摄影师,他们构建了我的人文底色,一切以人为出发点。第二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德国地理杂志,可以说这本杂志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心向远方。
‘摄影在别处!’
记者:但凡既有个人情怀又有广阔的视野的摄影师,内心深处是不是一直心向远方?在很多人看来人文地理摄影和远方应该是可以划等号的吧。
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叫《摄影在别处》,意思就是只有出去了才愿意拍照。这种心向远方的摄影师刚开始可能就是猎奇,时间长了就是深度的参与。在给我的新书《大地在上》写推荐的两位摄影师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杨延康住在深圳,但从来没拍过深圳的照片,他就是典型的“摄影在别处”。而王福春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任何时候都在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前几年在《炎黄地理》杂志的时候,连着拍了好几年山西,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个比较美好的时候。身边可能也有很多可以拍的题材,只不过我的性格比较喜欢往外跑。
记者:您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炎黄地理》杂志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师,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地理杂志如何完成一个主题?
在做一个专题的时候,摄影师最好要找一个文字记者或这方面的专家一起工作。如果摄影师自己来做这个专题,可能更多的是从视觉上来考虑,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的层面。而“地理杂志”的内容应该像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这样的工作方式一样采集整理各种信息。具体来说,地理杂志做一期地方的专题,首先得满足大众对这个地方的期待,把能代表这个地方的照片要拍到。其次,要拍点别人没想到但又属于这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锦上添花,既满足了人们的期待,又有意料之外。一个地方的专题呈现出来就应该像当地的一个纪录片,记录下当地人和土地的关系,不管是人物面孔也好还是当地的生活方式也好。比如拍一期哈尔滨这个城市如果没有拍到冰雪的内容,那你这个专题就说不过去了。
记者:我们看您的照片在构图和前景的运用上特别精彩,每次在观看取景框里的时候,你会考虑哪些因素?比如是否会有一个提前的预想、观察一下取景框的边缘。
每次在构图的时候,我在取景框里面就把画面给卡死,不给自己留一点剪裁的余地。以前在杂志的时候可能要做跨页印刷,就会避免“公牛眼”构图,如果拍摄的画面里有人物出现,直接下意识的就把人物给挪到旁边去,不管是左边、右边。但是不同的画幅对画面的影响不同,不管是4:3还是36:24的长画幅,都倾向于叙事,而正方形的画幅更有仪式感。现在很多电影都用16:9的画幅,就是因为长方形的画幅更利于讲故事。就像前一段挺火的一个app叫“足迹”,不管你拍摄任何场景,自动给你遮幅成16:9的宽幅,加上字幕马上就像一个电影的画面,试想一下,如果把电影的画幅改成正方形,这个电影还能进行下去吗?如果是用正方形的画幅拍摄宋庄那种地方,这个感觉可能正合适,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记者:提到西藏这个地方恐怕是最受摄影师喜欢的地方,最早的像庄学本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吕楠、杨延康都拍过西藏的作品,您这么多年也不断的去西藏拍摄照片,西藏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摄影师?
大家看到的西藏可能就是西藏的天很蓝,纳木错的风景很美,人们的服饰很有特点,这些都是西藏给你的表象。西藏对于摄影师来说就是一个挺大的陷阱,很容易被光影、服饰这些表象的东西所迷惑。前一段我在看马克.吕布1985年拍的一组彩色的西藏照片,我就拿了一些自己拍的西藏照片和马克.吕布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很多人都区分不开哪张是马克.吕布拍的,哪张是我拍的。马克.吕布在其他地方拍摄的照片,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抓到了当地的精髓,但是在西藏的这组片子就掉到了西藏的表象当中,可能只有一些照片从人们的穿着上能体现出当年的时代感。但是西藏就是不想让你体现出任何时代感,甚至他们文化的宗旨就是前100年和后100年基本一样,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
记者:到过藏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当地人很少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传统。
藏传佛教的文化比较严谨,不会出现特别突兀的东西,但是,青藏铁路可能打破了这几百年的沉静。我第一次去藏区应该是2000年左右,报道青海玉珠峰,2006年左右拍摄青藏铁路的专题时,前后去了六七趟西藏,明显感觉到这条外面突然来的铁路,对西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过一段我可能会总结一下这十年拍摄的藏区,但并不是我拍的多全,比别人拍的好,只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西藏的环境其实很脆弱、很残酷,当地的沙漠化很严重,人口密度又特别低。去年我在阿里地区拍摄了一张小牦牛死后的尸体,被沙子掩埋了一部分,你就能感觉到人对当地环境的一个侵蚀。
记者:正所谓,跳出摄影才能看到摄影师的价值。有些摄影师的作品有时候又突破了摄影的边界,成为社会公共领域的话题,这个时候才更能体现摄影的价值。您在拍摄一组作品、一个选题的时候,是否考虑作品背后的社会价值?
人文地理摄影就是着眼于过去,指向未来,但是表现的是当下。拍了这么多的选题,我觉得一个选题不放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是看不到这个选题真正的价值。在做选题的时候,最好选具有生命力的一些点,比如:一些历史遗产,传统的方式等,这些本身都是经过成百上千年时间的检验,如果你能拍好,那你的选题也能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是,如果把选题就定为新闻性的事件,那很快就会被新的事件淹没,这样的选题就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关于新书,大地为什么在上’
记者:时间也许就是检验一组作品最好的方式。我们来聊聊您的新书吧,这本书取名《大地在上》,这个名字很值得玩味。
这个名字对应的是另外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人对老天、神明的一个崇拜,二、冥冥之中人对土地总是有个牵绊。每个地方的那些人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很密切的依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不管你离开自己的家乡、曾经生活的土地有多远,人在冥冥之中和你生活的土地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比如,我的家在北京,每当离开北京的时候,总是会念着家乡的一些好,这就是土地拴着我的地方。
记者:您之前就出过《312国道私奔书》《108国道自游书》等多部摄影与旅行的图书,这本《大地在上》似乎就是一个扁平化的摄影书,收录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优秀作品。
这里面既有2000年我刚到地理杂志时拍的一些照片,也有一部分我自己旅行时拍摄的照片。可能由于在《炎黄地理》杂志的原因,每到一个地方就想把这个地方带回来的一个使命感。这本书里面的照片都是当时拍摄的大大小小的专题故事里面抽取出来的,是每个专题里面最精华的点,而且又能说一些摄影的技法,算是我这十几年历程的总结吧。这本书在编排上完全是扁平化,不像其他的一些摄影书往往就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本书没有什么前后顺序,随便翻开每一页都可以开始读,每一个章节都是独立的单元,比一个微信文章还要短,比较容易读的下去。
记者:现在回头来看以前的这些照片和当时拍摄时有什么区别吗?
每一次看感觉都不太一样,回头在来审视自己的照片耐看不耐看,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如果还能觉得耐看在往深处去想,拍摄时是不是受到了哪些照片的影响,用这个技法处理是不是合适,这样的话你在拍下一张照片的时候才能熟练掌握摄影语言的使用。
记者:这本书里每个章节的小标题都挺有趣味性,像“自然要用自然光”“热靴是只什么鞋”,是不是特别考虑了现在的一些阅读习惯?
对,就是一个能让人记住的兴趣点,让人在轻松的情境下吸收一些东西。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碎片化呈现信息的方式,这些都是我可能会用的一些招数,也可以说是人文地理摄影师拍照的18个方法,因为我是扔不开这些矫情的词,非得整出18大招来。比如说这两个章节,“创意的布局”和“来堂几何课”这就是讲构图,“创意的布局”讲的是怎么经营一个画面,“来堂几何课”讲的是怎么让你的画面更有形式感,可以说这些章节的设置是潜移默化的讲一个内容。就像这个“漫谈快门”其实是快慢的慢,我是想把这个“慢谈”和“快门”在文字上做一个对比,后来出版社觉得不太合适,就改成了这个“漫”。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