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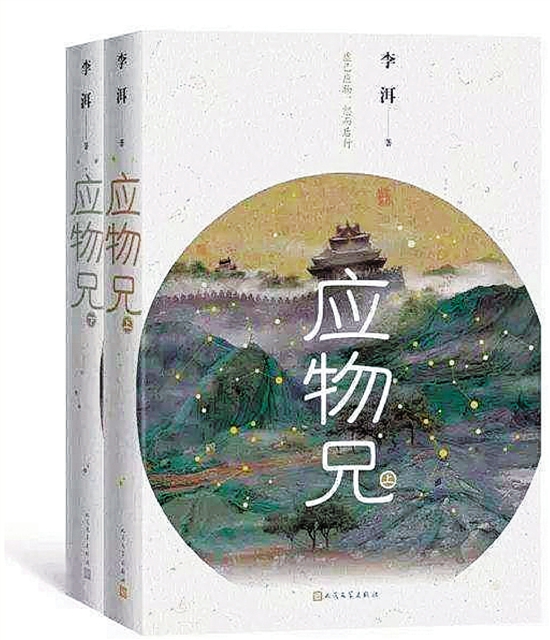
《应物兄》 李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采访者:张瑾华
受访者:李洱
这些年,人们先是知道李洱是《花腔》的作者,后来又知道他写了一部让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喜欢的书,名叫《石榴树上结樱桃》。
在文学圈,人们对李洱一直抱有期待,也有人会有意无意间扩散“中年焦虑”,一个60后作家,再不写出“传世之作”,给自己一个交待,给文学一个交待,是不是快过文学创作的黄金时间了呢?
当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替李洱焦虑时,84.4万字的《应物兄》出版了。为此,李洱写了13年。
“应物兄”能成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符号式人物?李洱说,他说了不算。有些事情,要留给时间来检验。
应物兄能不能成为典型人物,要靠读者读出来,作家说了不算
记者:因为多年没有拿出新作品,听说你遭到了大半个文学圈当面的“调笑”和背后的“嘲讽”。
李洱:你也嘲笑我了吧?嘲笑加同情?这当然是开玩笑了。
其实也有很多人鼓励我,安慰我。格非就当面说过,也托人告诉我:反正已经拖了这么多年了,就不要着急了。毕飞宇对我是既催促又安慰,几次对我说:听着,我告诉你,我相信你。苏童更是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不要怕失败,作家嘛,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怕什么?
坦率地说,我很感动。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您都在写知识分子小说,您笔下的知识分子也从青年时期步入了中年。我看您给知识分子取的名字都特别贴切,我很好奇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
李洱:除了应物兄、乔木、葛道宏、芸娘,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几经变化。程济世先生原来的名字是曾济世。因为“曾”是双音字,我后来就固定为程济世了。给人物起名字,其实就是凭感觉。有的名字,起得比较满意,有的则不大满意。
记者:就书中应物兄等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颓废的、内缩的倾向,我想到了贾平凹的《废都》,当然《应物兄》的时代比《废都》晚了20年左右,您可以说是贾平凹的后辈作家了,两书的地理背景近似,地处中原,有古都的气息,而且你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都有涉及。那么,您和贾平凹着意刻画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同一群人,还是很不同的两批人?
李洱:应物兄们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记者:如果我说,《废都》是写了知识分子的私领域,而《应物兄》主要写了知识分子的公领域,您同意吗?
李洱:你的划分略为简单了一些。儒家的私与公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无论是别人的要求,还是对自己的要求,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记者:鲁迅有阿Q,钱钟书有方鸿渐,王安忆有王琦瑶,都让人印象深刻。在您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中,应物兄这个人是您至今最满意的一次人物塑造吗?应物兄是否是您概括出的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符号式人物?
李洱:你说的那几个人,都已经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家只能出一半力,另一半力是读者出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读者读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作家说了不算的。
中年之后的中国作家,大概都会与《红楼梦》相遇,并对此做出思考
记者:写作13年,几百万字的底稿,最后锁定在84.4万字,在这个您一手建造的乌托邦里,有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而且为了让这个乌托邦更像一个大的江湖,里面还必须有三教九流,这是一开始写就设想好的吗?
李洱:最早只是想写25万字左右,确实没想到要写这么长。小说有自己的意志,小说中的人物也有自己的命运,不是作者完全能掌控的。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就是两个字:准确。你要准确地将人物自身的命运呈现出来。
记者:整本书看下来,我觉得作者挺“坏”的,有时候正着说,有时候反着说,有时正经谈学问,有时又在反讽,在戏谑,最后在庄谐之间摇摆得我也糊涂了,您自己对当代儒学到底持什么态度?
李洱:儒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对此向来尊敬有加。
记者:您的书中,“知一代”整体上有一种正气和脊梁在,比如“济大四老”,作者收起调笑正面地,敬畏地刻画的人物也多;“知二代”,也就是作者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以书中应物兄为代表的似乎在时代巨变中,处于一个摇摆的、粘滞的、彷徨的灰色地带中,不那么勇敢,不那么立场鲜明,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都旋转了起来,似乎有一种困境:不那么自信,又定不了自己的位置;而第三代似乎更外向,也有多种可能性,也有新的希望。
这种感受准确么?关于这三代人,最想让读者读懂的是什么?
李洱:读者应该能感受到,作者其实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啊。
记者:《应物兄》出场的人物,体量可能与《儒林外史》、《围城》甚至《红楼梦》差不多了吧,《儒林外史》写清末儒林圈、《围城》写民国知识分子,您的《应物兄》也通过现代建儒学院的故事衍生出当代知识分子众生相,进而溢出到社会各界,可以说小说题材相近,您写作时有意从这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中进行了某些借鉴吗?
李洱:我承认,那几部作品我都比较熟。但除了《红楼梦》,另外几部作品我都多年没有看过了。无庸讳言,《红楼梦》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对我有影响。同时,我也要承认,托马斯·曼(德国作家)和索尔·贝娄(美国作家,两位作家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对我有影响。或许需要说明一点,总的说来,《应物兄》要处理的问题,与前面提到的作家和作品,是两回事。
记者:您个人这些年的写作,是否有意在从西方先锋派风格向着中国传统如《红楼梦》回归?有个有趣的现象,这几年,看到几位60后著名作家,似乎越来越在意《红楼梦》,也在解读各人心目中的《红楼梦》,我读过您的《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这种向着《红楼梦》方向的转变,是因为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还是这一批作家纷纷人到中年,开始在文化上有了向故土和传统古典文化回归的倾向?
李洱:中国作家,人到中年之后,大概都会与《红楼梦》相遇,并对此做出思考。那个《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做驻校作家时的一个讲稿。香港的学生也喜欢《红楼梦》,他们想让我讲,我就讲了。如果他们让我讲《阿Q正传》,我可能讲得更好。
塑造的光怪陆离是否另有隐喻
“我这个人很老实,写东西的时候比平时还老实”
记者:书里面写到一个亦正亦邪的栾庭玉,很有趣的是他的母亲栾温氏,很像一件旧时代的文物一般,还有妻子豆花,这对婆媳一出场,仿佛把人拉进了旧社会,拉进很古怪扭曲的一个小的场域,这些人物的刻画,是另有隐喻吗?
李洱:没有什么隐喻,就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从小说发生学来讲,小说中的一切人物,都来自生活,都来自生活的启示。
记者:您平时应该会关注各种社会新闻吧。书中有双胞胎姐妹情妇,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他们给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光怪陆离感。您有没有一点私心,就是想告诉读者,作者李洱是个特别有趣、医儒阴阳五行奇门易术啥都懂一点的当代博学杂家呢?
李洱:不光写了动物,还写了很多器物、植物,所谓万物兴焉。你知道,我这个人很老实的,写东西的时候比平时还老实,从来不敢有卖弄的想法。
记者:你写器物、植物时,给人感觉的趣味是雅的,是书宅气。而写动物是蛮野的,是江湖气。
李洱:谁说的?小说的动物,我看挺雅的。比如书中写到的那些狗,不管是纯种还是杂交,都挺雅的。
记者:一开始以为狗会是《应物兄》里的动物1号主角,后来才发现更重要的蝈蝈“济哥”出场了。“济哥”对应着儒学大师程先生的乡愁,也对应着中国式人情关系,“济哥”担负着双重使命,是否也是作者将书中头号大儒程济世先生拉下神坛的工具?济世,他真的可担儒学“济世”吗?
李洱:我没有将程济世拉下神坛的意思。对儒家、儒学家,也不能用“神坛”一词。
记者:有评论者质疑,是否《应物兄》中所有的性话语都有必要。可以说每个作家写小说时都回避不了写性写情的问题,对此,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注:书中,一位教授如此观察校长的女秘书,那个穿着套裙的女人“屁股饱满,裤子绷得很紧,随时都有可能绽开”。主角应物兄看到当地女主持在公交车上的一个广告,在他眼中,她做广告的形态是“傲然挺着自己的乳房、撅着屁股,身子扭成S形”。)
李洱:你说的那篇评论,别人也转给我看了。我首先感谢这位评论家的阅读和阐释。
不过,我愿意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把复杂的话语体系归为“性话语”,那么中外文学史可能就得推翻重写。《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尤利西斯》、《红楼梦》,甚至包括《阿Q正传》,都有性话语过多的嫌疑。
可是,如果你把阿Q跟小尼姑和吴妈的关系,从《阿Q正传》里抽出来,小尼姑和吴妈可能愿意,读者可能不愿意呢。
记者:您对书中的女性人物,似乎比对待书中男性人物多了一点怜悯之心。
打个比方,好像您一边塑造出这些女性——理想女性如陆空谷、芸娘,有缺点的但还算可爱的女性如乔姗姗巫桃朗月,试图多理解一点她们,但又不知该怎么做才可以对她们更好一点,就在一边搓手搓脚,进退两难。我也看到了您对易艺艺、铁梳子等女性的讽刺,您是否对当下女性物化和女性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上持忧患和批判态度?
李洱:我只是应物象形,在写作之前没有想过要刻意去批判或赞美,在写作过程中只想着写得准确一些,再准确一些。毕竟,准确才是作家的第一美德。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