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健
被访者:谢有顺
(一)新诗的资源
记者: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以及美学传统,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后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有顺:这是好事。那时,格律诗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精神价值上,都已呈现格式化、无病呻吟甚至腐朽的本质,新诗不仅反格律,借此恢复长短句的自由形式,它更是对一种有活力、有血肉基础的精神和生活的召唤。
记者: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谢有顺:古诗中的精神可学,尤其诗人与大地的关系,极为重要。但旧体诗的形式已不可能复兴,因为这个形式几乎不可能再表达出现代生活的复杂与丰富。
记者: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有顺: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诗的本质并非格律,而是人的呈现,以及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新诗革命的早期,也有闻一多等人,试图在格律诗与自由诗中寻找平衡,探索二者综合的可能,现在看来也并不成功。格律诗与新诗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任何想再用旧瓶装新酒,都是徒劳的。

(二)新诗的“合法性”
记者:虽然已走过一百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入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
谢有顺:新诗百年的成就是很高的,诞生了不少好的诗人和好的诗歌。古诗在形式上每变化一两个字,比如从五言到七绝,都要历经漫长的时间,而新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才出现百年,就有如此成就,多么了不起啊!那些质疑其合法性的人,估计是不懂诗的。
记者:钱理群大概2006年写道:“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如果钱先生所言不虚的话,新诗写到让专业的文学教授读不懂,反映了什么问题?
谢有顺:读不懂有两种可能,一是诗人确实写得晦涩难懂,二是现代人的经验复杂而幽深,已非几句大白话就可明白无误地表达清楚的,它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探索才能抵达某种精神现实,这个时候,一定程度上的晦涩可能是无奈而必须的选择。卡夫卡的小说并不好懂,毕加索的绘画也非一目了然,但他们的作品意义非凡。对新诗也应作如是理解。
记者:九叶诗人郑敏曾说:“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您认为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
谢有顺:传统是相对的。百年新诗显然已形成自己的小传统,比如新诗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尊重,就是古诗所匮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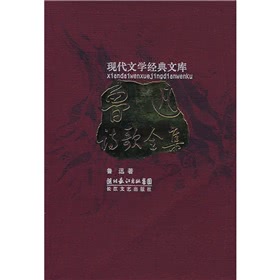
(三)新诗的成绩
记者: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在这一百年里,有哪些诗人、作品、诗论,您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谢有顺:最大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可以和世界各国诗歌有效交流的艺术。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出现,如徐志摩、冯至、穆旦、艾青、北岛、舒婷、昌耀、于坚、欧阳江河、王小妮等人,已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记者:百年新诗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对百年新诗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谢有顺: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百年来,最热闹的可能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却是诗歌。
记者:古人对诗歌的作用有很多论述,有的说是抒发情志,有的说是反映时代,在您看来,诗歌的作用是什么?诗人与时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谢有顺:诗歌最大的作用和意义是不断为语言建立新的标高,要领略语言的结晶状态,理解语言的优美、简约、精粹、凝练、丰富、复杂,最好的方式就是读诗。诗人有一个时代最敏锐的触角,它既表达一个时代,也预言一个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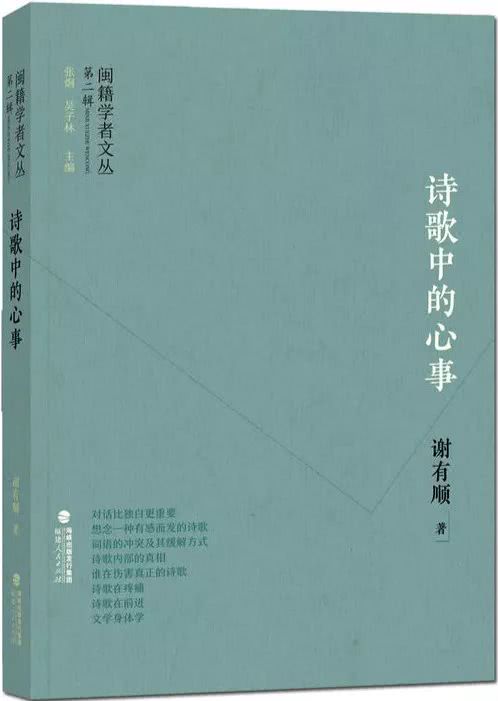
(四)新诗的未来
记者:现在有人认为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也有人说诗歌逐渐回暖,甚至到了“盛唐”的高度,对这种两极化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谢有顺:诗歌在回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的问题也很大,绝对不能说已到“盛唐”的高度,还差得远。不过,诗歌还会大放光芒,前景可期。
记者:现在有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新诗的关注,好像更多是集中在某些具有刺激性的“新闻事件”。诗人的“走红”也似乎往往不在语言之中,而是在语言之外。您能否发表一下对此现象的评论?
谢有顺:这些不过是暂时现象,诗人的立身之本还是要靠诗歌。以诗立世才是诗歌的大道。
记者:您觉得新诗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您对新诗的寄望是什么?
谢有顺: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诗歌也是生命的学问,无论新诗怎么发展,总是围绕着“语言”和“生命”这两个关键词往前走的,除此,都不过是稍纵即逝的语言泡沫而已。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