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者:行超
被访者:阿来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
10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推出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的系列专访。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十月签约作家”阿来,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行超对谈。一起走进作家阿来神秘而独特的文学世界吧。
作家简介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
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阿来是谁?
这个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个深山里走出来的、用汉语写作的康巴汉子,如今就坐在我的面前。初见阿来,看似寡言的他却有一种笃定而坚韧的力量。
“我们”的差异正在变小
行超:您曾说自己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但您的小说没有任何猎奇式的对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呈现,相反,您的作品主题往往指向关乎民族以及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您怎么看待少数民族身份与您的写作的关系?
阿来: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你必然会降生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会有文化,有民族。这当然是先天决定的。但是我们还得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比我们通常说的民族文化更大的东西,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国家和人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有时候过于注重本土文化和民族身份,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有所不足。
当然,我们也说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既要面对个体的人,也是面向全人类的。因此,语言的沟通就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多民族的国家都会有一种官方语言,不然就没有了沟通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汉语是通行的、官方的交流语言。而文学刚好是一个让我们能够互相了解和沟通的很好的工具。我们的语言要有包容性,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也好,那个民族的人也好,但是同时还是中国人。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不只是在跟自己本民族的人交往,而是在跟全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发生不同的交往。所以我们通过文学抒写什么、我们怎么对待语言,这都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事情,不然就会构成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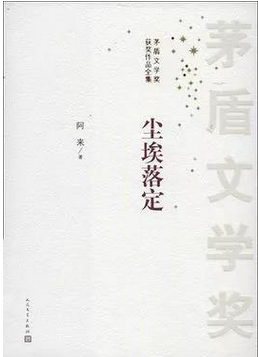
阿来代表作《尘埃落定》
行超:您曾在不同场合谈到马尔克斯、惠特曼、聂鲁达等西方作家对您的影响,不难看出,您对西方现代派、拉美现实主义等写作手法非常熟悉,但同时,这些手法在您的写作中却最终落实于对古老东方故事的讲述。东西文化的对峙与交融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我就认为现在我们有些话或者是有些文学观念,有些时候有一些偏差,就是过于注重地方性跟特殊性。当然文学当中地方性跟特殊性,或者是民族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强调到一个极致,然后认为它是跟人类、跟国家认同没有关系的东西,可能反而就矫枉过正,走到一个比较偏狭的路子上去。有一句听起来非常正确的话,其实它有问题。很多人相信这句话,我是不相信的。这句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容易了,但其实有可能吗?中国民族的东西多了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这么费劲地说“走向世界”干什么?我们剪辫子、穿西服干什么,我们取消裹足干什么?

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在揣摩,别人可能希望看到我们的什么特殊性,好像过去很多文艺作品也在拼命展示这种东西,现在大家慢慢有了反思。同样,中国的少数民族创作也有这个倾向,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我们要给更多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看。他们想看到我们少数民族什么呢?就是想看到那种特殊性。但是有些时候你却发现,真正按照日常生活去写的时候,这个特殊性不够。今天我们正处在国际化和全球化当中,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趋向同质化,而且同质化正在成为今天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流,所以跟100年前相比,可能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作家不应有“门户之见”
行超:《瞻对》在您的创作中应该算是一个异数,这个非虚构作品讲述的是汉藏交会之地的一段特殊历史,但是其中有很多细节非常生动,栩栩如生。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中“虚”与“实”的关系?
阿来:写《瞻对》之前,我本来是先听到一个传说。因为对这个地方和故事感兴趣,我就跑到当地去,算是深入生活吧。到了那里,我想要把所有材料都拿到手,一是当地的各种关于这些战争的民间传说,一个是一些当地藏人记录的、没有发表过的藏文本的记载。这一类的资料并不齐整,比如有一本没有前三页,因为当地人每年都会把它拿出来晒,晒的时候前三页被羊吃了。但是同时,瞻对这个地方,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在清代、在民国时期都是官方很受重视的。尤其是清代,对这里的官方记载很完备。两种记载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民间传说会有点走样,讲故事的人总想耸人听闻,就像民间创作一样,它会变形、会夸张。官方那种档案比较实事求是,只讲客观发生的事件,虽然官方材料很详实,但是民间传说更生动,它有那种带有细节性的东西,当你去揣摩时,就会发现其实创作者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都投注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尤其民间传说文本,对我来说有美学意义,有美学价值,更接近于我们文学创作的方向和追求。而官方史料撑起了基本事实骨架。把这两项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跟过去写作不一样的效果。
但是当我把所有这些材料都收集完的时候,却发现用不着你来编一个故事了。今天我们常说,现实的发展和多变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甚至超越了虚构的小说。在面对“瞻对”的故事和材料时,我体会到我们的文学其实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就是说,你采用什么形式,比如说虚构的小说形式,更富有想象的;或者是采用非虚构的形式,完全依赖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些时候材料不足,或者是材料的精彩程度不够,我们可能就要用想象去弥补。但当材料本身已经非常扎实的时候,确实犯不着再去虚构想象,那样反而画蛇添足。
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注重文学题材上的分别。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写叙事文学的,这个人是写小说的,那个人写散文的,写诗的。在我的文学观念中,我没有一定要写哪种文体,而是要看这个材料适合什么,材料本身会自动选择一种最适合它的题材。当它要求是这样一种题材的时候,我不能强制把它写成另外一种题材。所以我认为,作家不要有那么多“门户之见”,不要被文体所局限。我自己的观念要相对开放。这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从语言开始,就对民族文化保持敞开的态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尽可能地看内容挑选形式,看内容挑选题材。因为一种内容一定有一种最适合它的题材。作家的责任不是创造什么东西,而是当我们拿到材料时,要挑选出一种最适合的题材,挑选出一种最适合的形式。
我愿意做一个有限度的乐观的人
行超:从《尘埃落定》《空山》到《瞻对》,您的作品多是大部头的长篇巨制。近年来,您的创作重心好像转向了中篇作品,比如“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看起来体例变“小”了,但是意义却并不“轻”。真正的转变在于,您此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但这三部作品更切近当下,是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和反思。
阿来:写完《尘埃落地》《空山》《瞻对》,回过头来,我总在思考一些问题,历史还在往前发展,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慢慢发现,当下也有着很多问题,这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就写了一部《格萨尔王》。这些都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我的每一部作品不是想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而是我对于我自己心中迷惑的回答。所以文学也是一个我自己认知世界、认知现实、认识历史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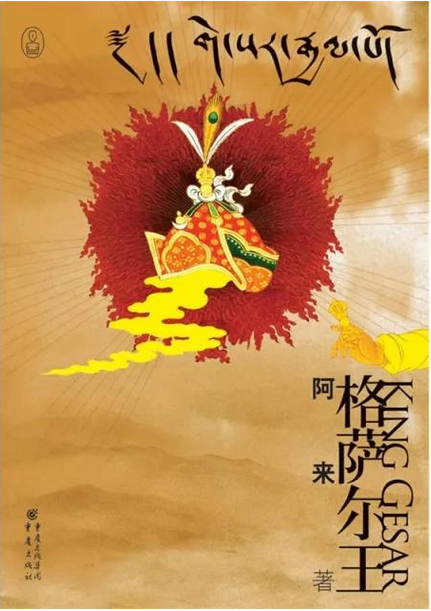
阿来代表作《格萨尔王》
《格萨尔王》完成以后,我就选择了写点短的东西。这之前我已经接连写了几部长的作品,就想要换个节奏。一般你写大长篇的时候,总是特别想在语言形式这些问题上下功夫,但是毕竟体量太庞大了些,不能够面面俱到。小说很多时候是一个形式,短一点的东西不是说不注重内容,它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语言、形式相关,以达到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当下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不算上诗歌跟散文,中国文学中“自然”很少出现。你想想《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基本都是在写人与人的关系,习惯去挖掘人性的恶和卑劣。而在有些西方文学中,虽然也有写人不好的东西,最后会有人性的温暖和人情味。这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当中相对缺乏。在当代文学中,我们写人跟人的关系,很多也是彼此算计、揣摩。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是这样的,作为读者得我不必要了解它,因为我不想了解一个黑暗的世界。

特约记者行超采访十月签约作家阿来
西方文学当中是有自然文学传统的。尤其是美国,有很多自然文学作家,梭罗、惠特曼等等,不是说他们的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思想性很高,我们要吸收这种东西。我去美国的时候,不愿意去那些游客爱去的景点,我就希望能去这些自然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地方去看、去听、去想。
行超:在我看来,您是一个具有悲观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创作之初到现在,一种具有反思、自省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立场在您的写作中一以贯之,不曾改变。在商品经济、消费主义的当下,这种精神显得更加可贵。
阿来: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宿命感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只有几十年,而生命又那么美好,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所以生命本身巨大的悲剧感是无法弥补的。我现在从事文学工作也有几十年了,我想让自己的这几十年生命稍微显得长一点,稍微复杂一点。我从事过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关系,这些都是我扩充自己有限生命的过程。

文学很容易导向愤世嫉俗、孤独、寂寞,诸如此类的情绪,但我觉得如果回到中国古典诗歌、散文的传统中,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健康的、审美的传统。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自然之美的发现,能够使我们稍微有点理想、有点浪漫,我觉得文学就应该保持这种传统。不然老写比较黑暗的那一面,令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本身就失去了价值,只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所以说,我愿意做一个有限度的乐观的人。
关于消费主义的问题,就作家自己来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首先要淡定,要沉得住气。因为文学过去是完全不讲市场的,今天也讲一讲市场。过去我做杂志,我就给我的作者说,市场的事情你就不要考虑了,经常考虑市场其实就是降低了自己。作家需要的是完成作品,而市场反应如何是出版机构所需要考虑的。市场在哪你不知道,谁买你的书你不知道。整天用市场、畅销这些不确定的概念来干扰自己,到最后只会妨碍你的写作。作家一旦去揣摩别人想要什么,这个文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对创作者来说,尽量不要考虑市场。文化是有分工的。出版机构拿到作品之后要知道它的市场在哪里,好的出版就是完成作品跟需求者之间的连接。
十月作家
行超:作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望?下一步有什么相关的写作计划吗?
阿来:作为签约作家基本上已经有了工作安排,明年上半年应该会去爱丁堡的写作基地。爱丁堡这个地方我其实已经去过一次了,它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园。因为我自己对自然有兴趣,所以很想再去待上一段时间。英国人在早年殖民时代把全世界的植物都带回国栽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至少有2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所以,那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上次我去爱丁堡几乎哪都没去,天天在植物园。但是植物是有季节特点的,我上一次去是杜鹃花的季节,那里有全球所有品种的杜鹃花。全世界最好的植物园都在英国,两个在伦敦,一个在爱丁堡。这次去我想多做一些记录,为自己今后的自然文学作品打个基础,写作可能不会那么快,我还希望将来出一些关于自然草木的作品,我已经积累了两三万张照片。

十月作家居住地·爱丁堡
行超:您觉得十月文学院的设立和“北京十月文学月”的策划,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和北京文学具有怎样的意义?
阿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文学机构,比如说我所在的四川也有文学院。但是作家协会主办的机构前期可以进行一些资助和支持,但是在后期的出版上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最多也只能推荐出版,结果怎么样没办法把握。十月文学院是与十月文艺出版社紧密相连的,这就为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发表阵地,而且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全国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我们现在常说文化的要和传播连在一起。一本书在每个书店销售多少,不是作家一个人的问题。

“十月签约作家”阿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开幕式上
行超:最后,请您为十月文学月送上一句祝福。
阿来:希望十月文学院能成功举办各种各样面向社会公众的活动,能够增强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热爱文学的群体,最后在出版方面越做越好。
采访手记
从《尘埃落定》开始,飞扬恣肆的想象力、灵动诗意的文字、带有魔幻色彩又贴身切骨的叙事,让阿来的作品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和难以超越的意义。在交谈中,阿来谦和、沉静,却不时地语出惊人。他敢于打破惯常的说法和思维定势,直面问题、直指要害,更不惧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对抗,他的锐利、坦诚、正直也照亮了他笔下的世界。
采写:行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青年批评家,《文艺报》评论部编辑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