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书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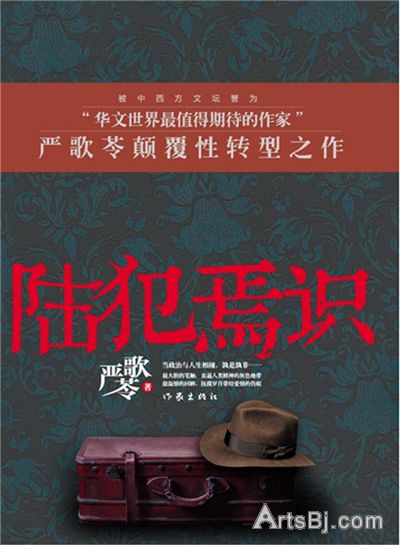
采访者:齐书勤
被访者:严歌苓
从《第九个寡妇》中“像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到《小姨多鹤》中美丽、坚韧、低调的日本女子多鹤,在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中,总会让人感觉到人物塑造的丰满与厚实。日前,严歌苓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是她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重磅作品。记者通过作家出版社采访了严歌苓,她表示,父亲在临终之前一直想让她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把《陆犯焉识》拿给他看,这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遗憾。
初衷 想写关于祖父的小说
记者:小说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严歌苓:《陆犯焉识》是我多年来很想写的一部小说,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通过它来转型。童年时,我的祖父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很“神”的人。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去了他曾经留学的学校,情不自禁地开始了解他、调查他、研究他。直到十几年前,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作品呢?虽然小说主要靠虚构,当然,这部小说的创作也90%是虚构,另外10%,就是我从小到大积累起来对祖父的印象和理解,两者拼凑成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记者:这本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与你之前很多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写人物,就是把他写得丰富独特,这是一个基本创作规律。
记者:在你的作品里,女性都很善良,比如《小姨多鹤》里的“多鹤”,而男性往往有很多弱点,比如《十三钗》里的士兵,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严歌苓:可能跟我自己是女性,我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有关吧。但我对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服气,《红楼梦》里的女性每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每个人都让人爱死了,而男性只有贾宝玉还比较可爱。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和曹雪芹都这么爱女性,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觉得陆焉识有很高贵的人格,有批判精神,他最后能用自己的形式弥补妻子。
记者:听说你整部作品都是用电脑敲出来的?
严歌苓:对,敲了40多万字呢。它是我第一部用电脑打字完成的作品,电脑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脑子里形成的句子和想法不够成熟就用指头打出来,打完之后,就会感觉这怎么和我脑子里想得相差这么远呢,脑子还没传达到就敲出来了,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敲来敲去还是达不到跟在纸上写的一样。虽然我现在打字已经非常快了,但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没有用笔写那么灵敏和准确。[NextPage]
遗憾 无法送给父亲的礼物
记者:小说中的丰富细节是如何得到的?
严歌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长辈们讲家里的亲戚朋友时会说到很多细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我很爱听故事,有时我会追问,他们就会进一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作家,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搜集细节,还要想象,一旦创作出一个人物形象,就要根据这个形象设想他为人处世的细节。所以我觉得想象力是作家首要的素质,如果没有想象力,了解再多细节都是没用的。
记者:《陆犯焉识》中的“犯”是什么意思?是一种隐喻吗?
严歌苓:出身于中国书香家庭的孩子,特别是长子,都是没有什么自由的,这是我的经验。陆焉识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他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被一个无形的枷锁套牢。后来他回忆起在青海时的流放生活,他一步步颠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诠释,但是一辈子他都在渴望自由。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而且他对妻子几度不忠,他有一种负罪心理,所以用“犯”是比较恰当的。
记者:你在写这个故事时有没有什么避讳的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年代,写一个人浪漫,写一个人不忠,很多东西都要用理解的眼光,用宽容的眼光,而不是进行道德评判,这是文学和其他文字形式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非英雄更动人”,浪子回头更动人,人有时候挣脱的实际是挺美好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就会发现原来我错过了。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本想将它献给父亲,爸爸临终之前说,我很想读到你写爷爷的作品,但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勇气拿给他看,我想把这本书印漂亮了捧在手里给他看,没想到他再也看不到了。
纠结 不敢看被翻拍的作品
记者:你的小说文字平实简洁,是不是跟做过编剧有关?
严歌苓:随着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及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过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现在的追求是要把语言和感觉完全写对了。你要诚实地问自己: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如果不是这样想的,就反反复复地改,而不是矫情地让人看你的文字多漂亮,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
记者:如今的影视文学越来越主流,相比之下,文学还有语言优势吗?
严歌苓:当然有,文学要靠影视来展现,但文字的华美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如果一段文字不用似乎、仿佛来体现文字的寓意,而是有本身朴实的意向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高级的文字。影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面临的挑战,因为电影占有的是最最先进的媒体、声音、图像和故事等。
记者:《一个女人的诗史》被搬上荧屏,如今的《陆犯焉识》感觉像是一部男人的史诗,是不是也要搬上荧屏?
严歌苓:是有一些影视公司想跟我谈合作,但这是一个比较难改的故事,时间跨度那么大,剧本不是那么好写的,所以我想再等等。幸运的是,我每部作品出来,很快就有好几家公司找上门来签约,而我的不幸也正在于此,很多作品被买去之后才发现很难拍,不拍了,放那好几年,还有一种就是拍完之后你根本不认识它了,甚至觉得哭笑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好事的背面一定是坏事,没人来买未必是坏事,被人买去了未必是好事,唯一的好事是他给你一笔报酬。
记者:你之前被拍成影视剧的作品,哪一部让你最满意?
严歌苓:我觉得陈冲的《天浴》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天浴》用童话的调子拍了非常苦难的故事,尽管规模非常小。有些翻拍作品我还没看到,比如《幸福来敲门》,有时候不是没有时间看,而是不敢看,感觉会惨不忍睹,有时候过了两三年再看,我反而觉得挺不错的,如果马上看,弄不好就会有心酸抓狂的时候,让人很纠结。
记者:你有没有关注一些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年轻人写作带有时尚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严歌苓: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书,而年龄稍大的人喜欢严肃的文学,和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读书,因此他们搞创作就成了时尚。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