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塞”
如果今天还有什么场景能够让我们更直接的想到无线电广播,也许就只有私人车载广播,并且总伴随着这样的场景:刺眼的夕阳搅扰着驾驶者的视线,车尾红灯迷离成工作日时间最后的尾韵,如同阻碍驾驶者归家的蛛网。在迄今为止最具像的巴洛克思想塑形中,德勒兹在《褶子》中转述了莱布尼茨的“巴洛克之屋”:
“在有窗子的下层和不透光的、密封的、但却可以共振的上层进行着一项伟大的巴洛克式装配工程,上层犹若音乐厅一般将下层的可视运动转换为声音。”
在交通堵塞的黄昏,在挤满了私人密封带窗箱体的城市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巴洛克装配”。
在这样的场景中,视觉联合触觉被封装在一种严格的直观程序之中,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而地面上被切割提炼的一切孤立信息就在空中的无线电波中被予以听觉。有趣的是,我们会想象流畅的驾车体验伴随着在连贯时序上展开的音乐,它可以来自广播但更多的来自数字播放设备。只有在想象交通堵塞的场景中,我们才会想到那些有所组织的广播内容:几公里外的事故,被播报的外部时间,今天的新闻接着一首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歌,来电听众被主持人进行羞辱式劝导的怪异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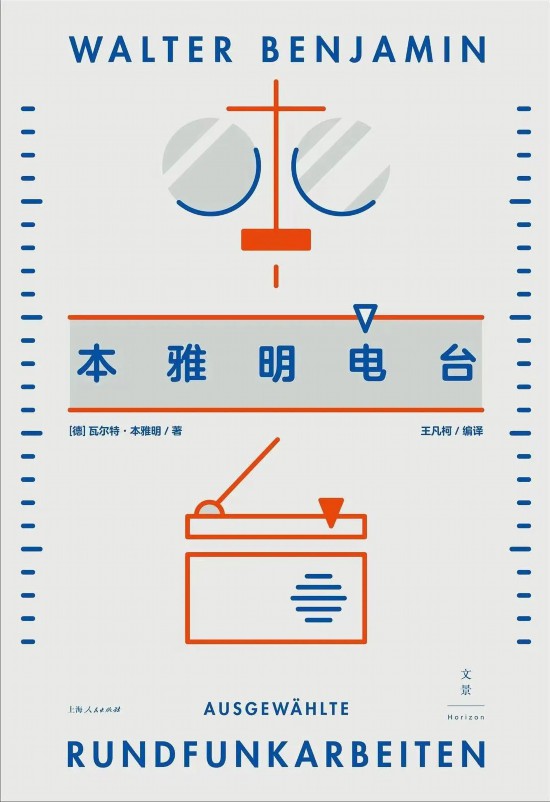
《本雅明电台》[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凡柯 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7
只要稍微带入无线电广播的媒介体验,以及本雅明所处的无线电发展时期,就会知道连贯地阅读《本雅明电台》是多么困难。但在路途上,以断续的方式读完这本书又是多么的自然。《那不勒斯》就是从交通堵塞的体验开始的,而本雅明对这座城市的描画实际上也围绕着密度与数字进行的。“东方三博士“、”七宗罪“对应的城市属性,对店铺的布局数量精确到3以内的估算,本雅明围绕着严格排比及或隐秘或公开的交易行为组织城市的日常。堵塞的隐喻是本雅明广播稿的底色,其中的名词和人物总是被不加事先介绍地密集抛出,只给予后验的解释。在《广州的戏院火灾》中这一点体现的最为明显,本雅明似乎在用行文模仿火灾的物质发生形式,在事无巨细地构建起庞杂的、无法被透视的中国剧场的文化空间之后,用对火灾篇幅极少的描述就将前文付之一炬了。这种体验都与交通堵塞极其相似:除非脱离了拥堵路段,在路段的结尾看到堵塞的肇因,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都市“巴洛克之屋”的下层向无线电的上层,向那个在外部时间中断处重构现实的信息层所转化的东西是否有所印证。
无线电广播天然蕴含着阻塞感,在形式、内容与技术层面均是如此。回到私人车载广播,虽然在1924年,私人车载广播就出现在了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但在FM(短波)技术尚未来临的AM(长波)时代,随便一点发动机静电就能干扰信号的时代,需要高解析度的音乐旋律线无法实现内外时间上的连贯同步。反之,对断续和颗粒感更具容忍度的语音则以“触感”的联觉形式成为了“物”。近年来,“蒸汽波“音乐以一种“故障性”在与车载音响的重新结合中就显现了广播的这一原始特质。
与本雅明著名的概念“灵韵”本就是相机成像时的物质现象一样,广播中的声音成为一种巴洛克要素,即“物”及其“触感”,也本是一种媒介事实。基于听觉中声音触动鼓膜的感受实际上“是一种远距离的触觉”这一看法,在《声的资本主义》中,吉见俊哉例证了上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种对广播的厌恶之心,这是由于这种“二维平面化展示世界的倾向”缺乏场域的承托而显得“无处置放”。作为“可触物”的声音及其信息需要在两种极易沦落的倾向中保留自身:一种是被过于清晰连贯的频率拖入背景乐,一种是沦为噪音。无论哪一种归宿都意味着作为“可触物”的语音将重新被溶解于外部时间之中,不再能够以自身“触动”听众内心的语言的“格式塔”。当播音者自然而然地使用“你们也许知道”作为起语的时候,他就暗示了这种希望被保持的“触动”机制。
“中断”
如果说在本雅明更为人所熟知的媒介问题中,光学的“无意识”在瞬时的图像媒介中分解并重构了现实,那么语音则是重要的后续步骤,它在连贯的历史时间之外继续置放这些现实,所形成的文本更像是一种空间矩阵。本雅明曾把通过广播与听众交谈的自己称为“化学家”,必须准确地测量时间,以期得出“正确的化合物”。
“时间”成为了与“语言”平行的构型材料,这是广播这一媒介真正的秘密。在单向的宣传式的广播中,除了急迫的“现在”这一时间要素之外没有其他时间配方被构入语言。而在广播的交谈之中,“过去”和“未来”均被构入。只有“现在”,也就是正在进行广播的时间,以“中断”的形式涌现。在《剧场与广播》中,本雅明将“中断”论述为史诗剧与蒙太奇的共享原则——爱森斯坦将蒙太奇定义为通过建立冲突空间对艺术中的“物”进行的动态把握——这迫使观众进入一种批判视角。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埃里克·奎因的推理广播剧中著名的“挑战听众”环节就是这种“中断”的范本,它明示了广播蕴含的“阻塞-重构”的现实创构。史诗剧“揭露”条件的任务是通过“中断”完成的,这一行为抵消了作为重构现实之阻碍的戏剧性幻想。这就好像堵车抵消了驾驶者关于现代性无碍流通的戏剧性幻想一样,在科塔萨尔的《南方公路》中,堵车使得人们暂时回到前现代的部落形式。
正如德勒兹否定“巴洛克物质”是完全的流体(一种类似FM技术中的音乐)而应该是具有弹力(一种“强制活力“的表现)的物质,当广播稿被以文本的形式阅读,它应当在阅读体验中保留了耳朵鼓膜的弹性,读者如同在遭遇了一个段落后被弹向另一个段落。在《冷酷的心》这样的童话作品中,读者仿佛就在两个世界(虚构的故事世界和现实的播音室)之间来回撞击,这种体验在《邮票骗局》所构建的在流通中被极端复杂化的“真伪辩证法”里也同样存在。在广播中,时间的先验性
被取消了,仅仅作为一种标识被附加于“物”。并也因此,语音成为了一种触碰,而非一种附着于外部语法的语义流转。
“巴洛克媒介”
将本雅明的广播揭示为一种“巴洛克媒介”,同时意味着本雅明思想中深奥的“巴洛克风格”在广播稿中才得到了最明晰的直接展现,这与学院研究者对本雅明的关注范畴相去甚远。使得“两个本雅明”(学院学术的和大众文化的)之间的某种一致性能够被提炼,让内卷的本雅明研究更为舒展,这也是《本雅明电台》的价值所在。
)才被本雅明用于都市时空的阐释。而早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已经援引“全景式”(panoramatisch)用以说明巴洛克的历史观。以“聚集所有值得纪念之物”的方式,历史被在舞台上“世俗化”,同时导致“无穷小的方法”。在这两个层面上,本雅明指出巴洛克的一个重要运作机制是“时间的运动过程被作为空间图像把握”。
历史时序在一种“中断”或“阻塞”中转化为趋向于“无穷小”的“人类事件”,在悲苦剧论述中令人费解的阐释,在前述本雅明结合广播稿的实践性论述中等到了浅白的明晰。甚至不必再经过复杂理论的过滤,在广播中,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样态。在AM时代的广播技术层面,这甚至就是技术物质在听觉中直接呈现的“微粒”状态。本雅明在《大众普及的两类方式》中表明,仰仗语录摘抄、作品选段和书信断篇的拼凑,或是直接朗读非专为广播媒介而撰写的已有脚本,这两种方法皆不可行,那么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有“直接处理科学性的问题”。“科学性”意味着文本必须在媒介的物质形式中,在被作为构成元素的语音解析度与物质化时间(即广播剧非常依仗的叙事“节奏”)之中找到构成性原则。可见本雅明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寻求技术与文本在物质性上的同构,一种直接的处理和传达的实现。就此,直到80年代,我们才在威廉·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中看到明确的媒介解释。
据此,本雅明的广播何尝不是他所论述的悲苦剧的一种当代形式?在相关论述中,与依照时间的悲剧不同,悲苦剧:
“是在空间的延续中展开的——也可以说是以舞蹈设计的方式展开。其展开的组织者,堪称芭蕾舞蹈大师的先驱,就是阴谋策划者。他作为第三类人物与暴君和受难者并列。”
如果说“暴君”对应着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创作者,将历史进程排列为可度量的空间序列,而受难者则是被动接受这种连续创造的,维持着戏剧性幻想的读者,那么阴谋策划者就是打破“对事件进行规范和定位的秒钟节奏”的人。而这不正是广播者所扮演的角色么?作为“无与伦比的悲苦剧场所”的宫廷,那个计时指针被扰动,时间被阻塞的“无家可归”之所,那个类似于交通堵塞中响着广播的私人驾驶舱的空间,不正是为广播剧带来深度的“表层之所”么?本雅明在《大众普及的两类方式中》写道:
“正如人们平日里能够在咖啡馆、书展博览会、拍卖会以及散步途中听到的那样,这些对话以变化莫测的讨论节奏,穿插着有关诗歌流派、报纸杂志、审查制度、图书交易、青少年教育与借阅图书馆、启蒙运动与愚民政策等主题展开”。
在此,巴洛克就是大众的日常信息交流方式,这一点在本雅明关于“游荡者”的论述中也早有体现。不是“上传下达”,也无关信息实证,公共空间的话语永远只在一种讨论与谋划之中动态地把握现实。本雅明对巴洛克(哪怕只取该词之中的“媚俗”之意)与现代技术手段下催生的大众文化所持的正面态度都最终指向同一个任务,那就是要永远保留对立于连贯历史时间的公共空间,将非辩证的、连贯流畅的历史时间的图像后置于对眼下动态经验机制的观察和构造。堵塞或是中断反而更加促成了经验模式的转型,这也是“辩证意象”的基本形成模式。在《儿童文学》中,本雅明以黑贝尔为范例表明了这种概念呈现的方法:
“在图像中。也就是说,当他讲述故事的时候,犹如一位制表师正向我们展示钟表的内部机械装置,并分别对发条、弹簧和嵌齿轮等部位进行逐一解释。然后,突然之间,他把钟表的另一面翻转过来,好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时间。”
错综的动力元件正如德勒兹在论述巴洛克时候所使用的连续生成的漩涡意向,一旦我们瞪大了眼睛“看入”了这一“谋划”,如同交通堵塞中的驾驶者打开耳朵聆听广播中的信息,那么这个被后置的“图像”,它所表示的时间究竟是这一“谋划”外部对应,还是“谋划”(齿轮动力架构)的自身生成呢?剥去“辩证图像”繁复的考据研究,本雅明无外乎是在提出这一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的提出方式通过最为平实的媒介形式保留了下来。如果日常的“谋划”本性与融入连贯历史时间的安逸不可兼得,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本雅明电台》让我们看到,这一抉择的急迫性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之中。而通过广播声音媒介,本雅明的实践又难免让我们想到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那句著名台词:
“不要怕,这岛上众声喧哗。”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