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1963-),美国小说家,作品风格打破体裁和类型的界限。25岁时出版第一部小说《匹兹堡之谜》。2011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2008年又凭借作品《犹太警察工会》摘得雨果奖。摄影/Benjamin Tice Smith
采访者:柏琳
被访者:迈克尔·夏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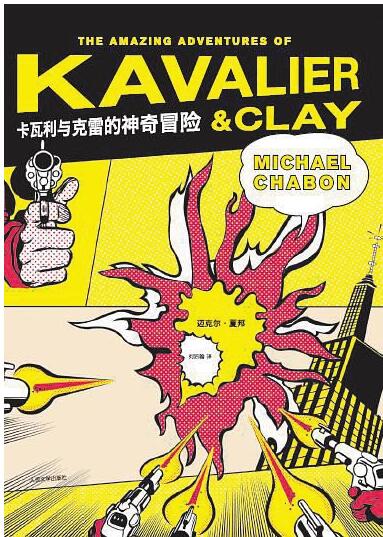
《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 作者:迈克尔·夏邦 译者:刘泗翰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月光狂想曲》 作者:迈克尔·夏邦 译者:孙璐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8年3月
对于1963年出生的美国犹太作家迈克尔·夏邦来说,生活可能是“失重”的。他出生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18年,而从第一代犹太移民来到美利坚的登陆之日算起,也已经产生了从曾祖父到他这第四代人的时间距离。
二战,犹太人,这些主题放到任何虚构或者非虚构的写作中,都能成为深邃的母题,偏偏对于夏邦这样不按牌理出牌的新一代美国小说家,这主题总“隔着一层面纱”。他曾不止一次谈过二战对于他的生活的意义,“二战也许是我整个人生中,唯一一个最具有主导力量的文化主题”,他读一切能读到的关于二战的书,将军的传记,或者战役的记载,却无法进入真正的历史现场。他敏感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却已经无法理解父辈的语言,无法想象希伯来文化的奥秘,他这一代“新犹太人”,处在了一个“想无可想”的尴尬境地。
不过,夏邦依然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的身份部分限制了他的创作领域,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思父辈的遗产,表现一个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作为“异乡人”的精神反思——安全感如何变成了理所当然?《犹太警察工会》或者《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无一不在探索自己的族裔历史。他也会用跨类型的写作方式去映照二战后的精神危机,漫画、科幻、犯罪小说,甚至是“跨”到非虚构领域的“回忆录”,他打破路径的限制,却殊途同归,同样抵达了探寻父辈历史的岸口。
《月光狂想曲》,迈克尔·夏邦最新的小说,表现一个犹太人二战后在美国的生存境遇,“外公的故事”,看似“家史”,实则隐喻一代犹太裔美国人的历史。夏邦在新小说里继续他“跨类型”的风格,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虚构嵌在非虚构中,“我的外公”在生命最后一周倾诉着他的人生,二战阴影挥之不去,太空竞赛从狂热到落寞,“月光”的意象宛若忧郁的叙事面纱。
身份意识
文化断层与无法定义的身份
记者:书里的外公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曾许诺外婆,带她“飞到月球上找个庇护所”,联想到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这是某种寻求应许之地的隐喻吗?
夏邦:所有人都梦想有一个“应许之地”,用以躲避世界对我们的伤害。对于书里的外公而言,他是个美国的犹太人,亲历了二战、数个政治阴谋和抵抗运动,他曾在残酷的战争中体会了苦涩和幻灭。犹太复国的梦想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政治意义上,他绝对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会认为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也因此,他必须自己创造一个避难所。事实上,外公的梦想非常私人化,他无力承受一个宏大的乌托邦,他的乌托邦就藏在他制作的月球基地模型里,里面住着他和外婆,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坐在重力沙发上,外面是种着胡萝卜和玫瑰的花园。
记者:二战后,美国文坛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犹太作家,像索尔·贝娄、JD·塞林格、菲利普·罗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定位和归属。作为新一代美国犹太作家,犹太人的存在问题也一直是你的关注点,比如《犹太警察工会》和这部小说。你这一代犹太作家和前辈相比,生存处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夏邦:美国的犹太人享受了现代犹太历史上相对来说最为繁荣和安定的一段时光。120年前,我的曾祖父来到这块土地,从那以后,美国的犹太人经历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曾间断的进步繁荣的时代,文化信心也增强了,然而这一段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二战前,德国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是不冲突的,二战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这一代,境遇又发生了改变。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把犹太人的安全感当做理所当然——我们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词不能定义我们的身份。然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那辈人却不一样,他们以移民身份来新大陆,大多来自欧洲,有太多痛苦记忆,他们想要割掉过去,融入新社会,热爱棒球,或者爱上可口可乐,总之他们不愿意回想自己的曾经。相比之下,我和我的下一代并非不想回忆,而是说——我们无法进入传统犹太世界,我们不懂意第绪语,也不懂希伯来文化里的秘密,我们想无可想。
记者:你认为有人该为这种“文化断层”负责吗?
夏邦:我依然用“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亲戚,比如曾祖父母或者曾姨妈、叔公等等,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掌握并且热爱意第绪语,然而这些长辈认为小孩子没必要掌握这门语言,于是,当他们讨论一些不想让孩子知道的话题时,就使用意第绪语。上一辈人认为,这种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中有令人羞耻的部分——这是一门关于困苦、关于贫民聚居区、关于他们遭受迫害并逃离旧世界的语言,他们认为这种文化记忆没必要传给下一代。等我再长大一点后,我已经可以听出谁在讲意第绪语了,但我依然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对我这一代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意第绪语是一门关于秘密的语言,我们无能为力了。
叙事界限
一切意义,都取决于描述
记者:我们谈谈《月光狂想曲》的体裁,这是一部小说,但在你的评述里,它是“回忆录”,书的前言里,它是“一堆谎言”。这本书是各种形式的混合,你为何尝试这种“混搭体裁”?
夏邦:这是一本小说,虚构的产物,但它成了某种“事故”,我的本意并非要用“回忆录”的形式来写小说,我本来是想扩展这个故事——写一个我从自己的外公那里听来的、关于他的弟弟被公司辞退的故事。在试图展开时,我把角色换成了外公,因为谁会写一本关于叔公的小说啊?外公才是故事里更亲切更自然的角色,于是故事的叙述就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然后我就一直维持着这种非虚构的腔调,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读着又像虚构又像回忆录的原因。
当你越试图给记忆赋予意义,你就越容易虚构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没有既定的模式,本身也无意义,意义都是描述出来的,取决于我们描述的方式。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读者总是希望从非虚构的作品里得到更真实的东西,事实上,虚构作品往往因为对事件的重组、意义的提炼、经验的重新排序等而获得了某种真实(或者叫做“真理”?)如果只阅读一本回忆录,你可能只获得事件本身。所以,我用“回忆录”的方式写这本小说,也有一点恶作剧的成分——我想幽默地反叛那种“回忆录”的书写定式。
记者:记忆有时候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怎么看待真相与虚构的关系?
夏邦:虚构有一种提炼意义的魔力,非虚构如果想拥有这种魔力,就要说假话才行。虚构可以让记忆更持久,即使记忆出现偏差,它依然有生命力,但非虚构写作想达到这样的状态,要困难得多。
然而,记忆是我最着迷的东西,当我下决心把自己听到的故事虚构化成小说时,我觉得也许适当加入一点真实的细节也不错。所以,我就跑去问我的杰克叔公的女儿弗朗西斯,和她的女儿杰西卡,杰西卡和我是同龄人。我问她们是否还记得杰克叔公被解雇的事情,杰西卡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弗朗西斯说她听到的版本不是“被解雇”。
天啊,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真相?面对真相,我们修订它,用自己的方式把原本无趣的东西变得生动。也许世上本没有真相,或者说,的确存在真相,但我们无从得知它的本来面目。这本《月光狂想曲》就在探索真相如何形成,每个人的真相版本是什么,所见即所得。
记者:你表达过自己对类型小说、流行文化的喜爱,你是否认为文学不应该有严肃和通俗的界限?
夏邦:我不会给文学下一个严肃和通俗的界限。我们所谓的主流的小说就是一种类型。有一种观点让我很不舒服,人们明明从一些优秀的通俗小说里得到了莫大的阅读乐趣,却羞于承认,因为他们被一种“我不该喜欢科幻小说或者奇幻小说”的奇怪观念所左右。
在20世纪,类型小说很长一段时间都声名狼藉,它们被刊载在一些销量很大的通俗杂志上,稿费却低得可怜,而作者需要不停地写,才能维持生计,也许它们中真有一部分质量不尽如人意。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许多大文豪都写过类型小说,往远里追溯,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短篇小说序列里,从莫泊桑、约瑟夫·康拉德到亨利·詹姆斯,那么多大师对哥特小说、恐怖小说、犯罪小说和科幻小说都跃跃欲试。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其类型文学的特性而被长期忽视或贬低。文学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我类型设限。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