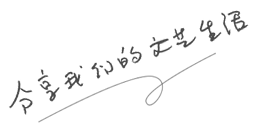有一次笔者跟闵福德先生聊天,他说霍克思在《红楼梦》英译的题目中与读者开了一个小小玩笑,问我看没看出来。我说没有啊,不过愿闻其详。闵先生笑了,他说The Story ofthe Stone这个题目当中暗藏了一个SOS。我当时又惊又喜,惊的是读了这么多年的霍译《石头记》,居然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在题目里跟读者开的玩笑! 喜的是虽说果然被霍氏瞒过,却终于还是明白了这里暗藏的机关。这一点虽极小,却未必有慧眼人能看出,当然这也正是在提醒我,需要更细心地阅读,才能真正明白译者的苦心。难怪霍克思把《楚辞》译作TheSongsoftheSouth,因为那也是SOS啊! 真是“昏昏长夜,得此豁然”。
元代陶宗仪曾在《南村辍耕录》中提到:“乔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致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颇有意思的是,他说的虽然只是写古诗,但我们移来讨论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居然也有暗合相通之处。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中国文学英译矣。
霍克思极其精妙的译文里,常常有些不经意就被我们忽略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往往隐藏着译者试图暗中透露给读者的信息。可以不夸张地说,霍克思这一点是得了曹雪芹的真传。霍克思故意不选《红楼梦》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题名作为他译文的书名,而选相对来说似乎平平无奇的《石头记》,原因有三:一是“红楼梦”这几个字的文化意义很难传达;第二是《石头记》这个书名本身具有多重含义;第三是霍克思跟读者开了个小小玩笑。他的译文,需要有心人才能真正读懂和欣赏。
《红楼梦》这个标题字面本身其实不难翻译,最简单的办法是译成“Red Chamber Dream”,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等译本,都是这么译的。只是霍克思觉得这个题目“所唤起的意象——红色屋子里沉睡的人——令人浮想联翩,充满了魅力与神秘;遗憾的是这并非中文所指的内容。在古时候的中国,有红色外墙的高楼——这正是‘红楼’的字面意思——是富贵与荣华的象征(北京原来的宫殿、庙宇和衙门都是红墙;而普通百姓的住所大部分是灰色的)。但‘红楼’很早就具备另一种更特殊的意思。它被用来特指富家小姐的住所,也可引申为富家小姐本身。”他进一步解释道:“《红楼梦》的爱好者会发现我的翻译中丢失的一种意象是这部中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红’。小说的书名是以红字开头的,‘红’也是其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象征——有时指春天,有时指青年,有时是好运或繁荣。遗憾的是,除了年轻人玫瑰花般的面颊和红色的嘴唇,红在英语里却没有这种联想,而我发现中国的‘红’与英语里的‘金色或绿色’倒是相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但没有翻译“红楼梦”这个题目,而且把“怡红院”译成了“快绿院(House of Green Delights)”。霍氏只是畏难而已吗? 显然不是。
《石头记》这个书名,看似平淡,其实层次十分丰富,至少可以有五种意思(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一共也有五个书名,分别是《石头记》《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情僧录》):第一,作者假托这是刻在一块女娲弃在大荒山无稽崖下的补天石上的故事,所以称“石头记”;第二,作者本人工诗善画,他最喜欢画的题材之一就是石头,所以石头也是作者自况,“石头记”可以理解成是作者本人的传记;第三,这是主人公贾(假)宝玉成长的故事,假宝玉者石头也,“石头记”就是贾宝玉的传记;第四,“石头记”也可以理解成南京的故事,因南京古称金陵,又称石头城,那是作者出生并成长的故乡,虽然小说中总是假托长安、京师,但书名之一《金陵十二钗》显然就直接告诉了读者这部小说发源地的本来面貌——南京;第五,石头上刻着故事,譬如摩崖石刻,藏之名山,方能存之久远,作者用刻着故事的石头为他的家族记忆立了一块丰碑,从此再也不怕被湮没。略早于曹公的郑板桥曾有诗曰:“顽然一块石,卧此苔阶碧;雨露亦不知,霜雪亦不识。园林几盛衰,花树几更易;但问石先生,先生俱记得。”园林盛衰,花树更易,百岁如流,富贵冷灰,一切都转瞬即逝,只有石头能超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死轮回而承载着永恒的记忆。《石头记》之为书名,作者、译者之用心深矣!
不光是题目,小说的开头霍克思也别出心裁。他的译文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一回开头是“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霍克思虽然译了这一段,却把它放在前言里。他的英译本第一回以一个问句开头:“Gentle Read?er, What, you may ask, was the origin of this book?(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霍克思的选择固然是版本校勘的结果,但笔者觉得霍克思最喜欢的书之一——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极有可能是他特别想让读者联想到的。《忧郁的解剖》正文之前有一篇楔子“Democritus Junior to the Reader(小德谟克利特致读者)”,作者假借小德谟克利特的名义给读者解释这部书的由来以及主题。开头就是“Gentle Reader, I presume thou wilt be very inquisitive to know what Anticke or Personate Actor this is, that so insolently intrudes upon this common Theater, to the worlds view, arrogating anoth?er mans name, whence he is,why he doth it, and what he ha?th to say?(列位看官,想必诸位急于知晓眼前这一丑角究竟系谁,假冒他人之名,为博大众关注,擅闯世情剧院,不知他从何处来,为何如此,有何话说?)”根据1998年牛津版第四卷的注释,这里的Anticke指的是滑稽丑角,Personate Actor指的是戴面具的演员。这不正暗合曹公笔下“甄士隐”“贾雨村”的隐喻吗?《红楼梦》通部书讲的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与伯顿假托小德谟克利特如出一辙。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曹公就是在提醒阅者这是小说家言,不必深究,而伯顿在楔子的结尾也说:“let no one take these things to himself, they are all but fiction. (请勿对号入座,本书纯属虚构)”。
当然,霍克思还有可能是在呼应翻译托马斯·穆尔拉丁文原著《乌托邦》的拉尔夫·罗宾逊(Ralph Robinson,1520—1577)。罗宾逊的英译《乌托邦》,早已成为经典。他在1556年修订版的译者前言(The Translator to the Gentle Reader)里说过:“所以现在,最亲爱的读者,拙译的不成熟,以及其中的错误(我想恐怕免不了),我毫不怀疑您在公正地考虑了所有的前提之后,会温和而善意地眨眨眼,假装没有看见。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我想我的劳动与辛苦就都没有白费了。”霍克思在汉英对照本第一卷前言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敢妄称所有地方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能让读者体验到哪怕只是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所获乐趣的一小部分,我也就不虚此生了。”这与罗宾逊的最后一句话十分相似。霍克思的译文开头要传递给读者的,也是与罗宾逊相似的谦逊、热切与自信。
霍克思从《红楼梦》中所得到的乐趣之大,以至于他甘愿辞去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而专心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读者从他的译文中也不难感受到他在翻译过程中的欣喜与愉悦,他的译文感染力极强,既保留了明显的中国特色,又凸显了地道的英文特征。霍克思对译文音、形、义结合的要求之高,全书中随处可见例证,其译文之充实丰满,也可以印证乔氏“猪肚”之说。即便是不懂汉语的英文读者,也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双语对照阅读,可以更清楚地明白译者究竟在哪些地方用心,又是如何在技艺精湛的译文中传递他对原文独到的见解的。
我们最后来看看《红楼梦》英译本的结尾。小说后四十回虽然是闵福德所译,但最后一首收场诗,却是霍克思译的: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When grief for fiction’s idle wordsMore real than human life ap?pears,Reflect that life itself’s a dreamAnd do not mock the reader’s tears.
全书一百二十回皇皇巨著,结尾最后一个字收在tears(眼泪)上。这真如小说中香菱所说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一字有万钧之力,而且回味无穷。中世纪但丁的意大利语名著《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三卷都用stelle(stars)一词结尾。据奥古斯丁说,古罗马人深信以逝者的名字命名天上的星星,相当于把逝者本身升华到天堂的高度。但丁的结尾用词意在呼应古罗马人这一传统,当然也不无对自己的作品能加入这一传统的自信。霍克思曾在给闵福德的信中说:“这部小说用这个字来结尾,还是很恰当的吧?”这说明霍氏比任何译者都更清楚地知道,《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作者用血泪写成的。正如刘知幾在《史通·自序》中说“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作者的苦心孤诣,译者的焚膏继晷,不论古今中外,无疑都是相通的。霍氏的译文要传递给英文读者的,正是曹公所谓的“其中味”。恰如脂批所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所以霍氏的译文,与曹公的原文一样,都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的结果,不曾轻易下一字,需要读者更用心地去涵泳体会,才能不辜负他们的一番心意。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