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学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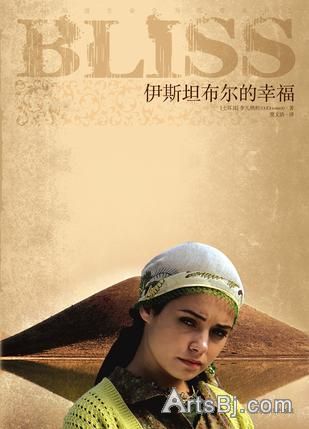
一个人能不能彻底变成另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
伊凡?库鲁达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而这时他正跟一帮喧闹的朋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家小海鲜馆吃饭。有条轮船经过,船上的灯光映在了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玻璃上。虽说春天已经来了,可是要坐在外面还是太冷了,所以里面暖气还开着。
星期天和几个密友吃午饭,坐在海边聊天,喝葡萄酒,这过去一直都是伊凡最喜欢的活动之一。现在听见笑话他也会笑,但是却对这项消遣失去了热情。同一个问题不断在他脑海里回荡——如果他愿意,他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吗?
有人在说笑话。有关东南部的战争笑话近来很流行,伊凡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
“一天,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设了个埋伏,目标是据他们所知每天晚上七点都要经过同一个地点的一队士兵。半个钟头过去了,没有人走进埋伏圈……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没人出现。于是有个游击队员焦虑不安地说:‘咱们那帮小伙子们可别出什么事!’”
每个人都笑了,银行职员米廷,接着又讲起另一个笑话——学库尔德人的腔调,用浓重的鼻音说话。
“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袭击一个村庄,把全村人都杀了,只留了一个老太婆和一个老头儿。有个游击队员拿枪指着老太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法蒂玛穆罕默德的女儿叫法蒂玛。’,不幸的女人回答说。
“游击队员对她说他母亲也叫法蒂玛,所以就不杀她了。
“他又问那个老头:‘你叫什么名字?’
“老头儿吓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我叫奥玛——但是大家都叫我法蒂玛。’”[NextPage]
一圈儿人都给逗得开怀大笑。伊凡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笑话,觉得挺有趣。
战争笑话流行起来之前,关于性的笑话是个始终不变的聊天话题。女人有时候说黄色笑话,不过,要是笑话太淫秽,她们会害羞地停下来,看一眼丈夫让不让她讲下去。要是男人讲这种笑话,就会压低声音,用比喻的方式掩饰那个真实含义。伊凡相信,性,主导着土耳其社会各个阶层的潜意识。
伊凡不善于讲笑话。他一般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强调关键的字眼,也缺乏模仿的才能。但是,他决定给大家讲一个他在美国的时候听到的笑话。
“谁知道那些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是怎么解释世界的意义的?”
“摩西说‘主’。耶稣说‘爱’。马克思说‘钱’。弗洛伊德说‘性’。最后,爱因斯坦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
伊凡的朋友礼貌地笑了笑,又接着说库尔德人的笑话。
灯光在爱奥尼亚有淫荡的意味儿……虽然伊斯坦布尔不是爱奥尼亚,两地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个社会的潜在活力和决定其行为方式的基本动机是性压抑。歌词里含有性暗示的歌手,强调自己性身份的歌手,都很受欢迎。主要的歌手里大部分人都是同性恋,难道这是个巧合吗?甚至在奈玛那个时代,这位伟大的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就曾写道,年轻人男扮女装表演色情舞蹈,勾引年纪大些的男人。
近来,在一份民意调查中,一名同性恋歌手和一名做过变性手术的男性,被选为年度歌手。伊凡研究过的编年史和历史手稿,都表明在奥斯曼帝国男同性恋普遍存在。许多高级官员和知名绅士,都曾出入有男性侍者为其按摩的浴室。有些文本甚至还描述这种活动的规则。
伊凡的研究目的是解读土耳其社会的性行为。他发表的文章总是遭到本专业同行的无情批评。在大学里,活像是在蝎子窝里,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是敌人。许多研究人员都是伊凡的冤家对头,一贯敌视他。他们从来不放弃指责他在文章里用了别人的观点。他们宣称他所钻研的课题之前已经由别人深入研究过了。作为一名没有修过历史的社会学者,他竟敢重复这种陈腐观点,还称之为科学研究!在土耳其,需要泛用“科学”
这个词来守卫自己观点。个人观点没有经过“科学”阐述,就被看做没有价值,除非自己的名字前面有个像样的头衔,如教授、博士、副教授等。这一来,土耳其就产生了了大量的教授,因为只要在大学教书教够一定的年限,就会自动得到这种头衔。
伊凡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揭示过这种教授过多的现象。他指出有些无知的教授连自己的语言也讲不好。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他那些冤家对头立刻群起而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是个骗子,是个吃软饭的家伙,靠他老婆的财产养活。
有时候,在大学里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伊凡会陷入沉思,心里纳闷自己怎么就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他很难理解这种憎恨,但是,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沉思终了时,他总是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没有必要把这事往个人身上扯。在这个国家,人人都互相憎恨。军人鄙夷市民;空军军官鄙视同级陆军军官;政治学系毕业生看不起拿法律学位的;商人讨厌政客,政客厌恶商人;媒体评论员靠推倒偶像博取名声。还有什么地方的报纸专栏像这样充斥着亵渎和谩骂?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盘散沙。他们培育仇恨,话语里充满讥讽、蔑视和恶意。
在近些日子以前,伊凡从来不在乎这些。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是很自然的事,成功必然招致妒忌。但是现在,这里的情形让他感到窒息。他不再想去俱乐部,不再迷恋伊斯坦布尔所谓的名流生活方式。他开始感到无能为力,像开车遇到打滑路段,觉得自己是在空谈,毫无价值,无比懦弱。他曾经感到非常成功地击败对手的方式,那些指责他们无用、脆弱、傲慢、低级或无原则的尖锐话语,那些用以抵御他们的坚甲利器,如今他却用来对付自己。他们是对的。他开始觉得,自己与他曾那样由衷鄙视的人们相比,不过是一丘之貉。[NextPage]
伊凡过去常参加国际会议和论坛,但如今在这种会议上他感到孤立,只呆在一个角落观察别人。他愿意和西方学者谈话,但是话题一旦转到了古希腊或古罗马哲学上,他就会三缄其口。他缺少一种和他们共有的背景。和阿拉伯学者在一起也好不了多少——他也不属于东方世界。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的哲学和科学术语,都没有植根于他的生命之中。他是个肤浅无根文化的受害者,那种文化鄙视不能用只言片语或现成套话表达的概念。
伊凡认为他和所有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一样,是荡秋千的空中飞人,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荡来荡去。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已有千百年历史的“东方社会”于二十年代(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译者注)忽然全盘“西化”之后形成的文化真空中,饱受煎熬。那时,阿拉伯字母也被拉丁字母取代。他就是个荡秋千的艺人,已经松开了东方的秋千把手,却仍然在空中飘荡,没能落在西方的接网上。
伊凡的夜晚充满了恐惧和泪水,他感到已经失去了对他所了解的那个自我的控制。他需要抛开自己的身份,找一个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克服这种已经植入他的肌体,其强烈程度与日俱增的死亡的恐惧。然而,只要他继续生活在象征他归宿的棺材似的家和办公室之间,他就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伊凡扮演不下去丈夫和教授的角色了。就像长睡不醒的恩底弥翁一样,他不得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但是他的命运并不是一个长睡不醒的命运。
伊凡记起了他曾经惊讶地读到过一个文坛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来到他的死敌屠格涅夫面前,说他想对屠格涅夫坦白一件事。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信任,屠格涅夫一时大惑不解。
“我曾经在一个浴缸里诱奸了一个九岁的女孩。”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言不讳地说完,然后便转身离去。
屠格涅夫听了一愣,便问道:“为什么告诉我这事?”
“好让你知道我是多么鄙视你。”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头也没回。
只有大勇者才会这样做,伊凡真希望对自己的敌人也做类似的拜访,但是他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或者哪怕是谎言好讲的。他的“成功故事”实在是不足挂齿。他自己是狗屎,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狗屎。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个垃圾堆,饭馆街上野狗徘徊、垃圾山滋生沼气随时可能爆炸,上面爬满了乞丐和海鸥,夜幕下儿童受欺凌沦为童妓,身穿女人衣服脚蹬高跟鞋的易性癖者手持尖刀抵住出租司机脖子。这里充斥着无知和污秽。伊凡甚至觉得不止是黄金角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海港。的水,就连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都开始腐臭了。在这些臭气熏人地段的饭馆里,他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以为自己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就因为他们出手大方,花几百块吃一顿包括生牛肉片、香蒜沙司、生鱼片,以及取了外国名字的大餐。无论是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是这种虚假不实的生活,都让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想法怎么跟别人说,特别是怎么跟妻子说,实际上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他已经知道阿赛尔的反应了:“你要是情绪低落,我们就去度假。”她会这样说,或者:“我们找个新地方去吃饭。”倒是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此外什么事什么人都不值得多费心思了。
又一次,伊凡想起了希达耶,他驾船出海去看卡瓦非的城市。当年家里送伊凡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希达耶拒绝走这条路,而是选择了扬帆出海,如今竟成了珍贵的记忆。
“我为什么要去伊斯坦布尔学习?”希达耶当年这样问道。
当时两人在伊兹密尔市海关原址上的一家水边小餐馆里,正喝着冰啤酒,一边看着落日把海湾水面染成了红酒的颜色,宛如诗人荷马描绘的景色。[NextPage]
“那不是我的生活,”希达耶接着说,“按部就班,遵守各种限定,死气沉沉。我想要的生活可不是这样。”
“那你想要什么?”伊凡问。
“我不知道,但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你不知道生命会为你带来什么!”
几天后,希达耶驾着自己动手制作的船,扬起一块凑合可用的帆,渐成孤帆远影,消失在了天边的海平线上。海风兴许会把他吹到克里特岛也未可知,要不就是什么不知名的岸边沙滩;也许吧,他已经逐浪随波不知所终了。
伊凡带着与日俱增的怀旧心情,对希达耶思念不已。
(实习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