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学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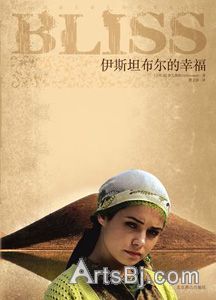
伊斯坦布尔东面九百哩,越过玛丽住的村子七十哩远处,在白雪覆盖的伽巴尔山的一处山坡上的前哨军营里,西玛尔激动得浑身颤抖着从自己的床铺上醒来。
他又梦见了在他的村子里流传了好几代的纯真新娘的故事。在他的梦里,那个纯真的年轻女人看了一眼他身上禁忌之处。接着,西玛尔就向她露出自己的私处,让她用纤柔的双手轻轻抚摸那里,让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虽说纯真新娘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可村里的小伙子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谈论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令人心里发痒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十五岁的女孩,她像家里一朵珍贵的花,养在深闺,避开了所有的邪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父母禁止她和别的小孩玩耍,把她隔离开来,使她无从了解男孩女孩之间可能发生的让人害羞的事。
到她十五岁那年,女孩嫁给了牧羊人哈三,他对新娘的天真无邪十分珍视,决定要让它保持下去。结婚当晚,他对新娘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贞洁的新娘。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纯真的女孩望着丈夫,目光里含着期待。
“我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他说着便把自己的东西露出来给她看。
“噢,天哪,”她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什么?”
“我要给你演示一下它有什么好处,”哈三说罢,就把他全部的私密技巧示范了一夜,一直忙到破晓。从那天以后,他妻子脸上总带着一抹神秘的微笑。她跟谁也没有讲过她男人的秘密,只不过在别人面前时,她会把那种心知肚明、半带嘲讽的目光垂下来。
几年后,哈三要去服兵役。这一分别就是两年,离家前,他搂着妻子告诉她说先停一停,回来后继续。“耐心等着那一天到来。”他说。他走了以后,年轻女人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微笑,眼睛里充满了渴望。“怎么啦?”众人都问她。“没怎么,”她回答说,“就是想哈三了。”[NextPage]
一天午后,正当她漫无目标地闲逛时,她丈夫最好的朋友米哈默德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这么郁闷?”他问道,“男人去当兵的女人又不是就你一个。”
“可是他跟别人不一样。”她叹了口气。
米哈默德追问哈三有什么不一样,她回答说:“他前面有样东西,别的男人都没有。”
米哈默德心想朋友好精明,便诡秘地笑了笑。“我有一样东西差不多哦。”他压低嗓门悄悄说。
哈三的老婆不信他的话,以为他撒谎。米哈默德就把她带到了一块荒野地,在那儿向她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从那天以后,他和纯真新娘夜里无数次秘密幽会,向她一次又一次反复证明。
时间过得飞快,哈三又回到了村里。让他惊讶的是,老婆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哀怨的脸色。他问起缘由时,老婆哭喊道:“你这骗子!你告诉我只有你一个人前面有那怪东西。”
“天哪,”哈三暗自思忖,“我失去了我的纯真新娘!”
他接着问她哪个人还有那怪东西,她就给他讲了米哈默德的事。
哈三感到绝望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又编了一个谎话来挽救自己。“这东西我以前有两个,就给了米哈默德一个。”
一听这话,他老婆突然痛哭失声。“怎么啦?”哈三问道,“你哭什么?”纯真新娘一边痛哭,一边捶打着哈三的肚子:“你为什么要把比较好的那个给他?”
就在故事讲到这地方的时候,西玛尔和村里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狂笑不止,而哈三究竟如何回答他老婆,一直还是个谜。尽管这个故事每天都会重复讲,可是一讲到这儿就会打住。西玛尔让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尤其是在夜里睡梦中,想象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他从来想不出纯真新娘的面容。他能在脑子里呈现的图像唯有她那白皙的皮肤,不过这也足够他满足自己的恶念,消磨时光了。
在哨所里的床铺上,西玛尔艰难地放弃了想象纯真新娘那热情的容颜。他感觉到床单上黏糊糊的湿了一片,想挪开,又犹豫了一下躺着没动,他一时间笼罩在羞愧之中。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光线昏暗,士兵们的呼噜声夹杂着火炉里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此起彼伏。站岗的卫兵不想吵醒熟睡的士兵,就轻轻打开火炉的铁门往里面添了几块劣质炭,那是他从煤堆里找出来的。
一股空荡荡的感觉在西玛尔腹部蔓延开来。他很愿意梦见纯真新娘,愿意顺其自然,把被她激发出的快感进行到底,但是他讨厌这结果。他不得不起身把自己清洗一下。在坠入罪恶的深渊之后,他要按仪式从头到脚把身上每一部分都清洗一遍,才能净化自己。
西玛尔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塑料手表。快到凌晨两点了。一小时后轮到他站岗,洗完后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休息了。假如他允许自己再小睡五分钟,那就更难醒过来了。但是再回到床上舒舒服服蜷缩在被窝里,再一次任由自己去想纯真新娘,想她那蜜色的肌肤,这才更诱人。无论如何,到三点钟,中士就会过来捶打他的肩膀,或者扭他的胳膊扭到快断了才罢休,直到把他立刻弄醒。也许他站完岗以后能找点时间洗一下。[NextPage]
就在西玛尔松懈下来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父亲。他几乎能看到老人那责备的目光,那一双眼睛在头巾下闪烁,手指愤怒地拨动一串念珠。
西玛尔浑身一颤,一阵凉意袭上心头,回想起那种自打儿时起就熟悉了的恐惧,不由得猛醒过来。他几乎向诱惑屈服,做了魔鬼的俘虏。他不仅梦见了纯真新娘,而且还琢磨着敢不做沐浴仪式就接着睡下去。他离打开地狱之门已近在咫尺了。所幸及时想到了父亲,给了他一个警告,他想起了老人的话:“一旦上了魔鬼的当,必须按规定做沐浴仪式,念诵两段祷文,请求真主宽恕。否则……真主禁止……”
有一个长长的描述地狱里各种刑罚的清单会跟在“真主禁止”后面,西玛尔一想到这儿,浑身血液就凉透了。他用不着亲身体验那些刑罚,也理解名叫女人的这种动物有什么欺骗和毁灭的影响。听了父亲的话,足以使他认识到恶魔是如何利用这些懦弱的动物来毁灭世界。
西玛尔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悄悄对他说不妨赌一回——把沐浴一事推迟到黎明再说。
然而不能保证他是不是能活到黎明。要是黎明前哨所遭到攻击怎么办?说不定他站岗时,从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打过来的一颗子弹会击碎他的脑袋。他的好些朋友就是在这种袭击中丢了性命。就在一个星期前,萨里被打死了。不论西玛尔想呆在床铺上不动的意念有多么强烈,他对带着不洁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却更为强烈。
他坐起身来。他的床位是上铺,所以在昏暗的光线下,还是能分辨出熟睡的战友们那些一动不动的身形。有些人睡得简直和死了没两样。还有些侧着睡的,张开嘴巴仰面睡的——正在做梦,咕咕哝哝说梦话,屋子里呼噜声磨牙声响成一片。
士兵们的粗咔叽布料军装在严寒的天气里穿了很多日子,这会儿正搭在火炉边烤着呢,冒着热气,弄得屋里一股酸霉味儿。洗了衣服晾在外面是不可能晾干的。外面天寒地冻,一搭出去立马会冻成冰棍。床单搭出去会冻成一块硬板,像船帆一样在寂静的伽巴尔山里招展。所以士兵们老是把湿床单裹在身上用体温温干。至于羊毛袜子,被漏进靴子里的泥水浸泡得早掉了色,他们一般是睡觉时贴身放进内衣里捂着,到了早晨,袜子就捂干了。
西玛尔从床铺上跳下来,光脚摸索自己那双熟悉的半高筒坚硬靴子。找靴子用不着低头朝床下看,凭脚的直觉就能找到。这双皮靴很沉,由于湿了晾干反复无数遍而变得橡树皮一样坚硬,但它是军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兵们已经习惯了脚下那种冰冷,慢慢透过厚厚的皮革,把腿脚冻得麻木不仁。随后在火炉边暖过来时那种钻心的疼痛,更难忍耐。他们的库尔德工人党对手没有战斗靴,只穿那种薄薄的廉价胶鞋。
士兵们发现,他们在战斗中打死的游击队员,穿的是同一种轻便运动鞋。这鞋在崎岖的山地行走很快捷,却挡不住霜雪严寒。虽然面临各种艰难危险,但生命还在继续,和打死敌人或被敌人打死比起来,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不过,尽管要弄醒屋里这二十几个疲倦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容易,但西玛尔还是尽可能轻轻挪动。他不能肯定他们当中谁能活过明天白天,谁又会死去。明天晚上,有些床铺就会空着,现在床铺的主人就会躺在雪地里流尽鲜血,不是中了枪弹倒下再也起不来,就是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
西玛尔系鞋带时,火炉边那个站岗的士兵用询问的目光瞪着他看。
“我拉肚子。”西玛尔说。士兵们常得这病,原因是太累,或者是饮水有问题。这是个到外面去的适当借口,好过说要去洗淋浴。[NextPage]
西玛尔把军装上衣往身上一披,就穿着内衣和长内裤出去了,粗糙的靴子把光脚磨得生疼。他听见外面狂风怒号,横扫山谷,席卷雪峰,仿佛播放着一曲属于一个无情世界的背景音乐。西玛尔刚来这儿的时候,这种声音让他感到害怕,现在他听了觉得很自然。两年之内,对这荒山野岭非常熟悉,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突击队员。
走廊里冷飕飕的空气吹在皮肤上像刀割一样。他快步走进卫生间。这儿虽然算是房子的主要部分,但是火炉的热力已经过不来了,走廊和卫生间里冷得就像在外面的山里。他冻得浑身打战,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哆哆嗦嗦脱掉内裤,把一半结了冰的水桶倒扣在自己脑袋上。他几乎尖叫起来,感觉好像自己的心脏几乎变成了冰块,但他咬住嘴唇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雾气从他周身飘起来,他顾不上牙齿不停打战,仔仔细细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遍,特别是向诱惑屈服的那一部分。他的牙齿直打战,但良心洁净了。他没有违背他那威严的、荣耀的、受人尊敬的父亲给他的戒律。他避开了罪恶,根据伊斯兰教法律做了该做的,为此感到心满意足。他毫不怀疑父亲是位圣徒:听从他的教导,能保证在今生和来世走向幸福。
西玛尔用自己带来的小毛巾擦干了身体,穿上衣服和靴子,又回到寝室区。刚一开门,他一下就感到置身于一团融融暖意的包围之中。炉旁的哨兵见他头发湿了,冲他笑了一下,不过什么也没说。这事在大伙儿身上都会发生。
西玛尔把湿毛巾铺在自己枕头上,随即爬上床钻进被窝,但他没有办法继续入睡。他想起了前一天他们杀死的三个游击队员。他们是库尔德青年,穿着破旧的衬衫,宽松的布袋裤,脚上穿着胶鞋,在这样的山里,这套行头远远不够。他们面孔的位置裂开了一个大窟窿,是G3子弹的效果。会不会有一颗子弹是从他步枪里飞出去的呢?在小规模冲突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不停开枪,而不问是否命中。谁也不知道致命的子弹来自谁的枪口。如果你真的瞄准了,你可能会知道你把谁放倒了,但西玛尔还没有这样的体验。
他一生中已经有两个年头在这辽阔空旷的大山里度过了,这里成了衡量士兵勇气和怯懦的地方。在爬完长长一段山路的尽头,当他们大汗淋漓站立在一座山峰顶上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就是大山之王——夏天里银波荡漾的河流,翡翠覆盖的山谷,在冬天全都冰封雪飘,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他们装备着精良的武器,身边有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所以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他们在山坡上巡逻,鹰隼般地俯视着下面的大地,哪怕再细微的活动也逃不过他们敏锐目光的侦测。他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进行毁灭,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快感。他们把自己比作神,头顶苍穹,君临天下。
然而山地并非总是如此宽厚。有时走在一片开阔地,士兵们就会处在远处山头的火力范围之内,子弹在大伙儿头顶呼啸而过之际,一股恐惧就会扣紧他们的心——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子弹擦着眉心或脑门飞过,生命悬在生死之间。单独一名的库尔德工人党狙击手就能压制住整个小队,造成重大伤亡。游击队员们配备有狙击步枪,专门瞄准当官的打。有时候,这样一支十到十五人的小分队,会用火箭筒、手榴弹、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对人数更多的部队发起攻击。突击队员在山顶上是主宰,在山顶下是猎物。
在山顶上的那种优越感并不持久,特别是士兵们要在开阔地停留好些天的时候。雨水雪片把他们淋得浑身湿透,他们会忘记什么是干爽的感觉。湿军装到了夜里会结冰,给本来就备受折磨的士兵又雪上加霜。在这种时候,士兵们无不悲观叹息,觉得这辈子雨也不会停了,此生注定要在湿透的尼龙军装里永远浸泡。还有更糟糕的,就是雨声里还夹杂着子弹的呼啸。
西玛尔和许多战友一样,出去执行任务时随身带一个塑料袋。他可不想再体验曾与阿卜杜拉一道经历过的那场噩梦。
阿卜杜拉是尼德市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停地讲笑话逗乐大伙儿,总是笑声爽朗。在他退伍前三个月的一天傍晚,他那个小队在外面巡逻。士兵们知道脚下的雪地里埋有地雷,但是只能冒险朝前走。在雪地里白天发现地雷尚且不容易,更不用说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了。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步,而每次执行任务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就会长长地出一口气。
没有任何声音,只有靴子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打破了寂静。突然,平地一声炸雷炸得地动山摇。士兵们本能地扑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却见阿卜杜拉飞到了空中,他踩上地雷了。[NextPage]
西玛尔离他最近。他向受伤的战友爬过去,虽然这有可能触发另一颗地雷。战友看上去情况不妙。西玛尔抓住他,想把他的头抬起来,放在自己腿上。
“我的眼睛!”阿卜杜拉惊恐万状,尖叫起来,“我眼睛里进东西了!啊,疼死我了!”
他的脸成了一副吓人的惨状,鲜血横流,但是西玛尔强迫自己抓紧他的头,看着他的眼睛。在原本是左眼的位置上,只剩了个空洞洞的眼眶。
阿卜杜拉继续发出虚弱的呻吟声:“好疼,好疼。”
队长和其他队员都围拢来了,西玛尔听见上尉对着无线电话筒怒吼:“老鹰三号,老鹰三号,这儿有个重伤员,派直升机过来。”
刺耳的回答声从另一头传过来。夜色降临。在这个时间飞行非常危险。他们要等到天亮再飞。无线电中的声音异常冷静,仿佛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雪地上有个生命正在渐渐消逝。
鲜血从阿卜杜拉脸上那个大窟窿里喷涌而出。西玛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该不该拿块布塞住那个窟窿?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战友坚持不了多久了。即便直升机马上到,他可能也活不了。
年轻的上尉嗓子都喊哑了,还是不停地请求着,努力说服对方。“求你了,来吧!他挺不到天亮。救救我们勇敢的战友吧。现在还不算黑。”
他接着又把所在位置的坐标报过去。
无线电里没有声音了。
西玛尔看着阿卜杜拉断了脚的残肢,伤口鲜血淋漓。他努力克制心头涌起的恐惧。他看见被炸掉的那节腿就在不远处,炸碎的腿和靴子泡在血泊中,像个陌生的物件。西玛尔唯一的安慰是阿卜杜拉此刻已经失去了知觉,疼得晕过去了。
上尉和士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仿佛祈祷应验了,引擎的轰鸣声和螺旋桨转动声打破了寂静。士兵们一齐仰头张望,一架直升机从附近一道山梁上面出现了。他们开始疯狂地挥手示意,直升机慢慢降低,吹起一阵雪花旋涡。
士兵们知道直升机不会落地,只会悬在离地几呎的高度,他们必须把阿卜杜拉扔进打开的机舱门里。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说不定会看见直升机,开枪打死驾驶员。军队不会容忍对自己不利的宣传,说为了救一名受伤的二等兵,损失了一架黑鹰直升机。机上的军医冲他们大喊,叫他们赶快动手。直升机悬在原地,吹得雪花漫天飞舞,机组人员大声喊话让他们快点儿。不管他们究竟喊的什么话,都被引擎的轰鸣声淹没而分辨不清。
几个士兵从西玛尔怀里把阿卜杜拉抬起来,穿过雪花的旋涡来到直升机跟前。他们把阿卜杜拉瘫软的身体一前一后悠了几下,然后扔向舱门。军医探出身来接人,结果没抓牢,伤员从他们手里滑落,垂直摔到了雪里。这当儿,西玛尔捡起了阿卜杜拉的那只还发热的脚,扔进了机舱。也许到医院还能接回到腿上去。
士兵们再次抬起阿卜杜拉,扔向机舱,但是又一次摔在了地上。第三次才成功,直升机随即升上空中,消失在那道山梁背后,而机上人员还在手忙脚乱地把伤员往里面拉。[NextPage]
西玛尔把阿卜杜拉的脚扔进直升机是出于本能。从那天以后,他巡逻时总要随身携带一个塑料袋。如果另一个战友踩了地雷,他就会用这个塑料袋装身体碎片。他知道别的士兵也要准备这么做。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一边吃罐头食品、罐装茶,一边还享受几根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香烟,他们彼此交谈,往往把内心深处的秘密掏出来同大伙儿分享。说不定到了第二天,昨夜你还向这个人倾诉衷肠,今天却要把他的残肢捡起来,塞进这样一个塑料袋里。
西玛尔彻底沐浴后放松身心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心里又想起用收音机听库尔德工人党广播时常听到的一个声音。他知道那个声音。有时候那个声音会直接请求:“土耳其共和国的士兵们,投降吧,别等到太晚来不及。快点自救吧。把你们的指挥官绑起来,交给我们。否则你们活不到天亮。”
一听到这话,刚到任的预备役军官就会一把抓起无线话筒向对方大吼:“你这混蛋,有种的你自己过来试试!”
对方会发出一阵爆笑,让西玛尔感到不寒而栗。那个笑声他太熟悉了。米摩……他儿时的朋友,他的伙伴,他的兄弟,他的知己,米摩。西玛尔听出了米摩的笑声。小时候在漫长夏日里,西玛尔和米摩一块儿躺在村子里的草地上,望着蓝天上慢慢飘过的一朵朵白云。他俩常幻想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他们俩人愿意一块儿分享,却没想到有一天他俩竟成为殊死相对的敌人,他们怎么会相信呢!然而现在,一个是在土耳其军队战斗的二等兵,一个是投身于库尔德分离运动的游击队员。昔日的老朋友如今在战场殊死搏斗,一心要杀死对方。这种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战斗已经超过了十五年。双方战死的人员已经超过了三万,包括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有些来自东安纳托利亚来军队服役的年轻人,后来也像西玛尔一样驻守山区了,另一些人,像米摩,加入了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对土耳其军队作战。
西玛尔一边听着米摩在收音机里发出的嘶哑声音,一边心里不能确定,如果在这一带山里相遇,他能不能举枪瞄准米摩把他击毙。
(实习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