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学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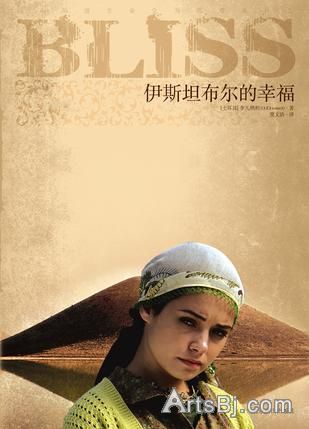
在凡湖水边那个尘土飞扬的村子里,玛丽陷入忧思的这一刻,远在向西七百多里外,位于亚洲和欧洲交汇处的伊斯坦布尔城里,一个有着“伊凡?库鲁达教授”这样响亮头衔的男人,在睡梦中大叫一声猛醒过来。这位四十四岁的教授知道自己才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最近他有了个习惯,睡着后不久就会惊醒。
他从没有失眠过,也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日常习惯——一过午夜就上床睡觉,轻而易举便沉入梦乡。可是过去两个月的每个夜晚他都会惊醒,并带着相同的恐怖感觉,好像有一只黑鸟在他胸腔里振翅欲飞。这个不祥的幻觉令他心惊胆战。他试过好几种治疗方法,甚至求助于烈酒,然而却毫无起色。
他以前一直睡得很沉,一觉睡到早上八点,神清气爽地开始新的一天,如今他却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不管他怎么努力,一旦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从各方面看,教授似乎都没有问题:他有个美貌的妻子,在大学里受人尊敬,以评论员的身份在电视上频频露面,连主持人都毕恭毕敬地倾听他的言谈。他以前也上过电视,不过目前固定每周上一次谈话节目。从杂货店的老板到街上的过路人,几乎都认识他了。没有人在看过这位高大英俊的男子后会忘记他的相貌,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灰白色的胡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没人会忽视这位教授。
伊凡一动不动躺在沉闷的卧室里,花园里的灯透进来微弱的亮光。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不想惊醒他的妻子。他知道自己不靠药物无法克服恐惧。
他起身轻手轻脚走进私人浴室,打开灯,灯光把里面那些昂贵的卫浴设备和斑岩大理石地板照得通亮。他坐在浴缸边上,开始习惯性地一前一后摇晃起来。
“你是个健康人……一切都很好,”他自言自语,“别害怕。这是你家。你的名字叫伊凡?库鲁达。在你床上的女人是你老婆阿赛尔。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今晚在四季酒店,你和妹夫塞达特还有他老婆伊拉尔,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寿司好极了,别担心。你喝了两瓶凉啤酒。晚饭后,塞达特用他的路虎送你回家。你看了一眼电视上的闲聊节目,和往常一样,愉快地欣赏那些长腿大波的年轻模特。你知道阿赛尔不在乎。她不会关注这些事。没有理由害怕。”[NextPage]
然而,恐惧依旧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仿佛他不再是伊凡?库鲁达教授了;仿佛有别的人住进了他的体内。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一直从外部观察自己。
他曾经梦见去医院探访一位病人。在梦里,他进了病人的病房,在花瓶里插了一束鲜花,然后在床脚坐下来。病人穿着睡衣,坐在床上面对着他。伊凡注视着他,发现他就是自己。他,伊凡?库鲁达,在看望自己。坐在他对面正在做梦的人,不是病人伊凡,而是访客伊凡。两人相对无语。他久久凝视着他那张苍白而布满病容的脸。
慢慢地,在病人身旁又有另一个身影渐渐现形,梦中的伊凡开始颤抖、出汗。这个渐渐现形的身影和那个已经在病床上的伊凡?库鲁达一模一样。现在床上有两个人,另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三个伊凡?库鲁达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接着,床上的两个伊凡?库鲁达一块儿向右边扭头,动作缓慢,整齐协调,展示出他们的侧面。伊凡感到脊梁骨自上而下打了一个寒战;眼前的两张脸开始碎掉。一点一点,脸颊、嘴巴、下巴、额头依次塌陷掉落。眼睛是最后消失的。那一刻,教授开始尖叫,他的妻子用胳膊肘顶了顶他,把他弄醒了。他为此一直对老婆心存感激。
阿赛尔睡觉向来很安静,几乎听不到她喘气的声音。他很幸运,自己睡觉鼾声如雷。有时候早上醒来,瞟一眼阿赛尔的面孔,伊凡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瞧,这是你老婆。你老婆阿赛尔。”
阿赛尔的鼻子做过手术,不过这是她那张完美的面孔上所做过的唯一校正。在他们的熟人圈里,像她这样整容手术做得这么少的女人可是绝无仅有的。
阿赛尔做健美操锻炼身体,保持体型,每周做六次,一直没有让自己的身体松弛下来。坚持锻炼,外加最新的健康食谱以及减肥药,使她免除了去做吸脂手术的麻烦。而她也很幸运:一位有名的巴西外科大夫,来过伊斯坦布尔为几个知名女人做手术,就是这位名医给她做了鼻梁整容。医生是个专家,技术精湛,因而她术后没太受罪,只是皮肤有点变色,鼻子和眼睛周围有点肿,不过几周之后就全好了。她有些朋友就没这么幸运了,反而弄得鼻子不像鼻子,嘴唇肿得老厚,呼吸都困难了。有几个更惨的连鼻子都快整没了。
“瞧,这是你老婆。你自己的爱妻!没有理由害怕。”伊凡对自己说。
阿赛尔是一位富豪船主的女儿,不需要伊凡供养。不过近些年来,教授的收入持续增长,这来自妹夫给他安排的各种电视节目。每个星期,他都要面对镜头和一些朋友谈话,这活动每个月都为他带来滚滚财源。钱多得花不完,他就把结余下来的存进银行,账户上的数目不断增长。
他的朋友有买了土耳其里拉国库券的,遇到经济危机就赚得更多,要比投资美元多赚将近百分之五十。有人也在股市赚了,但是伊凡不碰这类赌博。他是个学者、教师,不是股票经纪人,不过要是银行给高利率,不抓住这机会就傻了。
伊凡对钱的态度让他妹夫塞达特很恼火,在饭桌上谈起生意经的时候,他常说只要多留点意,就能把他赚的钱翻上五到十倍。教授就是不听。
伊凡和阿赛尔常在外面吃饭,喜欢伊斯坦布尔名流出入的新潮美食馆。这些饭店有的和他夫妇在纽约光顾的饭店没什么太大区别,夫妇俩每年都要去一次纽约。最近,他们老去一家名叫禅伽的有着极简装潢风格的复合式餐厅。纸月亮曾是个挺火的去处,但是库鲁达这圈人后来不常去了,说它变得“太拥挤、太一般了”。他们也很少去博斯普鲁斯海鲜大酒店,他们喜欢生鱼片和寿司,胜过了传统的青鱼和大比目鱼。[NextPage]
“我是幸福的,”伊凡?库鲁达说,这时他正独自坐在自己的卫生间里。“我太幸福了。”他又重复了一遍——说罢却呜呜哭了起来。
阿赛尔送给他的那些书,倡导主动思考的益处。东方智慧如佛教禅宗、道家哲学全都宣扬同一个理念:“让生活像河流一样流动;心态积极则一切积极;世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就是消极思维。”
阿赛尔从高中毕业后上了博斯普鲁斯大学,毕业后又在波士顿修了一门课程并在那儿遇见伊凡,当时伊凡是哈佛拿奖学金的学生。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还从来没有工作过。
伊凡和阿赛尔回国后在伊斯坦布尔安了家,这里曾经是古代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他们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伊斯坦布尔这样充满生气”,于是开始花时间享受这个城市给予的快乐。大都市的活力令他们激动,伊凡惊异于不断发展出的城市周围地区的居民区那勃发的生机。他常常注意到,这方面和纽约有一拼。即便是看上去满眼凄凉的贫民区,实际上也充满了勃勃生机。贫民区在伊斯坦布尔郊区雨后春笋般大片出现,成为来自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的数百万移民的安身之所。有人在这一带的一个街区开了家餐馆,取名叫“好伙计”,搞得这地方和纽约郊区简直毫无二致。
伊凡的姐夫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常常发表高论说,一个城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凶杀案才能算作大都市。“伊斯坦布尔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他总是这么说,“就差这一点了。”
伊斯坦布尔没有像欧洲其他城市那样有序地发展。它和纽约相像,居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穷富雅俗,无所不包。也有来自非洲的移民,伊斯坦布尔不缺少黑人居民。
伊凡觉得这个城市聚集了全国的精华,他本人就是最有学问、最受尊敬、最成功的居民之一。他和那些新贵们不一样,他有时间就读书、看展览,要不就去露天剧场或者是圣爱伦大教堂听音乐会——世界著名乐团和歌手举办的各种音乐会。
他喜欢在让—皮埃尔?拉姆帕尔(译者注:拉姆帕尔(1922-2000),法国长笛演奏家。)的长笛乐曲声中醒过来,他还喜欢一边听这支乐曲,一边在泳池游上半个小时来开始一天。阿赛尔不怎么喜欢古典音乐,不过她假装能分享丈夫的品味。他们也赶时髦。晚上偶尔去城里的著名夜总会听听同性恋歌手和异性模仿癖歌手唱的阿拉伯曲调,给他的文化生活添上一些本地色彩。伊凡觉得自己在东方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东方人,他对自己的这种感觉沾沾自喜。他并不势利,从不鄙视通俗文化。
去年,有个朋友为寻开心,在“东方俱乐部”庆祝他的生日,伊凡在那儿被领进了一个新世界。几个肥胖的同性恋歌手穿着“第三性”的服装,趾高气扬地站在桌子上,招呼大家都爬上桌子和她们一块儿跳肚皮舞。不久,大部分女人就都上了桌子一块儿跳起来了,踏着鼓点扭动腰肢,而男人们一个个呆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看着阿赛尔在桌子上放肆地跳舞,汗流满面,伊凡不禁沉思起一个问题,他的圈子里的这帮人在性方面的能量已经在一些礼仪的净化中被释放掉了,如同一种发泄。一般说来,周围的男人们要是用色迷迷的眼神看别人的老婆,彼此就会大打出手,但是在这里,男人们看着自己半裸的女人以性感的舞姿挑逗别的男人,却感到悠然自得。诚如《希腊左巴》一书的作者卡赞扎基斯(译者注:卡赞扎基斯(1885-1957),希腊作家,作品包括《希腊左巴》和史诗《奥德赛续集》。)所言:“灯火在希腊是神圣的,在爱奥尼亚爱奥尼亚: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爱琴海岸的一个地区,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希腊人曾在此建立殖民地。是淫荡的。”这地方有一种用双手拍打的手鼓,叫达布卡鼓,此地所特有,可以打出古意绵绵的声响和节奏,并使人陷入一种癫狂状态,即便是最冷漠最保守的人也会被唤起来加入那令人意醉神迷的舞蹈。
“一种集体意识中的节奏对一个国家比国旗意义更大。”伊凡暗自思忖。不是曲调而是节奏——区分了不同的文化。[NextPage]
他曾经在纽约时代广场维京唱片城音乐部实地考察过自己的理论。在那里,顾客头戴耳机试听新出的音乐光盘。这里按音乐分区,分为爵士乐、古典音乐、非洲音乐、中东音乐、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到处是头戴耳机、不停晃动身体各个部位的顾客。爵士乐爱好者会微微弓起腰,两脚随着持续的节奏敲打节拍;拉丁音乐迷不停地摆动臀部,而沉浸在中东音乐里的人则扭摆着他们的肚子。观察他们的无声舞蹈真是有意思。
伊凡打开自己的药盒,从无数种药品里挑出了一瓶思诺思安眠药,这药至少能帮他安睡一会儿。他为自己突然涌出的泪水感到震撼,这一次和过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严重。所幸阿赛尔没醒,没有目睹这艰难的一刻。他不可能把自己都不理解的那种恐惧解释清楚。
难道他真的无法理解这种恐惧的理由?难道他不知道原因?“别欺骗自己了。”他告诫自己。
阿赛尔一定会建议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去找个心理医生。“听听专家的意见,你会感觉好得多。他们毕竟是干那一行的。”这些话和其他类似的老生常谈也就是她能给出的建议了。
但是伊凡早就知道心理医生会得出什么结论来。
教授的绝望并非来自对自身问题的不了解,而恰恰是由于他太清楚问题的症结了。他曾经努力理解自己的情况,终于在读了一本书后完全明白了,这本书叫《沉睡的恩底弥翁》。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个牧童叫恩底弥翁,因为和一位女神恋爱而惹怒了众神,众神判他选择自己的命运。他难以承受这种惩罚,便选择了永远年轻,但永远沉睡,直到时间终结。
伊凡看了这本书以后,认识到他自己也和恩底弥翁一样,因为察觉到自己未来的命运而感到恐惧。一个人的命运应该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坚强到能够准确无误地了解生命的全部安排,包括何时会发生意外,或是死神会以何种模样到来。
这种想法彻底颠覆了伊凡对生命中所有曾被他视为牢不可破的事物所抱有的信念,如今这些事物都变成了绳索勒紧了他。他知道自己还会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坐在同一张椅子里看电视,在同样的饭店里吃饭,和同样的人见面,说同样的话……直到有一天,一辆救护车会载着他,驶过他每天走的街道,把他送到他经常光顾的同一家医院,他会在那儿一命呜呼。或者,没准儿来不及到医院,他就突然瘫倒,气息全无,死在了邓禄普软床上,或是罗塞特摇椅里。这些名牌家具是他和阿赛尔一块儿兴致勃勃地挑选来的,它们再也不是让他感到舒服喜悦的家具了,而似乎变成了临时棺材。他爱阿赛尔,那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无法忍受生命不可避免的千篇一律。
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他遇到一位加拿大教授,这位女学者介绍给他一种心灵转变的概念,这竟成了他头脑里的一座灯塔,其功效仿佛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灯塔给予水手的希望一样。心灵转变的意思是“超越自我,进入另一种存在”。其核心是“自我”这一观念。
在任何情况下,自我这一概念总是问题的所在,“我”、“自我”、“我自己”究竟是指什么?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的名字足以让人感到和自我分离。但是人又怎能和与生俱来、相伴到死的自我分道扬镳、与其“身份”形成异化呢?
教授越是思考这些问题,他就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异化的绝对意义上生活着的。就是这种社会和物质世界的规则保护我们免遭疏离流散。我们一旦偏离方向,就会重回轨迹,沉入温暖舒适、习以为常的水域。毕竟,我们的向导就是自己老坐的安乐椅那熟悉的舒适感,闭上眼睛也能拧开的水龙头,以及睡醒时脑袋留在枕头上的压痕。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与狗并无二致,狗在树下撒尿圈定自己的地盘,为的是在散发着自己气味的疆界里感到安全。对人类而言,熟悉的感觉和物品构成了满足的关键。[NextPage]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描述自己离开欧洲返回俄罗斯:“就像你穿上自己的旧拖鞋。”把脚伸进卧室里的旧拖鞋——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这就是人们生活的方式。如果人们在他们自己熟悉的世界里感到不安,那就像是个在地窖里长大的孩子,突然被丢到了一个公共广场。伊凡渴望挣脱备受约束和令人疲倦的安全生活,它在幸福的伪装下,简直要把他吞没了。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改变自己。一生至少应该经历一次个人的心灵转变。
思诺思安眠药开始发挥效力了。伊凡的眼皮开始垂下,意识渐渐模糊。在灯光昏暗的卧室里,阿赛尔像往常一样睡得很安静,仿佛一具尸体,一条腿伸到了被子外边。
教授轻手轻脚回到床上,脑袋枕在枕头上。睡着之前眼前的最后一个景象是两个年轻人和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他站在海岸边极目远眺,地平线上一条船的剪影渐渐隐没,那条船载着他的朋友希达耶到亚历山大,去探访诗人卡瓦菲(译者注:卡瓦菲 1863-1933),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诗风简约,集客观性、戏剧性和教谕性于一身。)所在的城市。
“希达耶到目的地了吗?”他心里问道。说不定他在哪儿停下来不走了,就在那儿安顿下来开始另一种生活。也没准儿遇上了天神宙斯吹下来的顶风,掀起巨浪把他的小船吞噬了。
“再见,希达耶,”伊凡嗫嚅着。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还是摆不脱那个走向死亡的恐惧,知道自己命运的恐惧。
(实习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