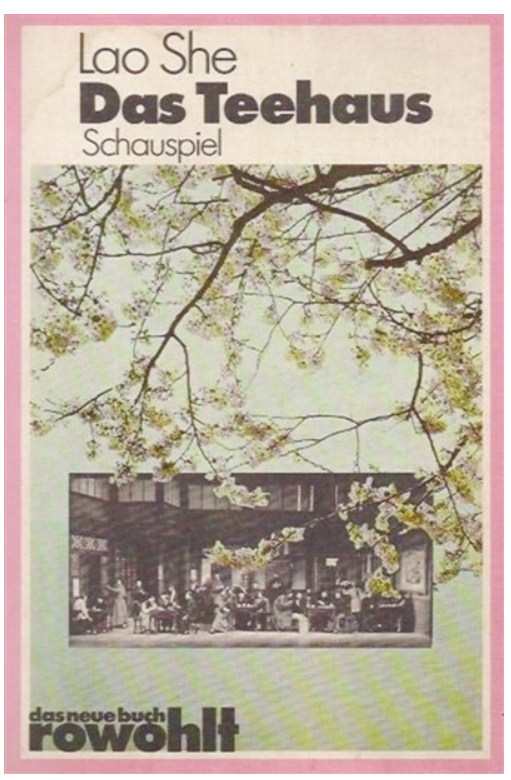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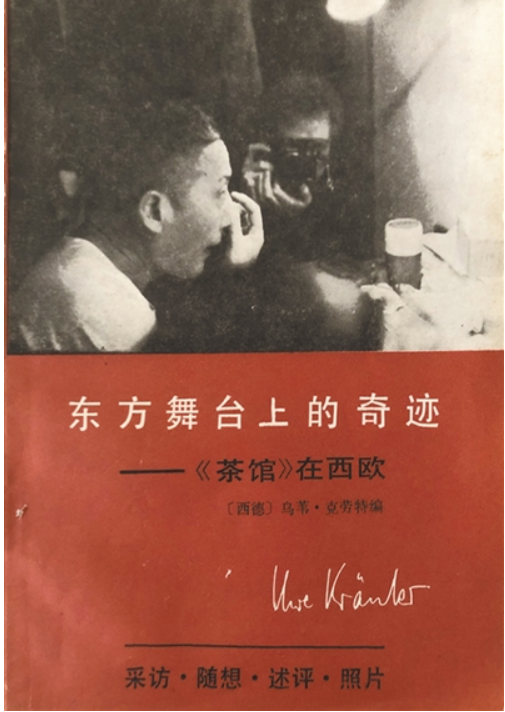

不久前,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中国导演孟京辉执导的话剧《茶馆》成功上演,这是该戏剧节举办73年来,首部入围核心单元的中国当代戏剧。然而对《茶馆》而言,却并非首次欧洲之旅。
2019年,已是《茶馆》在欧“开张”的第四十个年头。这与一个德国人有关——乌苇·克劳特。正是这位德国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西方几代观众得以领略中国《茶馆》里的百味人生。
时间回到1979年7月,德国《曼海姆晨报》刊登了一封来信,引起了不小的动静。这是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北京人艺)时任院长曹禺,在20天前写给曼海姆民族剧院的。他在信中说,中国话剧《茶馆》将赴曼海姆演出,同时曼海姆民族剧院也将应邀赴华演出。
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演出必将震动德国舞台。”《曼海姆晨报》这样评论。
1980年9月至11月,话剧《茶馆》先后在曼海姆、汉堡等11个德国城市巡演,之后又赴法国和瑞士。历时50天,上演25场,《茶馆》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反响,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
今天,已是满头华发的乌苇·克劳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充满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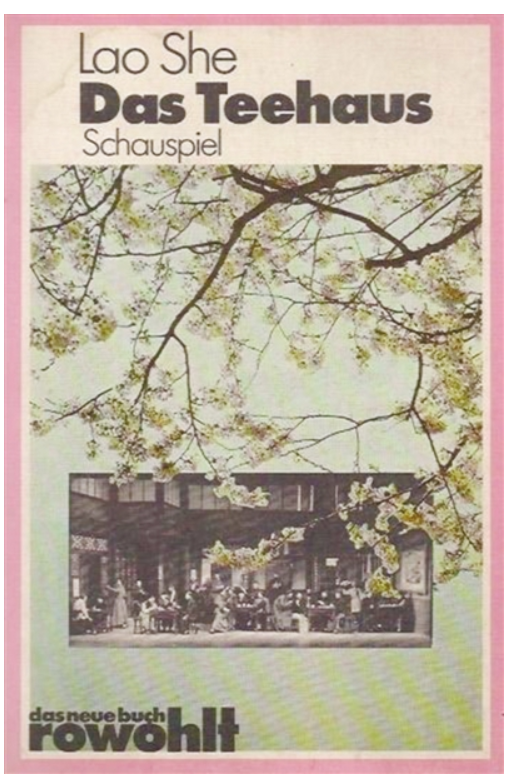
1974年,克劳特应中国外文出版社邀请来华工作。他原本打算待两年就走,结果一住就是40多年。在外文社,克劳特的工作是审校德文翻译作品,同事包括杨宪益、英若诚这样的大家。在他们的引荐下,克劳特结识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作家和演员们纷纷投入工作,他们希望和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克劳特说。
就在此时,话剧《茶馆》提供了绝佳契机。1958年《茶馆》在北京人艺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被誉为“新中国话剧的里程碑之作”。1979年2月,话剧《茶馆》以原班阵容复排公演,英若诚邀请克劳特去观看,没想到却点燃了他对《茶馆》的热情——他一连看了20场。
“20场《茶馆》,我从观众席看到了后台。”克劳特由此萌生了把这部话剧介绍到欧洲演出的想法。1980年,在中国同事们的协助下,克劳特翻译并出版了《茶馆》的德文剧本(见图①,李强摄)。“《茶馆》的故事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的是时代、贫困和家庭的故事,在欧洲很多国家都能找到对应的历史。虽然北京很遥远,但我想欧洲人一定能看得懂。”克劳特说。
然而,克劳特当时与德国戏剧界没有任何联系。“曼海姆离我的家乡并不远,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剧院。”于是,他从北京寄出一封信,收信人是曼海姆民族剧院——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彼时正为来年建院200周年紧张地筹备着各项活动。这封来自东方的意外之喜,令剧院兴奋不已。
“那时从中国寄一封信要十几天才能到德国,收到回信常常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克劳特回忆说。尽管沟通并不那么容易,但双方的合作热情很高。信件来往的同时,克劳特还请自己在德国的家人到剧院沟通,几经磋商,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合作。
“他们是那样地全神贯注,致使《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变得仅有咫尺之遥了”
达成演出意向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将遥远东方的“茶馆”搬上德国舞台,无论对北京人艺还是曼海姆民族剧院,都是陌生和困难的事情。德国工作人员态度严谨,演出合同甚至细化到海报尺寸和印刷数量。但与之后遇到的挑战相比,最初的这些磨合就不算困难了。
距离演出还有一周时,装载着话剧布景、服装和道具的货轮依然下落不明。几经调查得知,船因故停留在英国利物浦,德方只好另请运输公司前往提货。
演员们的遭遇更是一波三折。1980年9月25日,由75人组成的中国话剧代表团从北京登上飞机,刚刚飞抵巴基斯坦却得知,由于两伊战争爆发,飞机无法穿越战区。滞留卡拉奇一天后,代表团换乘外方包机继续向西,途中又因机械故障在阿联酋和埃及两度停留。克劳特作为联络人,与曼海姆民族剧院多次沟通。代表团最终抵达德国时,已在飞机上度过了80个小时。
首场演出被迫推迟,订购的80支欢迎玫瑰也放到冰箱里保鲜。而中方演员只睡了几个小时就马上投入演出。第一个登场的“大傻杨”以一段“数来宝”亮相后,雷鸣般的掌声立时响起。当时,于是之、英若诚、郑榕和蓝天野等一众演员站在大幕后,此前心中的忐忑和长途奔波的疲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饰演康顺子的胡宗温后来回忆道:“剧组准备了一套谢幕方式,最多谢幕五六次,结果却20次、30次都没法从台上下来,谢幕比演戏还紧张,演员们不知道该怎么谢了。”
在演出过程中,克劳特始终待在工作间里,为观众同步翻译台词。他说:“当我建议大家用一只耳朵听翻译,另一只耳朵欣赏舞台上演员们的对白和音响效果时,观众都笑了。”
观众们的表现,正如《南德意志报》所言:“他们是那样地全神贯注,致使《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变得仅有咫尺之遥了。”另一家《莱茵—内卡报》的评价则更直接:“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
回到中国后,克劳特在1983年编辑出版了《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一书(见图②,李强摄)。书中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并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茶馆》在欧洲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英若诚读此书后评论道:“翻阅着这本书,当初《茶馆》剧组访问欧洲时那些动人的场面又一一涌现在眼前:观众的热烈鼓掌,同行们发自内心的赞扬,普通欧洲老百姓对新中国真挚的友好感情,经过这三年的时间,仿佛更真切了。”
在《茶馆》赴德演出后两年,曼海姆民族剧院携反映二战反纳粹主题的话剧《屠夫》来华演出,克劳特同样参与其中。至今,他还保存着《屠夫》1982年来华演出时的海报、节目单和媒体剪报。毫无意外,演出受到广泛好评,该剧随即被翻译引进,从此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话剧《茶馆》走向世界的意义甚至已超出戏剧范畴,它让国外观众产生了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想法。”《茶馆》之后,克劳特又陆续策划了包括黄永玉在内的多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德国举行特展,在中德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也改变了克劳特的生活,他娶了中国妻子,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至今已有40年。中国飞速发展的40年,克劳特体会尤其深刻。他说:“中国每天都在变化。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我从不觉得自己老了,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学到新东西,同时亲手创造出新的东西。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你接受了不同的文化,便能从中汲取营养,我们很富有。”
克劳特一边说,一边打开微信朋友圈,向我展示他刚刚分享的诗歌,是德裔美籍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