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一位帮我整理书橱的“80后”小伙子,从一本旧书里抖落出一样东西,他捡起向我报告:“有封信!”我问他:“谁写给我的?”他把信封上的落款报告给我:“上海……李寄。”我听清了那地址,连忙让他把信递给我:“是巴金写来的啊!”他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是啊,巴金原来姓李!”我抽出信纸,发现巴金的来信是用圆珠笔写在了《收获》杂志的专用信笺上,现在将其照录如下:
心武同志:
谢谢您转来马汉茂文章的剪报。马先生前两天也有信来,我写字吃力,过些天给他写信。我的旧作的德译本已见到。您要是为我找到一两本,我当然高兴,但倘使不方便,就不用麻烦了。
您想必正为作协代表大会忙着。这次会开得很好。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感到遗憾。
祝 好!
巴金
一月三日
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哪年的事了,仔细辨认了信封前后两面的邮戳,确定巴金写信是在1985年的1月3日。
我在“80后”前持信回忆往事,他望着我说:“好啦!您又有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材料啦!”我听出了他话里调侃的味道。跟“80后”的后生相处,我不时会跟他们“不严肃”的想法碰撞,比如巴金的《随想录》,他一边帮我往书架上归位,一边哼唱似的说:“这也是文学?”我不得不打破“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自定戒律,跟他讨论:“文学多种多样,这是其中一种啊!”最惹我气恼的是他倒一副“不跟老头子一般见识”的神气,竟欢声笑语地说:“是呀是呀,这是一部大书!好大一部书啊!”巴金的《随想录》,确有论家用“一部大书”之类的考语赞扬,用心良苦,但从眼前“80后”的反应来看,效果并不佳。
在和“80后”茶话的时候,我跟他坦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供他参考。我感叹,个体生命在时空里的存活挣扎,其悲苦往往是隔代人不解不谅的。“为什么那么‘聪明’?”“怎么不敢当烈士?”是不解不谅者最常用的“追问”。记得萧乾先生晚年曾对我说:“有的年轻人那么说,可以理解,但要不了太久,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会比我们更‘聪明’。”其实全人类都有此类现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如金斯伯格,到七十年代也都成了那个社会守规矩的纳税人,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以前骂死的媒体采访,将著作交由他们以前鄙夷的主流出版商包装推出。
巴金无疑是写过无可争议的正宗文学作品大书的,不仅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其他长篇小说,还有无论从人性探索还是文本情调都堪称精品的《寒夜》《憩园》等中篇小说。当然,他后半生几乎不再从事小说创作,他的最后一篇小说也许就是《团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不是一篇杰作,更不能称为他的代表作,但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拍成放映后,影响极大。不过看过电影之后再去找小说看的人,恐怕很少。电影里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英雄赞歌》,在小说里是没有的,词作者是公木。巴金后半生没怎么写小说,散文随笔写了一些,我记得少年时代读过巴金写的《别了,法斯特》——法斯特是一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颇活跃的美国左翼作家,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的小说,但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泄露出来以后,感到幻灭,遂公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法斯特当然可以评议,但巴金那时写此文是奉命,是一种借助于他名气的“我方”“表态”。这类的“表态”文章,他和那个时代的另一些名家写得不少。那当然不能算得文学。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陆陆续续写下的《随想录》,却和之前的那些“表态”文章性质完全不同。他这时完全不是奉组织之命,而是从自我心灵深处说真话,表达真感情,真切地诉求,真诚地祈盼。这样的文字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得以激动人心,获得共鸣,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可以为之见证。“这也是文学?”年轻人发出这样的质疑,我也理解。拿眼前的这位“80后”来说,他觉得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那样的著作才算得文学作品。这思路并没有什么不妥,帕慕克并不是一位“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实际上这位土耳其作家的政治观念是很强的。《我的名字叫红》里面就浸透着鲜明的政治理念,但无论如何,帕慕克不能凭借着一些说真话的短文来标示他的文学成就,他总得持续地写出艺术上精到的有分量的小说来,有真正的“大书”,才能让人服气。
巴金后半生没能写出小说,这不能怪他自己。他实在太难了。“文革”十年他能活过来就不易。粉碎“四人帮”后,他公布过自己的工作计划,他还是要写新作品的,包括想把俄罗斯古典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翻译完,但他受过太多的摧残,年事日高,身体日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仍不懈怠,坚持写下了《随想录》里的那些短文。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写作,我们除了尊敬,别无选择。巴金晚年公开声明,他不是作家,只是一个通过写文章把心交给读者的人,我以为这不是谦虚,而是他已经非常明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生命,应有一个什么样的坚实的定位。

巴金
我不赞同那种因为巴金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但恢复了“文革”前的名誉地位,甚至更上层楼,就把他奉为神明,甚至非要把大白话的《随想录》说成巅峰“大书”的夸张性评价。那也实在是辜负了他最后给自己的定位。
“80后”小伙子问我:“巴金给你的信讲的究竟是什么啊?怎么跟密电码似的?”其实这也不过二十多年,但拿着那张信纸重读,我自己也恍若隔世。我和巴金只见过一面。从这封信看,我起码给他写去过一封信,这是他给我的回信。“你既然见过巴金,还通过信,前几年他去世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有文章?”我告诉他,以前的不去算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跟他交往频密的中青年作家很多,跟他通信的大概也不少,算起来我在他的人际交往中是很边缘、很淡薄的,对他我实在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过我既然发现了这封信,它也勾出了我若干回忆,而与眼前的小青年对话,也激活了我的思路,忽然觉得有话要说。
我跟“80后”小伙子从头道来。而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章仲锷。“他是谁?也能跟巴金相提并论?”我说,世法平等,巴金跟章仲锷,人格上应享有同样的尊严,他们可以平起平坐。确实,巴金跟章仲锷平起平坐过。那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和章仲锷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当时只有《人民文学》《诗刊》两份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我们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同人以高涨的热情,自发创办了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但一时没有刊号,就“以书代刊”,兴高采烈地组起稿来。章仲锷长我八岁,当编辑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带着我去上海组稿。那时候因为我已经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文学界和社会上获得一定名声,组织上就把我定为《十月》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章仲锷并不是“领导小组”成员,所以他偶尔会戏称我“领导”,其实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愿接受他领导的。他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的经验还是对文学界的情况的了解都比我熟络,去巴金府上拜见巴金,我多少有些腼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却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巴金祝贺《十月》的创办,答应给《十月》写稿,同时告诉我们,他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也即将复刊。他特别问及我的写作状况,为《上海文学》和《收获》向我约稿。他望着我说,编辑工作虽然繁忙,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小说写作继续下去。现在回思往事,就体味到他的语重心长。他自己的小说写作怎么会没有继续下去?他希望我这个赶上了好时期的后进者,抓住时代机遇,让自己的小说写作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说一定给《上海文学》写一篇,巴金却说,你也要给《收获》写一篇,两个刊物都要登你的。《收获》也要?那时记忆里的《收获》,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复刊后该有多少复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巴金却明确地跟我说,《上海文学》和《收获》复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写出了两个短篇小说寄过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学》上,《等待决定》刊登在了《收获》上。我很惭愧,因为这两篇巴金亲自约稿的小说,质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运,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坛,有过几多昙花一现的写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强行中断了其写作生涯,有的却是自己不能进入持续性的操练,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积累和悟性灵感固然重要,而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有前辈鼓励你不懈地“练手”,并提供高级平台,是极大的福气。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如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一种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向我为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巴金的行为写作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编刊物,自办出版机构,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事迹也只能听老辈“说古”,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编的《收获》,我作为文学青年是几乎每期必读的,也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别人多有列举的例子,我不重复了。只举两个给我个人影响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一个是《收获》曾刊发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恋爱,还有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地去伏击给鬼子做事的伪军通信员,将其击毙,没想到那人其实是八路的特工……让我读得目瞪口呆却又回味悠长,原来生活和人性都如此复杂诡谲——《辛俊地》明显受到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影响,但管桦也确实把他熟悉的时代、地域和人物融汇在了小说里。这样的作品,在那个不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国际范围的反修正主义也越演越烈的历史时期,竟能刊发在《收获》杂志上,不能不说是巴金作为其主编的一种“泰山石敢当”的行为写作。再一个是《收获》刊发了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说《童年时代的朋友》,跳出那时期“政治挂帅”对少年儿童只进行单一的阶级教育、爱国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贯穿全篇,使忧郁、惆怅、伤感等情调弥漫到字里行间,文字唯美,格调雅致,令当时的我耳目一新。这当然是巴金拓展儿童文学写作空间的一种可贵行为。
其实中外古今,文化人除了文字写作,都有行为写作呈现。比如蔡元培,他的文字遗产甚丰,老实说其中能有多少现在还令人百读不厌的?但说起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以及跻身学术界时那种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的行为遗产,我们至今还是津津乐道、赞佩不已。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固然是他杰出的文学写作,而他一度履行的“文学罢工”,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行为写作吗?晚年的冰心写短文《我请求》,还有巴金集腋成裘地写《随想录》,我以为其意义确实更多地,甚至完全地体现为一种超文字的可尊敬和钦佩的文学行为。
“80后”小伙子耐心地听了我的倾诉。他表示“行为写作”这个说法于他而言确实新鲜。他问我:“那位章仲锷,他的行为写作又是什么呢?难道编刊物、编书,都算行为写作?”我说这当然不能泛泛而言,作为主编敢于拍板固然是一种好的行为,作为编辑能够识货并说动主编让货出仓,需要勇气也需要技巧,当然前提是编辑与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种互信关系。章仲锷已被传媒称为京城几大编之一,从我个人的角度,以为他确实堪列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名编之前茅。
下
这篇文章还没写完,忽然得到消息,章仲锷竟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2008年10月3日午夜去世了!呜呼!我记得他曾跟我说过,想写本《改革开放文学过眼录》,把他三十年来编发文稿、推出作家的亲历亲为来个“沙场秋点兵”,一一娓娓道来。“你是其中一角啊!”我断定他会以戏谑的笔调写到我们既是同事又是作者与编者的相处甚欢的那些时日。但他的遗孀高桦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他的肺炎来得突然,他临去世前还在帮助出版机构审编别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一部专著竟还没有开笔!

刘心武与章仲锷(右)
从写这段文字起我要称他为仲锷兄。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1980年我一边参与《十月》的编辑工作,一边抽暇写小说,写出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如意》。这是我写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不再像写《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那样,总想在小说里触及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激情构成文本基调。我写了“文革”背景下一个扫地工和一个沦落到底层的清朝格格之间隐秘的爱情故事,以柔情的舒缓的调式来进行叙述。稿子刚刚完成,便被仲锷兄觑见,他就问我:“又闯什么禁区呢?”我把稿子给他:“你先看看,能不能投出去?”过一夜他见到我说:“就投给我,我编发到下一期《十月》上。”我知道那一期里他已经编发了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还有另一位同人正编入宗璞的《三生石》。这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说的阵容已经十分强大,我就说:“我的搁进去合适吗?”他说:“各有千秋,搭配起来有趣。听我的没错。”我虽然是所谓《十月》“领导小组”成员,但确实真心地相信他的判断。那时《十月》的气氛相当民主,不是谁“官”大谁专断,像仲锷兄,还有另外比如说张守仁等资深编辑,也包括一些年轻的编辑,谁把理由道出占了上风,就按理发谁的稿。
后来有同辈作家在仲锷兄那里看到过我《如意》的原稿,自我涂改相当严重。那时一般作者总是听取编辑意见,对原稿进行认真修改后再誊抄清爽,以供加工发稿。仲锷兄竟不待我修改誊抄就进行技术处理,直接发稿,很令旁观者惊诧,以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大”。仲锷兄却笑嘻嘻地跟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活猪也能开水烫,说你几句是你福,以后把字写清楚!”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觉得我那原稿虽较潦草但文气贯畅,怕我正襟危坐地一改一誊,倒伤了本来不错的“微循环”。你说他作为编辑是不是独具慧眼?
1981年我又写出了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写居住空间狭窄引发的心灵危机,以冷调子探索人性,这是我终于进入文学本性的一次写作,但我也意识到这个作品会使某些曾支持过我的领导和主流评论家失望甚至愠怒,写完后我搁在抽屉里好久不忍拿出。那时我已离开出版社,在北京市文联取得专业作家身份。仲锷兄凭借超常的“编辑嗅觉”,一日竟到我家敲门。那时我母亲尚健在,她开门后告诉他我不在家。他竟入内一迭声地伯母长伯母短,哄得母亲说出抽屉里有新稿子。他取出那稿子,也就是《立体交叉桥》,坐到沙发上细读起来。那个中篇小说有七万五千字,他读了许久,令母亲十分惊异。读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辞,跟母亲说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来您告诉他他不会在意”。我怎么会不在意?我回到家听母亲一说急坏了,连说“岂有此理”,但那时我们各家还都没有安装电话,也无从马上追问仲锷兄“意欲何为”,害得我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拿了那稿子,并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当时《十月》主编苏予家里,力逼苏予连夜审读,说一定要编入待印的一期。苏予果然连夜审读,上班后做出决定:撤下已编入的两个作品,以后再用,将《立体交叉桥》作为头条推出。《立体交叉桥》果然令一些领导前辈和主流评论家觉得我“走向了歧途”,但却获得了林斤澜大哥的鼓励:“这回你写的是小说了!”上海美学家蒋孔阳教授本不怎么涉及当代文学评论,却破例地著文肯定。这篇小说也很快地被外面汉学家译成了英、俄、德等文字,更令我欣慰的是直到今天也还有普通读者记得它。如果没有仲锷兄那戏剧性的编辑行为,这部作品不会那样迅速地刊发出来。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责任编辑也是仲锷兄(那时他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记得颁奖活动是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我上台领奖致谢颇为风光,但三部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虽然被点名嘉奖,却没有安排上台亮相。仲锷兄后来见到我愤愤不平,说就在后台把装有奖金的信封塞到他们手里完事,抱怨后还加了一句国骂。“80后”小伙子今天又来跟我聊天,听我讲到这情况说:“呀,这位章大编确实性格可爱,其特立独行的编辑方式也真是构成了行为写作!”
再回过头来说巴金给我的那封信。原委应该是1984年冬我应邀去联邦德国访问,其间见到德国汉学家马汉茂(Martin Helmut)。他虽然原本以研究中国清代李渔为专长,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巴金等老作家的复出和改革开放后新作家作品的出现都很看重。当时他是波鸿大学的教授,也是行为写作胜于实际写作。他自己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并不多,主要是写推介性文章,积极组织德国汉学家进行翻译,并且善于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社会影响,说动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德译本,还从基金会或别的方面找到资金来邀请中国作家到德国访问,联系媒体安排采访报道以扩大影响。并且他具有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资格,尽管他后来的立场和观点具有争议性,而且不幸因患上抑郁症在1999年6月跳楼身亡,但他那一时期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入西方视野的行为写作,我们不应该遗忘抹杀。我从德国回来,应该是把马汉茂在境外发表的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与巴金有关的文章、访谈的剪报寄给了巴金。马汉茂那时候跟我说,后来我又从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等那里听说——他们虽然观点多有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一致——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本来不错,但缺少好的外文译本。他们认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好的外文译本。马汉茂很具体地跟我谈论了巴金作品的英、法、德文的译本,其中德译《寒夜》的一种比较好。他说要是巴金其他小说的译本都能达到或超过那样的水平,那么西方读者对巴金的接受程度会大大提升。我大概是带回了《寒夜》的德译本转给巴金,所以他信里说“我的旧作的德译本已见到”。那时在“文革”后巴金手里已经没有几个自己小说的境外译本,他希望我能替他多找到一两本,心情可以理解。
改革开放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怎样的生机?一是作家的生存方式和作品的面貌都呈现多元了,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还有就是中国对外面的文学敞开了门窗,而中国文学也确实走出了国门,尽管到目前还是“入超”的局面。从巴金二十三年前的这封来信,你可以看出像我这样的新作家已经得到他那样的老前辈的平等对待,我们已经完全不必惧怕“里通外国”的嫌疑,可以坦率地谈论与外国汉学家的交往以及中国作家作品在境外的翻译出版情况。“80后”小伙子说他从网络上查到一份资料。天津有一位用世界语写诗的苏阿芒,写的诗完全不涉及政治,但因为投往境外的世界语杂志发表,竟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锒铛入狱,直到胡耀邦主政时才被平反昭雪。我说你应该多查阅些这类的“近史”资料,有助于理解祖辈父辈是通过怎样的历史隧道抵达今天的,而这几辈人也就可以更融洽和谐地扶持前行了。
巴金信里说“您想必正为作协代表大会忙着”,他的猜想不确。我这人不习惯开会,到了人多的会场总手足无措。他说的是中国作协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没等会议开完就回家去了,那以后我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会议,我从未为开会而忙碌过。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共识的形成、凝结、发酵和碰撞、破裂、分驰,是必然的,文化界包括文学界莫不有这样的现象。现在大体上歧见各方对问题的“点穴”几无差别,但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则择路不同。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往回走。巴金的一封信,使我对老一辈肩住因袭的闸门,自己走不动了,鼓励后辈冲出闸门,去往广阔的天地那样一种悲壮的情怀深为感动,我同时回忆到仲锷兄那样一起往前跑的友伴。就实质而言,我们的生命价值可能也都更多地体现于行为写作。我对“80后”小伙子说,创作出真正堪称“大书”的作品,希望正在你们身上。他没有言语,只是拿起那封巴金的信细看,似乎那上面真有什么“达·芬奇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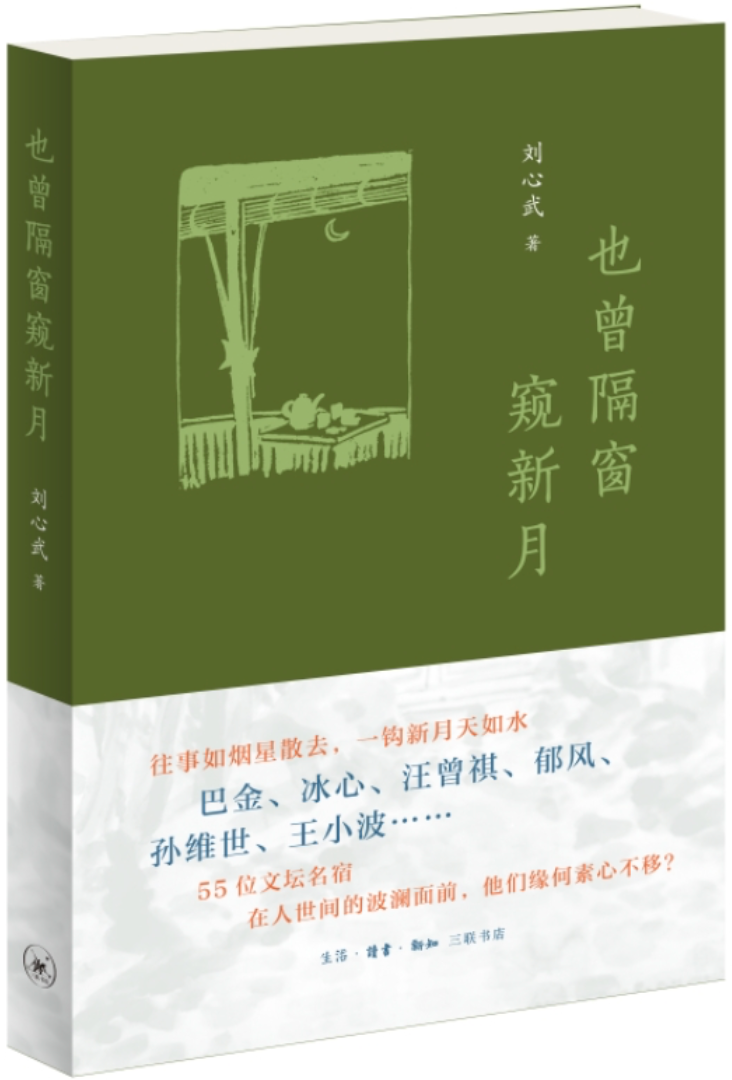
(本文摘自《也曾隔窗窥新月》,刘心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3月第一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