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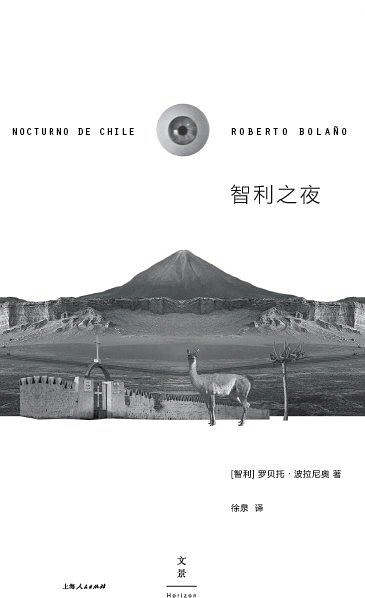
《智利之夜》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译者:徐泉
版本: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罗贝托·波拉尼奥
智利诗人、小说家。40岁时才开始写作小说,50岁时因肝脏功能损坏在巴塞罗那去世,在短暂的创作时间里留下了10本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和3本诗集。《智利之夜》是波拉尼奥第一部被译介为英文的作品,该书的西语原名为“屎风暴”。
读过小说,我们将难以忘记这些绝望的声音:
“在智利我们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在其他地方也是。为了避免自己跌入垃圾堆,我们才创作文学。”
“在这个被上帝之手遗弃了的国家里,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有文化的。其余的人什么都不懂。”
“不可动摇的时间在摧毁所有人的作品。最终连祈祷都会使人厌倦。”
“孤身对抗历史是没法做成什么的。”
波拉尼奥写出的,是文学的迷失,并借人物之口向我们追问:“这有解决方案吗?”
意识流中的六个故事
在智利如何创造文学
整部小说,是以“我”的口吻和视角来呈现的一次意识流动。“我”是一个自以为不久于人世的神父、批评家兼诗人,受到某位“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的指责和辱骂,陷入慌乱和恐惧,侧躺在床上,在头脑中进行了一场滔滔不绝的回忆和自我辩护。
这场头脑风暴(原文粗暴地称之为“屎风暴”),实际上包含六个彼此相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我”在批评家费尔韦尔的庄园里见到了聂鲁达,感受到农民和土地的善意,受到文学的召唤,决定成为一个批评家和诗人。第二个故事,则是作家萨尔瓦多·雷耶斯向“我”讲述的,他与德国作家荣格尔一起去拜访一个绝望的危地马拉画家,这个画家拒绝进食,在沉默中等待死亡,整日枯坐在窗前打量巴黎。“我”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某种莫名的精神力量,为之振奋,而费尔韦尔却给“我”泼冷水,讲述了一个鞋匠的悲剧:功成名就的鞋匠觐见皇帝,提出捐资修建帝国英雄纪念碑,也请皇帝提供资金支持,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英雄们立碑,守护这个世界岌岌可危的文明和道德(作家该做的事,由一个鞋匠在做,多么讽刺)。皇帝热泪盈眶,对鞋匠表示敬意。鞋匠随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金钱,而皇帝和大臣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时代和历史忘记了他,当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战争来临之时,他死在无法完工的英雄谷里。
“我”从中依稀明白,死亡和时间会带走一切。后来“我”日益感到厌倦和空虚,写出恶劣的诗。在动荡时期,“我”离开智利,去欧洲考察如何保护和修复古教堂,顺便写写游记。“我”看到欧洲的神父们普遍养鹰,用来驱逐鸽群。这一部分构成了小说的第四个故事。
然后小说进入到持续的高潮,写“我”回到智利后,面对独裁政权选择放逐自我,在古希腊作品中打发掉革命和政变的岁月。“我”对自己说:“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随后,聂鲁达死了,军政府上台。这时候,“我”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为最高领导讲授马克思主义,给军政府的首脑们上了十次课。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理解自己的敌人,以及如何保持心理优势。皮诺切特将军向“我”质问到,阿连德读过什么、写过什么?然后骄傲地列举自己写过的军事书。“我”克制不住激动,将此事告诉费尔韦尔,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但没有人真正在意。我依然享有荣誉和赞美,小说最后写的,是“我”在宵禁期间出入女作家玛利亚·卡纳莱斯在别墅举办的文学沙龙。有一次,一个剧作家醉酒闯入别墅的地下室,看到了一个被折磨和囚禁的男人。剧作家没有声张。事后人们才知道卡纳莱斯的丈夫就是军政府秘密警察的头目。这个美国丈夫倒台后,“我”去看望落魄的卡纳莱斯,她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的文学生涯结束了。离别时她忽然告诉“我”:“文学就是这样被创造的。”
回忆的最后,“我”也这样告诉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在智利就是这样创造文学的,就是这样创造伟大的西方文学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说不。随后他的声音消失了。“我”自负地以为自己战胜了他。
波拉尼奥的自我烛影
业已衰老的年轻人
阅读过程中,有个问题会不断浮现:这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究竟是谁?
读完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我”的另一个自我。是那个对文学忠贞不二,不肯在权力面前逃避、屈服的自我,也是那个最开始满怀激情,然后被欲望、死亡和恐惧慢慢消磨掉的文学圣徒。他的辱骂不光针对“我”,还针对包括费尔韦尔在内的其他作家和批评家。他不能原谅“我”们所有人。作为所谓的时代亲历者,作为文学的守护者,“我”们背叛了文学。“我”们都选择了逃避责任、美化历史、攀附金钱、向权力献媚,沉湎于自身的名誉和虚无。“我”们让文学流连于批评家的庄园、古意盎然的欧洲之旅、秘密警察的文学沙龙、最高权力的后花园。文学与那些纯朴的农民没有关系,与社会和正义没有关系。文学是“希腊和拉丁作家,是普罗旺斯作家,是温柔的新体诗,是欧洲的经典,最后才是托尔斯泰”。这是文学的死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面临死亡的时候,恐惧袭来,投身文学的人没有被文学拯救,一生的文学事业没有带给“我”们安慰,反而像噩梦中的影子一样,带给“我”们耻辱和恐惧。
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他不怕死,不怕失败,他独自一人,不怕被历史抛弃。他像那个垂死的危地马拉画家,愿意接受失败,然后慷慨赴死。他也像那个为了堂吉诃德式的理想而献身的鞋匠一样,愿意为自己事业的尊严去死,为文学而死。
实际上,那位业已衰老的年轻人,也是作者波拉尼奥本人。他对文学有着极致的虔诚,对拉美的文学史,也有着同样的愤慨。控诉权力,为文学致哀,是波拉尼奥的一贯主题。他的小说不像我们惯常接触的作品那样关注现实人生和平凡人物,而是始终围绕文学本身,执着地讲述作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们的故事。他真正关心的,只有拉丁美洲的文学和文学的历史。
人们津津乐道于这部小说的结构,意识的汹涌流动,速度如水泄一般,整部小说九万字,只分两段,且最后一段只有一句话。但真正让人惊叹的,还是波拉尼奥的语言。那完全是诗的语言,有诗的密度和浓度,一个个的隐喻,一个个的谜语,从头至尾,贯穿始终。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只有诗歌才是波拉尼奥最为钟情的。他的语言中充满许多难解的谜语,当他写道:“我看见了一群猎鹰,成千上万只,在大西洋上方的高空中,朝着美洲的方向飞翔。有时候,太阳在我的梦中变成了黑色。”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的具体所指,我们只能感受到他提供的那份诗意。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猎鹰?“我”放走的猎鹰罗德里格暗示的究竟是什么?那个一再出现的“索尔德罗”究竟意味着什么?谁的索尔德罗,哪个索尔德罗?那个危地马拉画家究竟在巴黎的黄昏中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能真正理解波拉尼奥,不能完全破解这些隐喻和诗句。对拉美当代文学,对智利的文学图景,对他独具一格的文学传承,我们所知甚少。而这些东西是波拉尼奥小说的全部素材和全部的主题。他写的小说,相当于一部部虚构的作家传记,一部部虚构的文学史,他以此来反复重申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荒野侦探》写的是一群诗人和艺术家寻找一位失踪的女诗人。《2666》则是以史诗的架构来呈现几位文学评论家和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的生活和时代。《美洲纳粹文学》写的是九十二名文坛恶棍的故事,虚构掺杂纪实,使读者难辨真假。《遥远的星辰》《护身符》《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也都是以文学和文学爱好者为主角,书写这些人的梦想和罪恶。
细读过《智利之夜》后,我发现自己对眼下大部分批评家、作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不由得想到,他们读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是怎样被创造的?经典是怎样产生的?谁在依附权力?谁在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谁在为转瞬即逝的荣誉和声望洋洋得意?谁遁入了虚无而不自知?谁在以文学的名义背叛文学?原先习以为常的一切,忽然变得可疑和可憎了。在一种悔恨的悲怆中,我仿佛也看到了那个怒气冲冲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会推荐普通读者去读这本书,因为很明显它是写给某些特定读者的,写给那些曾经狂热地爱过文学的人,那些在文学和青春中投入全部激情的读者。波拉尼奥对三心二意的一般读者不屑一顾,会让很多人受到冒犯。他坚定地保持着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在他心目中,只有某类特定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才值得付出全部生命,无愧于自我、历史和时代。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