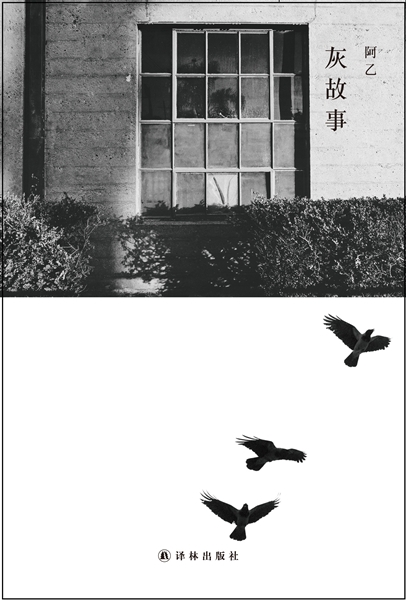
书名:灰故事
作者:阿乙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定价:38.00元
出版日期:2016.6
关于本书
《灰故事》为中坚派作家阿乙的成名作,收录三十则故事。这部集子一版再版,无论在书评界还是大众读者间,都积攒了极佳的口碑。本书的译林新版,在装帧上再作精进,与作者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一起推出,既是作家本人对创作生涯的回望、对文字元气的回味,也是阿乙对自己真挚的检验:这许多年的字里行间后,在写作这件事儿,他究竟迈出了多远?
一份警察工作,曾让阿乙近距离目睹人世百态,极端的、畸形的案例在眼前铺陈。褪去制服后,以局外人之眼再观案中人,他写下了这一篇篇仿若嵌入了你我、惊心动魄又晦暗荒谬的故事:桥上,爆炸案的肉体残骸四散零落;棺材里,裹挟着死老鼠腐臭气味的女尸等候开肠;馄饨摊边,混乱中捡钱的刹那决定了他的一生……阿乙文风冷冽、残虐,呼应着的是那吊诡的人生处境、顽劣的人性盲区。
本书亮点
★ 最有故事的中坚派作家阿乙成名短篇集,汇集阿乙创作艺术的灵魂精魂
★ 阿乙最为经典的作品集,一版再版,本次的新版装帧精美,由作者亲自校订,适宜收藏
★ 故事可读性强,涉及面广,颇有中国小镇生活浮世绘的味道,却不失深刻犀利,发人深省,富有启蒙的意识
媒体评价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北岛
阿乙的小说令我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
——李敬泽
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王小山
我们这种扑腾得很厉害的人,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阿乙这样的人会留下。我很庆幸,在他出道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帮助,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将来文学史上会顺带记上我的名字。
——罗永浩
精彩试读
在流放地
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一定会看到沟渠似的海洋、鲸脊似的山脉、果壳般的岙城派出所,以及蚕子大小的一张桌子。桌子的南北向坐着警校实习生我和小李,东西向坐着民警老王和司机,四个渺小的人就着温暖的阳光打双升。
扑克天天在打,当时的我只觉一夜没睡好,像是被绑架而来,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觉得诡异。
有时一些俗语也是诡异的,比如“百年修得同船渡”。一个男的因为父亲忙,拿着讨账单上了船,一个女的因为感冒要去对岸看病也上了这艘船,两人素不相识,下船后却去了民政所登记结婚。而我、小李,以及一大堆同学之所以来到石山县实习,也是因为石山县公安局局长的儿子高考时少几分没上线。警校破格招收了人家公子,人家知恩图报把石山县建成实习基地。我就这样从魂牵梦萦的省城来到陌生的石山地区、石山县,然后被石山县局政工科长随笔一划,划到柏油路晒满柚子皮的岙城乡。
我在这个鸟地方遇到五十岁的民警老王。一个民警的人生轨迹按照常理判断,应该是“乡下派出所—刑侦大队—局某个有油水的科室”,可是老王却反过来了,是“局某个有油水的科室—刑侦大队—乡下派出所”,好似朝官苏轼一贬黄州,二贬惠州,再贬儋州。按照司机的说法是,老王品质出了问题,先是在局里有笔账对不上,接着在刑侦大队和女嫌疑犯的逃跑没脱开干系,由此像块抹布被塞过来了。老王在派出所待着时,日日指桑骂槐,说都不是东西,有次说自己在县城带了个女人去洗浴中心洗澡,洗到一半,门被踢开,是局纪委的来抓奸。“狗戳的,我让你们好好看着,这淫妇是我老婆。”
也许是这罕见的贬谪使老王变成一个怪物,在路过他的办公室时,我时常能听见凄楚的叫喊声,偷东西的喊一声,老王就阴阳怪气地说“何辉东我让你喊”,赌博的喊一声,老王也阴阳怪气地说“何辉东我让你喊”——何辉东就是这里的局长。而在我见不到他时,那又准是他坐吉普车下村了,回来时他一般满脸酒气,像充血的阳具。司机说:就为了下去混包烟,汽油烧了大半缸,红梅哎,四块五一包。
派出所的所长和一切有前途的民警根本不想惹、不想理老王,关系老早就挑明了:你我只是同事。老王似乎悻悻。他现在也许要感谢上天给他派来两个年轻的外地实习生,他可以用鹰爪掐着他们的肩窝,呵斥他们,让他们走十几里路去取个毫无意义的证,在他们回来后又让他们重新去取,如此来来去去,他便有了狱卒式的快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只要让囚犯不停地重复某种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把甲水桶里的水倒在乙水桶里,再把乙水桶里的水倒在甲水桶里,如此反复,囚犯肯定要自杀。”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现在,老王的右手捉住左手的两张牌,想出又不敢出,想了很久,去桌上废牌里一张张查,却是越查越犹豫,越查越担心。我心说,不就是梅花一对10吗?我快困死了,我一夜没睡。我就在这暖酥酥的午后阳光里,微闭着眼,慢慢走向混沌,许久才听到霹雳一声响:对10!
我勉强睁开眼,抽出梅花两张甩出去,说:管了。老王大怒,说:耍什么赖。我定睛一看,出去的不是对J,而是J、Q各一张,急忙抽出手中另一张J,可是老王五指伸出挡好:年轻人啊,耍谁呢?我想发作,愤怒的河流却在喉管处倒流下去,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可是我又确曾感觉到有愤怒声势浩大地来过,我这是怎么了?我的脾气很好的。
老王捡了这二十分,控制不住笑意,风吹过这脸肌颤动的笑意时,像是吹拂收到金条的太监。这局完了,我听到变态而幸灾乐祸的声音:钻!
我涨红脸,像条狗钻到桌子底下,看到那边已经蹲下的小李很无奈地摇着头。后来的很多局都是如此,一个像老年女人的声音在一次次下判决:钻!我慢慢麻木了,觉得命该如此,有次不该钻,竟恍惚着钻过去半个身子。
老王哈哈大笑,说:瞧你多像条狗啊,不给钻也钻。
我起身时,本已冰冻的愤怒之河忽然返涌上来,我匆匆把牌洗好,说:抓。老王抓一张牌,舔一下口水,恶心得要死,我心说:再不让你了。老王仍像从前一样,把每张牌当围棋下,将我拖入到他漫长而无聊的长考当中。可是我决心已下,只要他一出牌,就迅速把自己的牌拍出,他出对7我就出对8,他出对K我就出对A,他想把牌抽回去,我就死死压住。小李的脚在桌子底下踢我,可我忽然就是这么坚决。
老王起先还想讨好,见我眼眶突出,被激怒了,也开始愤愤地出牌,好像要在战场上将我心服口服地整死,可是分数却在我面前不由分说地多起来,过八十分时,他的脸色不好看起来,到一百八十分时,就蜡白了。这样他还没完,钻桌子要到两百分,他的尊严看起来还牢固得很,我甚至都知道他要说:让老子钻没那么容易。他有这个侥幸。
我手里抓着一张大王和所有人手中最后的一对,这一对将把老王埋下去的五分翻成二十分。底下埋五分的人就是这样,小肚鸡肠,患得患失,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可是他竟然还说:五分我让你们捡。听到这可笑的话,我眼前辉煌的终点摇晃起来,我几乎幸福得坚持不住了。
果然,他倒数第三张没有出自己那张大王,我把大王拍出来,又把那一对拍出来。老王眼睛傻在那里,我把底翻开,找到那张方片5,说:钻吧。然后便看见汗珠像饿鼠从老王的发根里蹿出。不一会儿,这个失败的老头转动一下眼睛,很快换了一张牌,说:小伙子且慢,你的一对我管得起。
我站起来说:你哪来的一对?你偷来的老Q是我第一手出的。钻吧。
老王好像正在作案的小偷忽见顶棚的灯全部打亮,竟是无地自容起来,他恳求着说:就是你错了,就是你错了。我清脆地回击:钻!
我原以为他不可能妥协,可他却命令司机端起桌子,猫腰穿了过去。我本来一直在等这个场景,它来了却忽然没了快感,就好像真是一条狗在面前毫无关系地路过。我木然地坐下来,眼眶有了湿意,重新陷入到麻木而随意的情绪中,重新胡乱地出牌,而老王已像条发怒的豺狗,在牌桌上左嗅右嗅。
对这样狭隘的报复,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让我钻我就钻,我什么脾气也没有。可这也触怒了他,他想我应该像个被强奸的妇女,死抓床单,狂呼救命,表现出受凌辱的样子,可我却麻木地袒露着性器,像一条死鱼,连“你操你操”都懒得说。有次我钻出来还面露微笑,我不知道怎么就微笑了,我控制不住稀奇古怪的情绪。老王紧张地盯着我脸上盛开的花朵,备受嘲弄。
我合拢牌,有气无力地说:不打了吧,我困了。
老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就像晾晒着的被单,风往这边刮,就往这边飘,风往那边刮,就往那边飘。我有一张没一张地出着,头慢慢往桌上凑,终于跟着睡意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了,然后又迅速感到肩窝处传来刺痛。我犟直头,盯着老王,说:放下。老王恶狠狠地说:好好出你的牌。
我便秋风扫落叶,三下五除二,把手上两个拖拉机打出去,又用一个拖拉机扣底,把分数变成两百多了。我不承认自己是在戏弄这厮,只是这把牌太好了,我不想打,他偏偏让我打了,现在好了,牌局可以结束了,我可以原谅他,回到床上睡觉。可是,从嘴里飘出的声音却是“钻”。老王没有反应,我看看他,他正抚着脸上的汗寻思挽回尊严的策略。我知道他有的是办法,这个贪恋扑克牌像贪恋女人一样的怪物很快将从冰窖嚣张地归来——无论如何,我都只是个可供欺负的实习生。
老王敲着桌子说:你不好好打。
我无力地说:你钻不钻?
老王敲桌子的节奏更快了,好像要告诉我他的愤怒多么急迫——你不好好打,是你不好好打。
我说:好,那就不打了。
说完我站起来。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摸清老王是什么脾气,我正要走,他又推起半边桌子气呼呼地钻了过去。到此时为止,一切还都属于一个派出所内部的正常活动。
可是,在我被一种凄苦的情绪裹挟住,并促使我作出更坚定的决定后,事情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我知道老王肯定要通过牌局组织更疯狂的反扑,我知道这天我不钻几十趟不会结束,可是想钻忽然也难,是要让他次次打我们小光啊,我觉得这是荒谬而永无止境的任务,就好像西西弗斯把石头一次次推上山,推上去,还要回到山脚继续推。我如果不坚决点,就永远走不出这无聊的圈套,我并不是你的羔羊啊,老王。
老王兴奋地洗牌时,我把那个决定说出来了:不玩了,到此结束。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向厕所。我看到前边是一条十米长的细小水泥路,路两边是肥沃的青菜和一辆废弃摩托,吴教导老婆洗好的床单正在微微飘荡;太阳如此明亮,床单上的蜜蜂在一朵红色大花上清晰地展翅飞翔,花有六颗瓣,瓣中心有十二根嫩黄的花蕊。可是在我的脑后也有一双眼睛,我看到无数根白发瞬间从老王的头皮生出,我看到他身体筛糠起来,他努力了几次才扶住自己,然后眼睛冒出被羞辱的火。他抽出笨重的五四式手枪。
在警校练习射击时,我就知道五四式比六四式笨重,正因为笨重,瞄起来准,杀起来狠,而我宽大的背部现在就是那硕大的靶子,这块靶子在只有十米的水泥路上强制着镇定移动,随时都可能被洞穿——在这么有效的射程范围内,最笨的射手也不会失手。
我听到后边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你让老子钻了,你不来,你不是耍老子吗?你给我站住。
我听到后边传来焦急的声音:别啊,他还是小孩子,真是孩子。
我听到后边枪栓拉响,一颗子弹上了膛。
我的腿微微抖了一下,像是很饿很饿,可我还是昂首继续往厕所走。厕所的边墙写着最后一个汉字:男。那荒谬的汉字近而遥远,那时间凝滞了,我的背部湿透,我在等待飞啸而出的子弹。
可是在双腿自行行走很久后,我还是走进边墙的阴影了,就像士兵走进掩体。那个怪物失败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把枪了,放回去丢面子,端在手里也丢面子,最后应该是司机不容分说帮他塞回枪套了。他连说几声“干什么”,没有阻挡住司机的好心。
厕所内有两块长木板,木板下是只大粪缸,蛆虫们拥挤着往外游,游到缸沿一半又溜了下去。我裤子也没脱,掏出口袋里一封揉皱的信,蹲在木板上一边看一边号啕大哭。那是一封致“岙城派出所艾国柱先生”的信。
我昨天接到时看到“先生”二字已承受不住了,急急打开看,种种不祥的预感一一坐实。这意味着,从一九九五年的此日起,我被正式宣判放逐了。这个女孩绞尽脑汁花半小时写了很多温暖的话,又觉得这样会给别人留下奢望的机会,就又加了些严厉的话,想想过于严厉了点,就又去写些温暖的话。她不知道最后写完时,这信已和法院判决书一样硬朗,格式如此:你的行为……导致后果……鉴于此……
她的意思如此明显。而我那么爱她。我对她持久的追求与骚扰,属于我的初恋以及我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全部被判定为不合法了。那诡异的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一个下午,一个男的因为父亲忙,拿着讨账单上了一艘船,一个女的因为感冒要去对岸看病也上了这艘船,两人素不相识,下船后,男的开始单恋。好了,这事情妈逼的结束了。
我把信丢进粪坑,擦干眼泪走出来。太阳模糊了,远处的司机、小李正在接受老王对年轻人虚张声势的批评,我知道他的脊梁骨被我敲断了。我低下头,不去看他,以示我很害怕。我会给年纪大的人留点面子。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