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明 诗人,1955年出生于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年轻时当过知青、码头工人。1989年赴巴黎第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常年在法国从事电台新闻记者职业。现居家写作。今年5月,出版诗集《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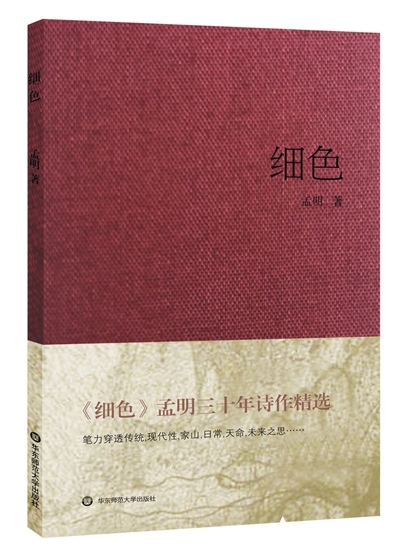
细色
作者:孟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旅法诗人、翻译家孟明。
带着三十年精选诗集《细色》,诗人孟明如剧场中人,来到人们眼前,又很快抽身离去。5月在北京,6月在上海,出版方组织、举办了两场新书分享会,他谈得极少,现场主要是读诗。趁这个机会,孟明回到故乡海南省亲。结束这一切后,他复归欧洲,8月联系他时,已在西班牙、法国游走。
归来仍是客。孟明的名声更多来自翻译:他译介诗人保罗·策兰,其译作被认为将策兰的诗歌精神在汉语语境中予以完整呈现;他翻译尼采著作,尼采诗集《狄俄尼索斯颂歌》“中译本前言”竟多达115页,译介甚至影响了他对诗人本身的看法。“在我看来,诗人的最高涵养是尼采说的诗与思的集大成者。”孟明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篇前言中,他再次提出“语言就是我们的故乡”。
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位,孟明和许多人一样,去国离乡,成为一位“隐居”诗人。在写作中,他常提及“天命”——那一种与时代、个体紧密勾连的不可言传的命运,但要谈论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己的“天命”,他觉得“困难且不妥当”。在此背景下,汉语或者说母语,为孟明提供了精神的庇佑,即使长年身在异乡,精神亦有着落,时间不至于白白流逝,进而避免布罗茨基所说的“流亡的平庸”。
“我在异乡有这样的感受,仿佛是一种宿命,一个好的诗人,不管在何处,远离故土,他必定总要回过身去抓那撇弃的‘母语之舟’,不是‘母语’这个被人挂在嘴上的轻浮概念,而是其中本质的东西——家山之物。抓不住,就什么也别写了。”孟明说。
人人都是异乡人,传统日渐瓦解、身心轻易分离的时代,我们应如何自处?孟明呈示了自己的选择。
重返故乡
“老实说,这次我麻木了”
孟明1955年生于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小时候,他读到父亲的一本案头书,即郭沫若1962年点校的《崖州志》,书中称崖州有“邹鲁之风”,不得甚解,脑海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原来,这里从唐代起就成为贬逐忠良的流放地,孟明还记得唐朝诗人李德裕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后来北上求学,他一直跟朋友说自己是从“鬼门关”出来的。
读中学时,孟明面对的是一个禁书年代,“只有鲁迅读得最多,我几乎翻遍了鲁迅的所有著作;我至今对鲁迅的偏爱,兴许就是那时来的”。他寻觅到一本钱春绮翻译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爱不释手,“至今还记得不知哪首诗里写到阳光下海面那‘一大片黄金’”。正是钱春绮译介的海涅,把孟明引向了现代诗。《爱情故事》一诗就是1987年在海涅的影子下写成的。
直到孟明上高中,三亚还是一个破败的小镇,镇上居民不多,除了老码头一带几幢砖瓦大宅和日军战后留下的颇为别致的日式吊脚楼,民居多是泥墙茅草房和简陋的木棚屋。但是,他感觉,那里的海岸、沙丘、芦苇、田畴甚至荒草,在荒凉之中莫不透出热带宁静的自然之光。这当然是如今回望的感受。多年后,三亚已建成高楼林立的地级市,房价骇人,以旅游业闻名,国内外游客趋之若鹜。幼时,孟明被送到舅父家,那里家家都去孔庙挑水,如今,人们用上了自来水,井已弃用,孔庙焕然一新,香火兴盛,成了一个供人参观的商业景点。对于一个浪子来说,故乡的记忆被改写、更新,甚而基因再造。今年6月,借新书分享会的契机,孟明回乡省亲,走在到处高高耸立的钢筋混凝土之间,没有惯常所见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惊叹,而是越来越默然,他坦承:“老实说,这次我麻木了。”
新书中,一首题为《枫木鞘花》的诗写道:“一切都在融化,吹蚀;时代/高耸着,吹蚀的生命,/夷平,而后高耸,更高的重迭猥闶的时代,/单调而乏味,但高耸……”孟明所见,正是这样一番景象。他担心,家乡人会在现实中“越来越麻木”。
“我在外游学多年,每次重返故乡,面对新的世态炎凉,尤其在如今人们对小康盛世的啧啧颂扬声中,总有一种他人难以体味的失落感。我知道,当一个人的故乡成为记忆,或记忆成为故乡,也就意味着地平线上家山之物已荡然无存。”孟明对记者说。
以诗见证
从青春无畏到道路迷茫
1973年,孟明刚中学毕业,接到“上山下乡通知书”。他成了一名知青。就个人经历来说,孟明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和后悔”,但清楚记得,下放到一个农场没几天,县里派来的领队干部就当着全体知青的面,命令他把随身带来的几本书扔到茅坑里去。孟明拒绝了,因此成为“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
当年,孟明写了一首《梦》,末尾是:“死亡也像稻花,/白中带紫,我们曾经采撷,以——/无畏的青春和对苦难的无知。”稍加修改后,他收进了新书。“这首忧郁的小诗,可以说是我知青年代的遗物,也是一个见证。”
回城后,孟明得到政府的招工安排,当了一名码头工人。他从小最恨当码头工,“一种最脏最苦的苦力活,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硬着头皮上,这份工作前后持续了约两年时间。他至今记得那一种感觉——在深暗的货轮舱内装卸含剧毒的“六六粉”一类农药时,飞扬的尘灰呛入肺腑,似乎马上就要窒息死去。
时代移山伟力,突然终结了这一切。1977年,恢复高考,孟明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1984年,又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社科院外文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对于孟明个人,这可以说是一段学院式的平静生活,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1949年以来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西方学术著作如潮水涌进中国,形成“文化大爆炸”的局面。彼时,诗歌成为集体性的狂欢,“第三代诗人”正在崛起,于坚、韩东、徐敬亚等为人瞩目,孟明则志在理论研究,与诗人团体没有太多来往。1989年孟明远赴巴黎求学。
此后,写诗成为沉重的负担,“需要克服自由人的失败、母语的困境、政治概念的直接投射等多层因素才能调整”。最初几年,孟明的诗歌写作不经意就会流露某种“历史伤悲感”。他1993年写的《我们总是这么说》颇为典型,其中说:“你会写下很多东西,因为/记忆是个永远的擅入者。/它,总是以灰暗的方式到来/令你惊慌……”
母语传统
看那些“在语言中寻找祖国的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孟明先后研读法语专业、法国语言文学专业。2003年至2005年,近五十岁的他,又在巴黎耶稣会神学院学习了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外语为阅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思想上的参照。
这不只是语言使用的问题,对于身在异国的诗人来说,它尤其突显了写作的困境:如何使用母语?怎么处理与个人血脉相连的传统与记忆?有的诗人改头换面,甚至努力“换血”,有的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有的则持守着汉语本身的精神气质。
诗人张枣1986年出国,常年旅居德国,夜里喜欢一个人坐在阳台喝酒。他多次向孟明透露写作上的危机。也曾回国教书,在孟明眼中,那时,无论生活和写作,张枣似乎都还无着落感。中西诗意之间,不断锤炼、融合,最终,他的诗作被认为是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完美结合,“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风靡于世。
2010年,张枣去世后,诗人钟鸣评论道:“他倡导由诗重构‘母语观’,‘母语是我们的血液,我们宁肯死去也不肯换血’,可以说,自1980年代至今,出国诗人群——就母语写作而言,独有张枣一人,越写越好,其余几乎‘全军覆灭’。”
孟明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他同样认为“语言是我们的故乡”,即使异国他乡不停奔走,他坚信自己仍然生活在母语这个“故乡”里。不仅如此,他忧心汉语在延续过程中急剧断裂的巨大鸿沟,不是缩小,而是日益扩大了。“丛杂、广博而精妙的汉语古典语文的辉煌废墟和枯瘦的现代汉语急促的历史变迁,后者已经进入电脑的技术时代,竟没有一种经由思想前后衔接的可能,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因此,孟明既用汉语努力寻找、书写家山,试图理解天命,又在语言层面做出积极尝试,如加入《周易》等内容,以衔接古典与现代汉语。尽管在诗中写到“而我们将痛苦地怀疑/那个在语言中寻找祖国的人”,孟明仍然没有忘记强调——
“母语‘故乡’的振兴,也许诗歌是一种可能。”
当身边的一切都是学来的东西,不是你本己之有;没有本己,没有出自你血缘的家山之物,异乡就是彻头彻尾的异乡。这种异乡里潜藏一种危险,当它变得漫长,长到你驾驭不住,那就是布罗茨基讲的“流亡的平庸”了。
对话
没有天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记者:在诗中,你写道,“不懂家山,就不懂天命”。对于你自己,家山与天命是怎样的关系?
孟明:家山是安葬的东西,也是记忆之物:传统,历史,遗产。家山成为基础和承托文明的座架,此种基础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不懂家山,就不懂天命”,这句话出现在一首小诗里,它隐含了外婆生前传递给我的东西,也是《细色》这本诗集中最重的分量,和她一起葬在我家乡的坟山。
你问家山和天命是什么关系。天命,这个词似乎不好懂。记得《中庸》开篇第一句讲“天命之谓性”,这就是一个前提。“天命”这个词今天听起来相当的沉重,仿佛是某种支配人的东西。古人说天命,指的是一个人的造就,也就是自然造化赋予人的东西,所以称为“性”。“性”,性格,性情,秉性,天性,说不定也包含了“身家性命”。天命之谓性,朱熹解释说“性”就是造就一切事物的“理”。按“天命”这个词的古老含义,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人透过天命成其所是。可是按常人的看法,天命这回事很难去言说的,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天命大抵也属于隐微之物的范畴,令人畏惧。
人对天命的畏惧,也因为天命有好有坏。比如人常讲,这人命好,那人命不好。但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者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没有天命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没有天命可能就意味着没有未来,就像一个人被遗弃了,存在的处所一片空白,没人理你,人仅仅在时间中流逝,只有时间,没有历史,也没有着落。如果天命首先给人的是忧思,迫使人去思虑它,那么对天命的思虑,说到底不过是想看见天命罢了,去会见它,把握它。所以,人与天命相遇其实是与天命赴约,两厢情愿。我这个人陷入生活逆境时,偶也害怕天命,担心不好的东西落到自己头上。其实,人规避天命中不好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尽量避免自己的存在变得平庸。
天命藏而不露。人不是凭空就能知天命的。家山即传统,老话说“学而时习之”。今天一切从新,记忆塌陷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民族找不到自己的天命,至少诗人可以通过重建记忆来模仿天命。
诗集中有一首长诗,标题就叫《天命》,是我漂泊在外多年之后,回到故乡做清明祭祀时写的。在这首诗里,我写我的故乡小镇,写那些已逝去或者正在消逝的东西,包括记忆的场所、城墙、土神、山社以及当地人的轶事,那些曾经造就我童年生活的东西。就好像我是一个回来的人,试图寻找家山并理解一种天命。
记者:说到天命,总让我想起墓志铭——这一种奇怪的联想。我的问题是,如果写自己的墓志铭,你会写些什么?
孟明:我不会给自己写墓志铭。假若只是一个提问,需要答复,我会说:“本人长卧于此,但最好到别处去访问他。”
不立足于母语的根基,写一千行也是空的
记者:对于汉语传统,诗人张枣的写作颇为典型。你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为什么?对你有何影响?
孟明:一个“真正的诗人”,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远胜于一切“伟大”“杰出”的形容词。张枣是个写诗极为苛求的人,不到火候不轻易出手,出手则多为佳作。而且,张枣对人们所说的现代性有一种紧张感,他宁可到感性的事物里寻找,譬如到古老的东方经验里寻找。他有这种洞察力,他在异乡写作能驾轻就熟地赋予他的词语以一种少有的置换功能,母语之物往往占上风,所以他的诗没有那种玩现代性词语的干巴巴的毛病。我欣赏张枣,是因为我们有同感,而且知道写诗的人有一个命运攸关的立足点;没有这个立足点,写一千行也是空的。这个立足点就是母语的根基。张枣从一开始就站在这个立足点上,从未离开。他早期写梅花,写楚王梦雨,后来写马勒,写跟茨维塔耶娃对话。后来的一些诗是他到国外后写的,看似异国题材,可是你认真读一读,譬如《跟茨维塔耶娃对话》这首长诗,开篇就说“我向你兜售一只绣花荷包”;接下来,他的词语依然坚持人们鄙弃的“老调调”:“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白云悠悠,玛琳娜……”多么清新啊,在异乡,有这种调式!我敢肯定,这是一种复调,在家山和异国之间,在新旧之间;新就是旧,旧就是新。
我和他同在异乡,他在德国,我在法国,当中隔着两条河,一条是波德莱尔的塞纳河,一条是荷尔德林的莱茵河。张枣喜欢波德莱尔的诗句“回忆的母亲,情人中的情人”,而我偏爱荷尔德林那句“并非无用地虚构了颂歌就为古者响起”。古者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尤其在思想贫乏的时代。当我读到张枣诗中那句“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我就明白了我们共同的困境,因为“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边界”。这种处境,我不喜欢用“流亡”或“精神流亡”这个词语来形容,但我知道诗人骨子里“精神贵族”这个东西是抹不掉的,不写则罢,只要你用汉语写作,不管云游何方,母语这个高贵的东西总是牵扯着你,不仅在笔尖处,而且在血管里,所以我时时有“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感受。
当身边的一切都是学来的东西,不是你本己之有;没有本己,没有出自你血缘的家山之物,异乡就是彻头彻尾的异乡。这种异乡里潜藏一种危险,当它变得漫长,长到你驾驭不住,那就是布罗茨基讲的“流亡的平庸”了。我常常听人说,文化换血可以造就一个伟大诗人,这个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在异乡有这样的感受,仿佛是一种宿命,一个好的诗人,不管在何处,远离故土,他必定总要回过身去抓那撇弃的“母语之舟”,不是“母语”这个被人挂在嘴上的轻浮概念,而是其中本质的东西——家山之物。抓不住,就什么也别写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