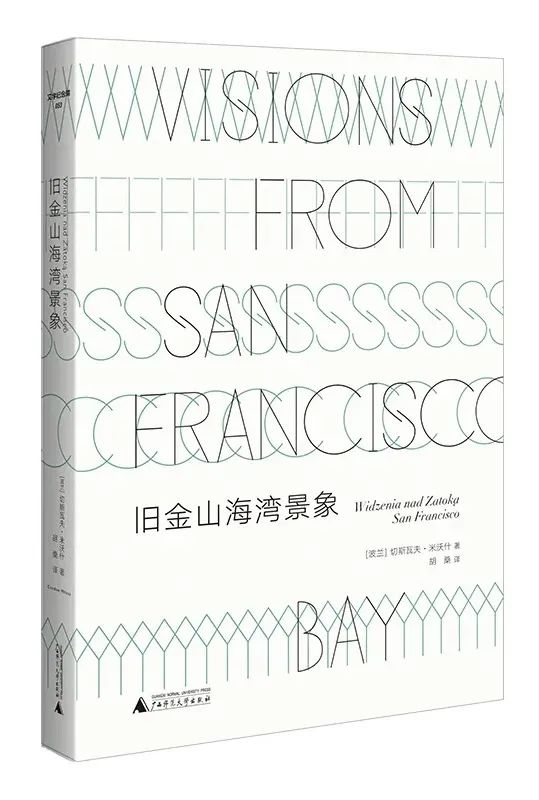
论十九世纪
在这里,十九世纪从四面八方攫住了我。这与建筑毫无关系;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仍然是营地,只是带顶的四轮马车和帐篷已经被房子取代。难以永恒存在的房子;其上的石膏赋予它们欺骗性的石墙外观,然而它们由木材建造而成,这在西海岸很低廉,更防地震。房子是加利福尼亚狂热地进行摧毁和新建的目标,凭借着某种精灵魔法般的速度,一小群船员戴着色彩明亮的头盔架起了脚手架,盖上了屋顶。所以,几乎看不到一座古老的纪念碑,一座大约七十年老的砖头建造的工厂,或者类似于那些西部地区的木头门面,并且竖着拴马桩。
我不喜欢十九世纪,尽管它富于才智。即使当我身陷自己时代的可怕事件,既是一名大木偶剧场的观众也是演员,我一直认为我不会想要生活在那时,而更喜欢已经降临在我身上的东西。这个世纪产生了大量以前从未见过的词汇,学会了使用词语掩盖人类根本的二元性,并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分泌所谓的文化是一种人的属性,就像一条蚕吐出从自己体内分泌出的丝线;然而,由于每个人也拥有一个身体,他的生理功能无休止地奚落着社会交往和精神惯例的变化不定的规则。我可能搞错了,但我在我们更遥远的祖先身上感觉到,对待这些奇怪安排时拥有一种本能的、几乎非自觉的仁慈。正是他们同意这些惯例,似乎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些惯例,并以怀疑的态度运用它们。最崇高的想入非非伴随着异口同声的称赞,粗野的捧腹大笑的称赞。布道文章、神学著作、十四行诗,均以高贵的人为性背叛了自身,因为它们与不太庄重的知识共存,此种知识通过低劣的幽默表达出来。沉静的、无忧无虑的文学结束于十八世纪——从那时起,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无仇恨的色情文学,它其实只在表面上具有微弱的意义。
十九世纪是一个精神的世纪。一种崇高的音调具有强制性,一旦那种音调响起,它就升起了那些同样崇高的新的音调,它们反抗乐器起初所调准的那些音调。精神推翻了惯例,但谁只要打破惯例就会在每个行动中创造出新的惯例——在风暴和压力中获胜,然后变得绝对,变得过于严厉而不允许怀疑的微笑贬低它们。可敬的德国教授在夜总会里全然陷入了哲学的狂欢。诗人折磨着自己的肉体,这肉体囚禁了那些无边无际的精神。政治家在讲台上诉说着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飘逸的田园二重奏在牧师住宅吟唱;窗口宁静的书籍与花朵在这个世界中保护了一座充满诗意幻想的海岛。
从波兰到法国,再到美国
在特定国家的历史存在中可以观察到某种永久不变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过变化而获得的持续性原则,通过持续性而获得变化原则。在西欧,持续性如此强烈,以至于十九世纪的结构似乎保持不变。那些选择残酷的生存斗争作为主题的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今天也许和他们涌现出来的时候一样不怎么过时。马克·吐温或厄普顿·辛克莱笔下的美国不再存在,但法国,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然而,即使在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也不尽相同。在美国,人与人的暴力冲突发生在表面,在公开场合。在欧洲,暴力变得形式化,与几个世纪以来神圣化的阶级分裂相结合;它被内化,变得根深蒂固或被烤融到内部,如果人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达。美国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大胆、机智、慷慨、浪费之上,欧洲的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激情——吝啬之上。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庞大而崭新的经济领域,适应了那些我们越接近二十一世纪时就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需求: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构成的领域,给它们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西欧没有产生任何类似的东西,在这里,教育一直是为少量精英所独占的东西。在美国,私人资本的挥霍使得开端成为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了来自税收的资金。在欧洲,资本的吝啬有效地阻止了为这一新领域奠定基础,并且,政府财政是否能够克服日益扩大的差距是令人怀疑的。
我在西欧生活的所有年月里,甚至没有收到一份来自任何知识传播机构的聘用通知。的确如此,我的领域,斯拉夫文学,和异国有关。然而,在一片至少有一半被斯拉夫人民占据的大陆上,人们竟然如此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我在法国的许多年里,我遇到的所有真正的聪明人物都是欧洲同盟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少量强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才可以与美国和俄罗斯构成任何形式的平衡力量。他们遇到的阻力,导致他们的计划实施得非常缓慢、三心二意,此种阻力在我看来,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造成的,这种狭隘精神拒绝承认我的资质,认为它是多余的,只是因为我是一个从栅栏另一边新来的人。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