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钢琴家ayaka办过个人演奏会,上过《泰晤士报》。住在中目黑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六本木,算得上大家口中的“港区女子”(港区即日本的六本木、中目黑、赤坂等繁华区,港区女子过着缤纷多彩的生活)。直到人们发现,她在中目黑的家是一户独栋里、二楼许多间中的一间。木门咯吱作响,房间面积不足8平米。没有独立的卫浴、没有厨房冰箱。“逃犯生活啊。”
人们的惊讶也令ayaka感到惊讶,她对所谓的低配生活并没有过不满。但显然,空间已是普遍意义上社会等级的记号。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一章里论述了这一现象:不同阶层占据不同空间,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韩国电影《寄生虫》的空间与阶层间就有明确的指向。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代表生活内部的、狭小简易的房间,自然与住客体面的外表形成反差,成为话题。

其实,青睐拥挤空间的人为数不少:吉本芭娜娜喜欢下北泽一间“自由又狭窄”的小书店,呆在这家书店“就好像在自己的巢穴一般”(《关于下北泽》);《塔楼上》的主角中年导演“喜欢狭小的房间”,哪怕没有阳台延展出去连接邻街,也钟情于塔楼顶端局促的阁楼本身;《花束般的恋爱》中,八谷绢第一次去山音麦家,由他替自己吹干头发,小房间将两个人包围起来,酿造出心动的甜蜜和令人安心的归宿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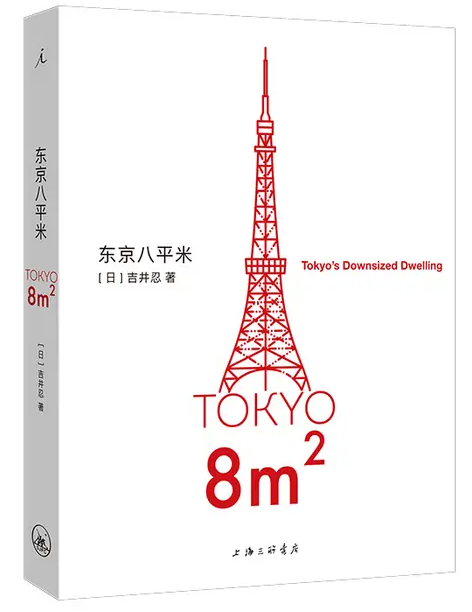
“蜗居”一直存在,必然有其理由。吉井忍对自己生活三年多的“东京八平米”进行梳理,写成了同名新书,从“回到八平米”“身处八平米”“走出八平米”“东京与八平米”四个维度,客观、真诚地描绘了八平米生活的多种面向,也由内向外审视了闹区中的独居生活。它有着人们期待的、吃苦打拼的一面,但绝非限制、不便那么单一。以最大优势——便宜的房租为例,不仅适合收入不稳定的自由撰稿人,且时不时闲置“蜗居”也不会觉得可惜,租客因此获得了常常出差的自由。如果能自我认同,“蜗居”也能散发精神富足的舒适感。“八平米”不是奇观,而像一种气候,反向塑造着住客的习性。
没有冰箱洗衣机的八平米
吉井忍的房间不设厨房和浴室,纯粹的布局和有限的空间强迫住在其中的人对物件的去留做出选择,大件家电首当其冲。要不要冰箱,吉井忍经过了一番权衡。有冰箱固然方便,对她的小房间来说则弊多利少。冰箱占据可观的面积、耗电、发出的噪音会被放大,搬家时大家电丢弃或转手的麻烦也促成了不添置冰箱的决定。一旦开始过没有冰箱的日子,吉井忍从买菜时就把握一人一餐的用量,至多用余量做成便当,尽快吃掉。她偶尔也去附近的料理店,或用便利店的三明治解决一顿。没有冰箱的介入,三餐也没有耽误,倒是维持着不囤货、买来就吃光的健康习惯,以及人和食物之间亲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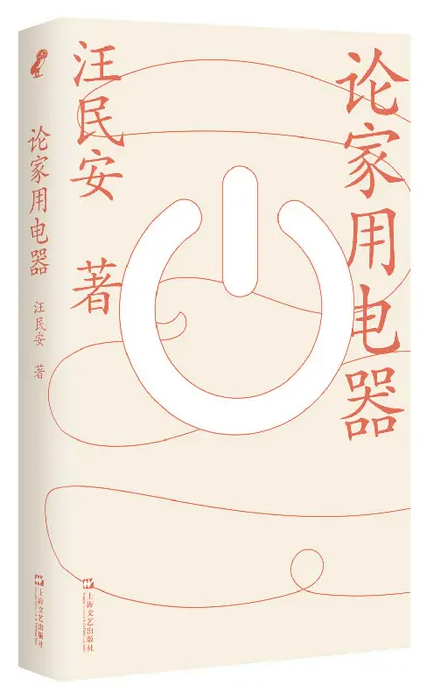
假如回头来读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中对冰箱的解读,就会更深入地赞同吉井忍的决策。他认为人们吃冰箱加工的大量变冷的食物,直接改造了肠胃的功能。此外,冰箱很容易让人产生盲区,人们出于节约的目的把食物放进冰箱,但这一举动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浪费。从冰箱中拿出来扔掉的东西,远比从中拿出来吃掉的多,也比没有放进冰箱而日见腐坏的东西多。冰箱的不可见性庇护了正在腐败的食物,从而成为食物腐败的根源。
这本对家用电器的洞察和剖析之书进一步指出,生活中的机器越来越多,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越来越闲暇。他以劳动和修养两种语义对家电进行划分,冰箱同属于这两种语义,洗衣机则当之无愧构筑了劳动的空间,它取代了人的工作,但也需要人的侍奉。家电悄然驯化、改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在休息和劳作这两个对立空间中不断转换。因此,摒除家电的房间,看似失去了房间的内核,实则也规避了大量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也算是一种拒绝被驯化、被改造的表态。没有洗衣机的吉井忍习惯去一家走路三分钟就到的投币洗衣间。带着洗好烘干的衣服,顺路吃完午餐回家,把劳作关在门外,享受还原为修养之地的家。
把人往门外推的八平米
洗衣机一旦进入了洗衣小铺之类的公共空间,劳作也有了休闲、社交的附加值。在洗衣机运行的节奏里翻完一本杂志,抬头看看陆续经过门口的行人,吉井忍享受身在世界之中的孤独时刻。如果小铺里还有别人,对话就有可能发生。汪民安怀念的,人们在固定时间走出家门、聚在河边,一起边洗衣漂衣一边聊天的社交活动,被家庭中的洗衣机瓦解了,又在洗衣小铺里复苏了。
当然,并不能对偶然的对话抱持太多与友谊相关的期待。有时对方过于主动强势,甚至让人无措和不适。吉井忍在投币洗衣间几次碰见一位近七十岁的阿姨,阿姨开门见山地问起她独居、婚姻等隐私,还因为突然进来了一个男人,就中止谈论自己、把话头转移到吉井忍的年纪上。一方面,吉井忍在承受陌生人唐突的好奇和忠告,另一方面,也听到了对方的故事。“我呢,离倒是没离,是逃出来的。”阿姨忍受了丈夫四十年,等到一个能掩饰开关门声音的大雨天,趁着丈夫睡觉,把事先收拾好的东西从窗户扔到路上,打车离家出走了。距今快十年了,她再也没听说过那个男人的消息。
钱汤的社交就更松弛了。“八平米”没有浴室,成全了喜欢日本钱汤的吉井忍。那里的老板也许是见的人多,对话很有分寸感。她只在门口番台坐着,每次吉井忍出入打上照面,就“打工结束啦”“泡完澡回家睡得舒服”之类寒暄几句。钱汤的其他客人,专注于自我放松,也很少用成篇的对话打扰别人。曾经有位女士在穿衣间主动和吉井忍打了招呼,却还没等到她回应就飒爽地离开了。吉井忍还因此对她产生了愉快的印象。这些人际关系好像一场雨,不必过分争取,只要身在其中就多少能获得一点。它们无关得失,却一次次加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走出“八平米”,吉井忍尽情探索和享受着东京这座城市的便利,外食、泡钱汤、洗衣、泡咖啡馆、打工,这些日常也结成了她的人际关系网。“八平米”与东京生活的关系令人想起瑞典电影《女孩和蜘蛛》。莉莎要搬离和玛拉同住的家,电影记录了这一过程。镜头很少离开她们的屋子,搬家工人、帮忙搬家的家人、朋友、楼上楼下的邻居、宠物狗和猫频繁出入其中,令视角流动。电影借房子里的一只蜘蛛为意象,将这些亲密又疏离的人们网罗起来,由此形成的张力在狭小的空间中膨胀,人与人的错身或进退间产生缝隙,渗透秘而不宣的情谊。一次次走出八平米,就好像电影的运镜,摄影机代替人眼,不断越过房间、从家中望向窗外,产生层次和通透感。封闭孤立的空间被全面打开,向各处伸展,和人情交融,变得有机又耐人寻味。
对长时间独处的人来说,气味相投的开放性关系,不至于疲于应付,也能建立他们和眼前世界之间的信赖。熟悉的店铺最容易变成这样的避风港。一家吉井忍常去的荞麦面店,竟然成了她和老板娘互相流泪宣泄苦闷的地方。有一次,老板娘送了吉井忍一盘天妇罗,说着有客人抱怨这个天妇罗有点酸,“停下了手头的事,掉了眼泪”。吉井忍一边回味着好像是有点酸,一边对着她的眼泪挺起胸膛保证说:“一点都不酸!”另一个晚上,吉井忍在地铁里绊倒,累积的疲劳焦虑令她被这根稻草压倒,钻进荞麦面店,就向老板娘哭诉。另一间是为了给附近早开工的工人卖咖啡而凌晨三点一刻就开始营业的咖啡馆。经营者大泽先生经历过战争混乱、经济增长和衰退、家庭的破裂与重组,总是边做咖啡边和吉井忍分享回忆。回忆之丰富鲜明让吉井忍惊讶,那间咖啡馆是一片过往之地,她在别人的回忆里游荡,避开了外面无奈的世界。吉井忍和大泽先生保持了多年的联系,有一次大泽先生一边擦着用了三十多年的咖啡机,一边猜测是机器先坏还是他先走。见吉井忍劝慰自己,反而加了一句,你别担心,总能找到替代我的人。
世界中心的八平米
自己的担忧被大泽先生看穿,吉井忍感到吃惊,也意识到:“早晚要面对现实,并给自己一个答案:离开日本二十年后回国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京八平米也是吉井忍心中的一块领土。年轻时她辗转于成都、上海、北京,住过的房间有三十多个。拮据时她和丈夫住在北京一间毛胚房里,丈夫舍不得午餐开支,吉井忍就随手做便当给他带着,由此诞生了《四季便当》。后来丈夫“找到真爱”,两人离婚,吉井忍只身返回日本。在“八平米”里住的三年,也是她离开中国之后亲手建立起的另一种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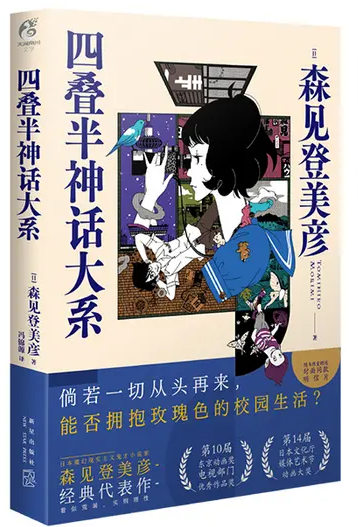
吉井忍一直在强调“小”与“大”的依存关系。八平米是四张半榻榻米的面积,是“小”;而四叠半是含有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是“大”。森见登美彦的小说《四叠半神话大系》也将四叠半大小的宿舍作为原点,想象和重启了加入不同社团的不同大学生活。吉井忍重建生活的原点就是这八平米,面店、钱汤、洗衣小铺、咖啡馆……都在她生活的延长线上,东京的繁华提供了她在蜗居外自在的生活。住过三十多个房间之后,吉井忍已经可以回到四叠半的原点,似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第一次走进这个小房间,看到东边南边都有玻璃窗,她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小,“那是一种脱离物质束缚的自由感”。小房间宽敞的即视感在吉本芭娜娜《关于下北泽》的回忆里也出现过。一家熟悉的店铺在营业时,让她感到非常宽敞。店主夫妻二人几乎都在室外的地方做着生意,那里总是灯火通明,各种蔬菜摆放得整整齐齐。后来店铺关闭,她才发现那个空间“真的是如此狭小”。小家会越住越大,我们有理由这么相信,这是因为有人的力量。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