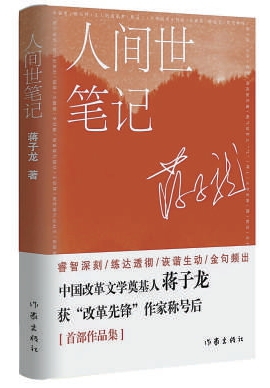

从1965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新站长》算起,文坛老将蒋子龙已在文坛跋涉57年。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更被视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也令他一夜成名。
已过耄耋之年的蒋子龙近来陆续出版小说集《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人间世笔记》,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诙谐练达。同是天津作家的林希与蒋子龙相熟,评价对方“是一个不说绕脖子话的人,一条硬汉”,这在他后期的散文中尤其突出。比如《故事与事故》,将社会万象里的合理与悖理、有益与无益,作了极准确的解析,由此,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严肃的社会责任感,还有文学真实的可能。
1.“念故事的人”
蒋子龙清晰记得自己青年时代听过的苏联歌曲《小路》里面有一句歌词“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他的文学之路便是如此。
上到小学四年级,蒋子龙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蒋子龙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他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蒋子龙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往下念。”直到他的眼皮实在睁不开,舌头打不过弯来,二婶赏给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
由于蒋子龙这种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闲书”都往他手里送,蒋子龙可以先睹为快,渐渐看书成瘾。他常想,自己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说来有趣。蒋子龙成为作家,全因一则赌约而起。他在天津读中学时,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他投给《天津日报》的退稿钉在墙上,还语带讥讽:“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作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不服气的蒋子龙到图书馆拼命看书,一个人躲到铁道边的林场深处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社,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遭遇惨败之后,蒋子龙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考进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后来分配进了国家重点企业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蒋子龙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后就当上了生产组长。
正当蒋子龙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海军来天津招兵,凡适龄者必须报名并参加文化考试,蒋子龙竟考了个全市第一,招兵的参谋对工厂武装部部长说:“这个蒋子龙无论什么出身,我都要定了。”参军入伍的蒋子龙又步入海军制图学校继续上学。“那时从京津沪招了一批中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学习测绘,毕业后绘制领海图。渐渐地我的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
因为学习成绩好,蒋子龙在海军制图学校当上了班长。那时部队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月月有晚会。蒋子龙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都得编几个小节目。演过两回,领导认为他还能“写两下子”,遂叫蒋子龙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无所不写。
有一次到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起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让我心里发生了一阵阵战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蒋子龙想,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文学,当下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
过去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而投稿,此时,他才意识到,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是件异常严肃而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1972年,《天津文艺》创刊,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
“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我舍不得丢掉文学,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专业,每经过一次磨难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学。”蒋子龙说,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造本身,是执着求索与痛苦研磨。他的人生就这样被文学“绑架”了。
2.成名作曾屡陷风波
初涉文坛,又是“工厂业余作者”,蒋子龙起初的几部小说,屡遭争议。
《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是姊妹篇,没有“一天”,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
“文革”结束后,蒋子龙从被“监督劳动”的生产一线调出来代理工段长。由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将涉及大型发电机的转子交由他们车间锻造,便让蒋子龙列席这个大会。会间,原《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在会场找到他,说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年初复刊,约蒋子龙为复刊第一期写篇小说。《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想登上去的文学圣殿,可蒋子龙当时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不敢太过兴奋,因为心里没底,只是答应试试看。
话虽这么说,丝毫不敢马虎的他白天开会,晚上通宵开夜车构思,会议期间完成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刊登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不承想,小说很快被界定为“宣传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以至于他一度下决心不再写小说。
“文革”结束后,在工厂的蒋子龙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蒋子龙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幸好正掉在炉件旁边一堆装过炉件的空稻草袋子上,否则就没有后面的“乔厂长”了。
这一年,蒋子龙得了痔疮,去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三天,病房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外面正下大雨,她淋得像落汤鸡,进门就鞠躬,向我赔礼道歉。”蒋子龙一打听,才知道是《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先是找到工厂,又从厂子找到医院向他约稿。蒋子龙被感动了。他开始构思,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小说里,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小说后来改编成影视剧播出,著名演员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乔厂长”,同样引起轰动。
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境遇一样,《乔厂长上任记》也曾招致批评。这时候,蒋子龙反而不怕了。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就再写一个短篇。下班的路上,蒋子龙买一瓶啤酒,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吃过晚饭,就在厨房里写小说。当天晚上写完,第二天看一遍改一遍,再誊清寄走。
那段时间,蒋子龙出作品最多。批这篇,还没批完,下一篇又出来了。“他们瞄准了火车头,可是火车开了,放枪只能打到车尾,有时还没打着,这一篇还没有批透,新小说又出来了。”蒋子龙的“游击战”打得好不痛快!那时期他先后写下《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我获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蒋子龙说,和《人民文学》结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这话不假。《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蒋子龙也被誉为改革文学奠基人,2018年更是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3.文学王国与《农民帝国》
蒋子龙当年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早已不复存在。当年所谓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像“天津重机”一样淡出公众视野。
可蒋子龙依然在关注工业。每年,他都要下几次工厂,有时候是他熟悉的机械行业,有时候是完全陌生的电子软件设计行业,更多的时候,他走进工人们中间,和工人聊天。可是他悲哀地发现,交流的话题越来越有限。
蒋子龙所在的小区附近建公园,看到有工人在焊不锈钢管,一种亲近感让他不由自主走上前。他一看大失所望:好的焊点像鱼鳞,像花纹,可是这工人的焊缝却歪歪扭扭。蒋子龙问:“你是几级工?”对方说是五级工。蒋子龙说:“你要是五级工,我就是十五级工了。”
机器可以买国外的,但是技术队伍买不来。他特别希望像农村调查一样,搞一次工业调查,多跑几个像造船厂、机床厂这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中国目前的工业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他说,自己还要写一部关于工业的作品,希望用作品证明工业振兴的源头和力量。
十多年前,67岁的蒋子龙出人意料地以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冲击文坛。“我在农村待了十四年,在城市待了六十多年,仍觉得不能融入城市。”来自农村的蒋子龙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农民。
评论家惊呼:蒋子龙转型了,他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车间转向村庄,从工人转向农民。面对这种所谓题材上的重大跨越,蒋子龙却颇不以为然,“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不会去局限题材的。我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三十多年来,我的笔尖触摸到了演员、医生、工人等等,原因就在于我对什么样的人有感觉就下笔,我的写作不分题材。”他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这是情结,也是一种责任。”他笑言,自己现在做梦,与城市有关的都很少,即便做了也记不住。
为了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农民,蒋子龙看了很多哲学书,他想找到一个看透生活的工具。但是一到动笔却很困难,“老想写出几十年来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得失,写来写去就写不下去。”直到后来想明白一个道理:写的是小说,写小说就是写故事,何必在思想上找?“一个作家很奇怪,写了大半生小说,仍然会因为卡顿而耽误进度。”
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农民帝国》里,人们习惯称财大气粗的农民为“土皇上”,小说主人公郭存先打心底认为去掉“土”字就是皇上,他要创造一个“帝国”——这就是他的全部人生情结,而瞧不起农民的也正是他自己。在当今现实里,怀有郭存先式“农民情结”的又何止他一人?
写作《农民帝国》对蒋子龙来说是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跨越,但是,面对已经在农村题材上耕耘了很久的作家,蒋子龙仍有信心,“我的语言氛围是典型的河北味。那么多高手,我可能写不过他们,但我和他们的味道不一样。”为了写好主人公,蒋子龙研究过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但为了避免“对号入座”引来麻烦,他极力模糊人物原型的影子。他要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
4.“人泡在生活里”
蒋子龙书中有这样一幕场景:法庭上犯罪嫌疑人有意为难法官,说了句“炮打旗杆顶”,法官接话道:“雷击小和尚”。这两句是蒋子龙的一位泳友在淋浴时讲的,其他泳友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蒋子龙怕忘记,带着一身肥皂沫跑到更衣间拿笔记下来。
这种事很多。蒋子龙说,灵感从哪里都可以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就是等不来,求不来。常常是越想有灵感,灵感偏躲得越远。作家也是普通人,只是比不写作的人在生活中多留几分神、存点心,换句话就是“人泡在生活里”。
《人间世笔记》里很多内容取材于各路新闻,但是蒋子龙从不到网络上获取写作素材。“网络、微信上的东西时效性极强,一出来顷刻成旧闻,不具备文学品性。以前我有剪报的习惯,有时我会翻翻那些旧资料,若还能让我心动,便会咂摸其味道,如能激出我思想的火花,就可能成为素材。”
他始终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尤其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因为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不过这个过程也需要有编辑助力。蒋子龙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批好编辑,像秦兆阳、苏予、许以等,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他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国内文坛也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没有龙世辉就不会有《林海雪原》,没有萧也牧就不可能诞生《红旗谱》。
在蒋子龙眼中,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把自己当宝贝;一种是把自己丢掉,又找了回来。前一种比如杜拉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而他本人,自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不知不觉中一直在丢失自己,从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到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全都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直到可以掌握手里的笔,他才开始慢慢找回自己。
回顾八十年人生,蒋子龙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还没有丢失做人原有的善良,没有以自己的性格去过一种快意恩仇的生活。“我创造了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文字。若说有遗憾,是没有把该读的书都读完、读透,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都写出来,而且写得更好。”蒋子龙说,达不到自己心里的那重标准,不只是遗憾,还很痛苦。
人活着是要不断总结的,到老年系统地回顾一生,写本自传,留下自己一辈子的感悟或是教训,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须写的一本书。几年前就有朋友劝蒋子龙动笔,但他至今还没有想好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年轻的时候,蒋子龙兴趣广泛,在篮球队打过中锋,乒乓球曾赢过天津工人代表队一号种子选手,吹拉弹唱也能替补登台,还喜欢京剧、河北梆子,年轻时胆大能喊两嗓子,可是现在不敢了……
他觉得,文学创作有很强的排他性,自从把精力转到写作上,其他爱好渐渐全丢弃了。不过,他一直保留着“多听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企业、下农村,轻易不会放过,朋友聚会也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如同灵魂透气,一大快乐。还得泡在生活里!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