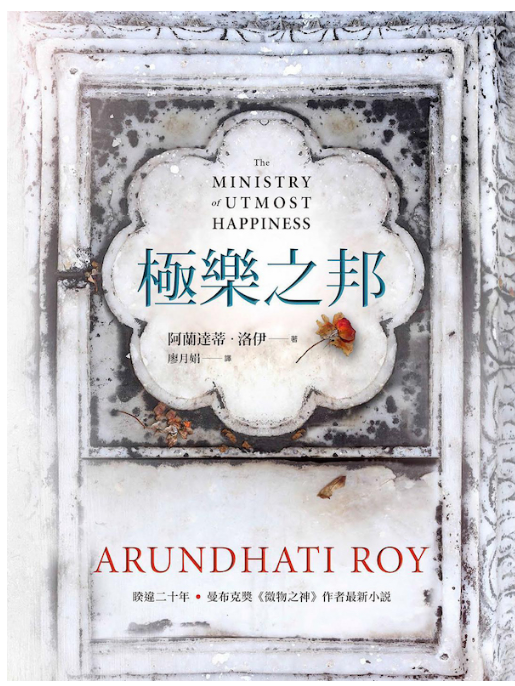
《极乐之邦》,阿伦达蒂·洛伊著,廖月娟译,天下文化2017年8月出版。
对见证了世界足够荒诞的那一面的人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这是阿伦达蒂·洛伊的遭遇。
二十年前,当时不过二十岁的南部马拉巴尔海岸出身的女作家,凭一部《微物之神》,初出茅庐便夺得布克奖。二十年后,洛伊带着她的第二本小说《极乐之邦》回到文学评论家的视野。“二十年磨一剑”听起来足够动人,仿佛孤独的文字匠人。然而,《极乐之邦》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学出走的洛伊在二十年里积攒了厚厚一沓著作,主要是些时评文章、政治分析、思想整理。这些文字无所谓什么精巧构思和深刻雕琢,它们松散、直白、翻着毛边,看得出有些是形势逼人而草草落笔,有些完全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产物,是彻彻底底的意识形态论辩,有些则是一腔热血的大声疾呼——什么应该重视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尔而圣雄甘地其实是个反动的角色,什么博帕尔毒气事件的遇害者为何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除此之外,是一个个现象一个个人:纳尔默达河的原住民抗争,东部丛林中和部落民一起打游击的武装反叛者,愈发威权、野心勃勃和不宽容的印度政治,席卷而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番红花色浪潮……她批评印度的种种问题,批评西方的帝国主义,把自己变成一颗刺头,并且还因此而一度暂入囹圄。
《极乐之邦》不太像一本小说,更不用说它无关许多作者心心念念的作品情怀。它不是这样一件东西。它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因为精巧地希望不落俗套,而是很纯粹自然,像是作家二十年来的笔记簿。和那些非虚构文字的最大不同是,在《极乐之邦》里,洛伊选择让自己的战斗者形象暂时退出。
这种退出一开始有些生硬,小说有许多不加修饰雕琢的痕迹,比如洛伊过于“政治正确”乃至几近迂腐的底色,在《极乐之邦》开头的几章里格外明显,那是最容易抓住眼球、最能为当代读者理解和吸收的部分,但也显得最像她一切专栏文章的同款调味。就像一道融合菜,吃货总能兴奋地品尝出自己熟悉的口味:主角是穆斯林跨性别人士安竺(尽管她是印度传统中的海吉拉Hijra而非西方意义上的跨性别者),配角是贱民“萨达姆”与印度政客们。故事的舞台一是“9·11”事件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古吉拉特族群暴力,故事的舞台二是2011年(存疑)的全国反腐社会运动。你能想到的主流社会之外的角色都被归拢在情节推进中,眼见着那个令人熟悉的,眼花缭乱的,充满了混乱和冲突但又显得颇有各种可能性,能够同时容纳贪官污吏、变性人和瑜伽嬉皮士的印度就要呼之欲出,却突然间又戛然而止了。故事跳到了喜马拉雅山谷中的斯利那加,跳到了印控克什米尔。随着这一跳,《极乐之邦》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跌出左翼政治理解范围的重量。
这是《极乐之邦》的与众不同的“下半场”。
关注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是印度左翼的某种政治正确。以至于在一些人看来,左翼过于关注克什米尔发生的国家暴力问题属于策略上的不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领土争议,已经无可挽回地混合了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被公共主流舆论转化为一小撮克什米尔民族分裂分子或伊斯兰圣战者,与大印度梦想之间的冲突。对四分五裂的印度左翼来说,关注克什米尔,意味着完全放弃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共处,近些年他们更是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大打经济牌,被扣上了一顶反对经济发展的帽子。这是需要面对选举政治的印度左翼所难以承受的。2016年以降,正是通过操作克什米尔议题,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得以在尼赫鲁大学中壮大支持自己的学生组织,配合内政部的行动,在舆论、司法和行政上三管齐下,成功压制、削弱了学界和媒体中的左翼传统。

2010年9月13日,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抗议人群中一个小男子大喊独立口号。
克什米尔的暴力,今天回头看来,是记忆中那仿若黄金时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潜伏的无数暗流之一。从1987年选举失控开始,克什米尔人聚居的首府斯利那加周围就烽烟四起。抗议、武装冲突、渗透、反渗透、镇压、复仇,直到世纪之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战争。在这十年里,卢旺达发生了屠杀,巴尔干半岛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战火中迎来了杀戮。但是克什米尔的痛又有所不同,它发生在一个以实行民主制度自豪并且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和平国家中。十年之间,数万人“失踪”,其中许多人的下落永远也没人知道。
那是一个恐惧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政治广泛结合的时代。这些地方像是一根试管、一张试纸,测试着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后人们会走向何方。恐惧的政治诞生于两极意识形态对垒的退潮、消解,它把一切都转化为文明冲突式的语言,其中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想象为全人类适用的终极意义,把任何对这种生活的剥夺视为撼动自己的根本价值——生活方式、语言习惯与想象现代世界的方式不同,都变成了生死存亡式的冲突,每跨出一步都变成了对底线的突破。
洛伊已经是印度右翼口中“反国家”阵营的一员,她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但《极乐之邦》值得咀嚼之处是洛伊似乎“出走”了。当小说遇到斯利那加周围的高山谷地发生的一切时,她没有选择最轻松、最容易代入的语言,没有直白伸冤或呼吁同情。她拉开一大段距离,抽身前往远处,但却又因此得以贴到最近的地方,用最细腻的笔触描摹其中的灰暗、混沌与荒诞。我们时代的荒诞感就像一只飞蛾,被洛伊做成标本,虽然凝固,却仿佛还扑扇着翅膀。
人在极度高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今天会变成荒诞。发生在联合审讯中心的一幕是一个例子。女主角之一的蒂洛和已经成为武装组织领导人的老同学、克什米尔民族主义者穆沙相互倾慕,他们发生关系,穆沙遇军方追杀,蒂洛被抓来询问。情报机构的老同学老情人何巴特策动着享受调查记者道德光环的纳嘉去营救她。纳嘉也爱她,并且讨厌穆沙,他想救出蒂洛。军方心怀鬼胎,只要调查记者按照需要写一篇报导带动舆论,一切就都办得妥妥当当。小房间之外,军官们享受着和猎物追逐并讨价还价的戏码,用一盘盘点心和一个个恐怖的微笑,提醒小屋里的人谁才是真正的话事人。最弱势的是那个绑在椅子上的武装分子,他以为自己将要成为烈士,并且会有人写他的事迹,殊不知他的生命和故事已经被拿来交换了好几轮,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在计算他的价值。一场利益交易,一场猫鼠游戏,一场权力表演,也混合着奇怪的感情选择。蒂洛这个角色成了所有拧巴关系的投影。
发生在克什米尔的暴力的荒诞在于,人们最后找不到谁是施暴者,谁是受害者。在克什米尔,冲突远看发生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前者是克什米尔人而后者是印度政府,但拉近镜头,这一切都模糊起来:世俗派乃至社会主义派的克什米尔民族主义精英,被受中东影响的圣战分子武装暗杀;印度军警杀死圣战分子;克什米尔公务员两头不是人:民族主义精英唾弃他们,军警怀疑他们,圣战分子杀死他们;洛伊暗示,还有权势一方养寇自重,有意让问题不可解决。所有人都是咬着尾巴的一匹接着一匹的狼——亲人和朋友随时会在莫名的压力下捅自己一刀,敌人却有时展现出惺惺相惜的温情。而等一切落定,克什米尔人死于克什米尔人之手,民族主义者死于圣战分子之手,圣战分子死于同僚之手,负责照名单杀人的强力部门人员不知道是如何死亡的。又或者所有人都活着,却不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活了下来。
洛伊让蒂洛收藏了一本《幼儿英语文法和阅读文摘》,这是一出戏中戏,笔记中的笔记。这个题目下是穆沙收藏的心酸而荒诞的故事:一个向往去国外接受训练的克什米尔男孩为了先得到足够的钱,供出三名武装分子给准军事部队,最后因为参加武装组织死在后者枪下;一个圣战士党指挥官被杀了,调查的警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最后军警准军事部队成员宣布是他们干的,获得了一大笔政府赏金,一周之后圣战士党的二号人物被发现死于枪杀,原来是他夺权时杀死了指挥官,结果被忠于指挥官的武装人员杀死,这个故事最后被报纸写成“无辜的平民被圣战分子杀害”……
在高压和频繁的暴力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片灰色。它显得像是大史诗末尾俱卢之野的毁灭的战争,没有人是胜利者,所有道德和法则也都被摧毁了。洛伊试图提醒读者的是,在这场战斗中,所有人都是普通人,驱动他们上场撕杀的并不是什么恐怖的原则,而是最简单的情绪:恐惧、愤怒、憎恨、贪婪、犹豫,这些构成灾难的质料从未远离我们,它只需要合适的条件就可以生长。可是,它们生长的环境恰恰又需要否认这些质料——只有当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善恶分开两个世界并且鉴别出敌人和自己人的时候,俱卢之野式的虚无才成为可能。
洛伊笔下的这些政治灾难,背后几乎是死结:印度希望在克什米尔展示自己的体制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的能力,希望在克什米尔建立国家认同,但印度的体制和认同,却和印巴冲突,和印度教/穆斯林的二分的身份冲突越来越难以分离,在莫迪时代,就连经济发展也登上了同样一驾战车。
克什米尔这样的危机的另一面,是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整个社会彻底撕裂成两大阵营直接冲突、划分敌我、互相屠杀的巴尔干,但它却很可能浸润在慢性的、像癌症一样致命却不迅速致死的暴力之中。这种暴力正是来源于避免它成为巴尔干的力量——投入其中的试图让它稳定的力量,把令人生畏的决裂与对垒细细分解到每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分解到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关系中,让它不再有社会性的杀伤力,暴力几乎变成了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变成每个人都瞪大眼睛寻找敌人的想象力比拼。故事中穆沙的女儿就死在这样的场景中,一场发生在斯利那加的街头抗议,因为远处一辆车压爆了一瓶芒果汁而被误认为是有人开枪,最后血流成河。
洛伊多年来投身印度的草根政治。《极乐之邦》里,她在笔下还原了这些年新德里政治的无数场景——曼莫汉·辛格政府经济学家式的枯燥讲话、安纳·哈扎雷充满表演欲望的反腐败民众运动;政治新星“普通人党”领袖凯吉利瓦尔德的平庸。政治总是给人带来希望又快速落空,就像曾经席卷德里市议会的普通人党,曾经被寄希望于成为印度两党政治之外的一股清流,如今却丝毫无法迈出德里,领导层内斗不休。
洛伊的文学不寻找政治的出路,尽管她的时评永远都在寻找政治出路。记录,描述,并且身处其中,是《极乐之邦》里洛伊对“文学何为”的解答。文学置身荒诞之中,游离而漂泊不定,困惑而自我怀疑——蒂洛永远在怀疑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她热忱而天真地投入政治,热忱地活着,又明知道对发生的一切也许并不能做到什么,只有像个儿童,把一切都当成发生中的童话故事,人才能不至于冷漠地转过脸去,或是捶胸顿足地丧失信心。把经历的荒诞变成童话的语言,“极乐”就有了一种不喜不悲的况味。也许这就是这个荒诞的时代中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注定状况。我们都是如此荒诞地活,如此荒诞地爱,如此荒诞地进入,或成为历史。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