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1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着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很早就发现,许多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象,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余光中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散文了。慢慢地,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录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绝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并有力地为文字挽回了神圣感。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七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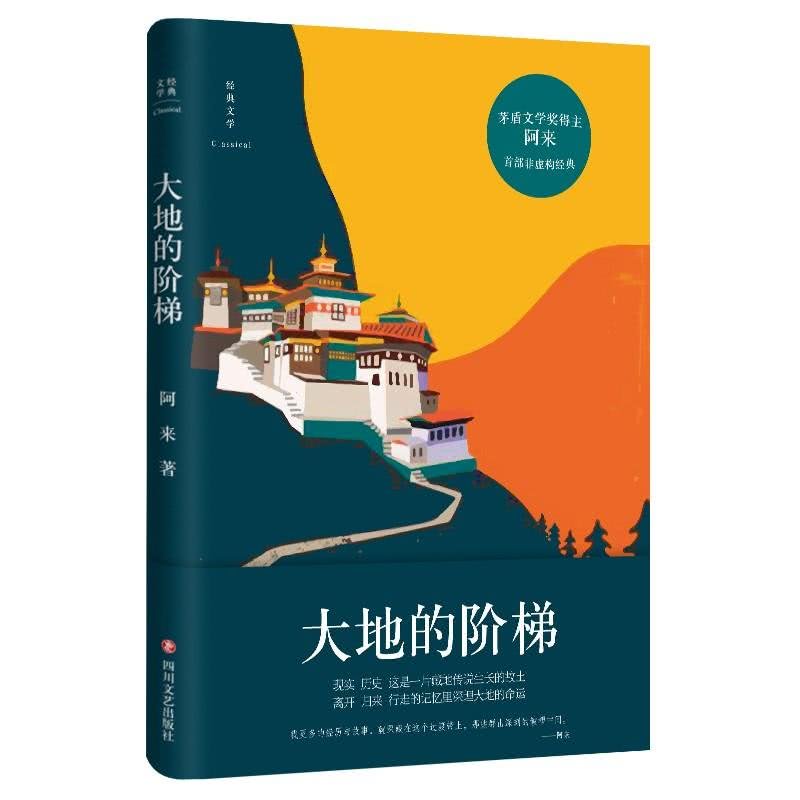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试看以下这段文字: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小喇嘛突然开口说:“我知道你的话比师父说的有道理。”
我也说:“其实,我并不用跟他争论什么。”但问题是我已经跟别人争论了。
年轻喇嘛说:“可是我们还是会相信下去的。”
我当然不必问他明知如此,还要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不出理由。
“其实,我相信师父讲的,还没有从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见的多。”
我的眼里显出了疑问。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犹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阶梯,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这个年轻喇嘛如果接受与我一样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个诗人。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方也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不是要与我讨论什么。这些山间冷清小寺里的喇嘛,早已深刻领受了落寞的意义,并不特别倾向于向你灌输什么。
但他却把这样一句话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上。2
这是作家阿来在一篇题为《离开就是一种归来》的散文中的一段文字。这篇散文,在初读的时候,会觉得一切是那么平常,并无多少意外的惊喜。但是,如果多读几遍,慢慢地,就会发现,小喇嘛的那段话居然使一个对多数人来说悬而未决的信仰问题瞬间就释然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字的境界吗?把一层一层的山比作“阶梯”,并说“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如此令人难忘的表达,使“我”以上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信仰更多的是指向世界的奥秘状态,是生命的一种内在需求,它并不能被理性所证明或证伪,因此,辩论对于信仰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小喇嘛说出“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时,他已经悄悄地从辩论的理性漩涡里出走,来到了生命直觉的现场,或者说,大自然的奥秘轻易就制服了他心中还残存的疑问。
阿来记下了这个难以言说的精神奇迹。它也许只是一句话,但作家的心灵捕获到这句话的分量时,他的文字就与这句话中广阔的精神空间紧密相连,散文也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轻浅的外表,成了内在心灵的盟友。这使我想起诗人布莱克的著名诗句:“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在一朵野花里看见天堂,/把永恒放进一个钟点,/把无限握在手掌。”“一粒沙子”是轻的,但“宇宙”是重的;“一朵野花”是轻的,但“天堂”是重的。散文的轻重关系,似乎也是这样:在它所记述的事情和人物里面,也许仅仅是一些常识,但作家要提供一个管道,使读者能从常识里看见“永恒”和“无限”。也就是说,散文的话语方式可以是轻的,但它的精神母题则必须是重的,它的里面,应该隐藏着一些可供回味的心灵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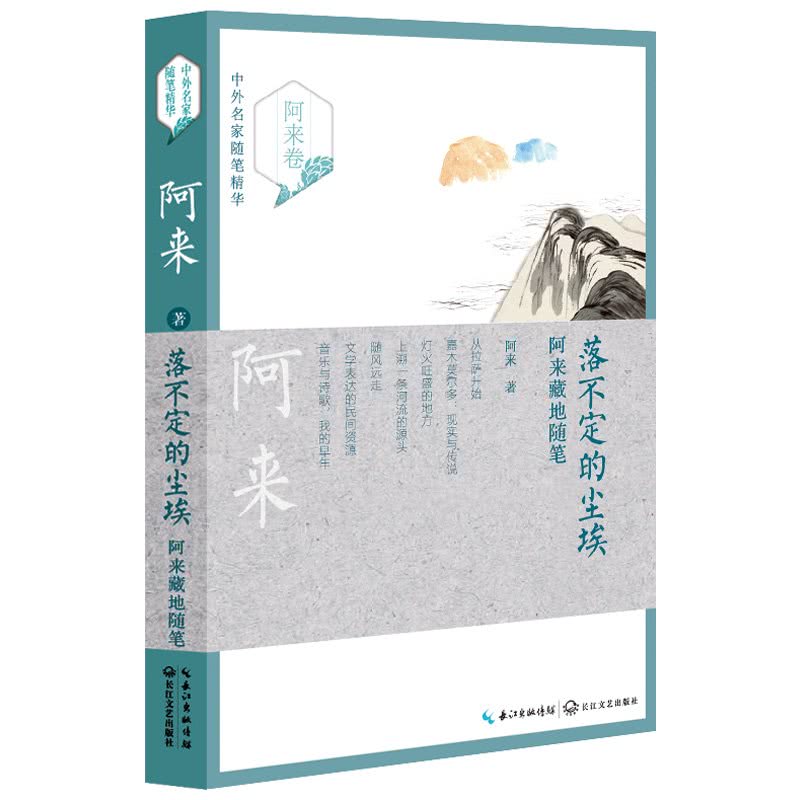
阿来散文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散文的轻与重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本来,像他这样的藏族作家,写起宗教和西藏,是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的,话语方式上也很容易变得作态,正如其他一些作家那样。但阿来没有这样,因为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已经了然于胸,它们已经内化到了他的生活之中。我记得他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叫《西藏是形容词》,目的是为了还原真实的西藏。他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名词。”“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了许多主观的东西,而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3“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4
阿来对西藏的态度,其实也可看作是他的散文立场:反对概念化和附会,追求“以双脚与内心丈量”故乡大地。比如西藏,这本是一个“重”的命题,但太多的膜拜者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过于沉重和神秘的地方,真实的西藏实际上已经远去。这个时候,写西藏就不该使它变得更“重”,而是要从西藏的神秘里超越出来,走进西藏的日常生活,走进西藏的人群,重新找回西藏的真实。可以说,此时,本真的西藏、不神秘的西藏反而成了西藏真正的“重”之所在,因为这样的“重”不是附会上去的,而是从里面生长出来的。这就好比阿来在《怎样注视自然》一文中所提到的“自然”问题。当大多数人都把自然当作抒怀的对象的时候,人们会发现,那个被彻底遗忘了的自然本真才是自然的“重”之所在。他说,《话说飞鸟》一书的作者儒尔·米什莱“在历史研究之余,把眼光转向了大自然。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残酷的,而法国南方的地中海岸,自然却呈现出和谐美妙的景象。于是,他便乐而忘返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一次次地发生过。
很多学人被宫廷放逐,如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等,等等。他们处于江湖之上便寄情于山水,写出了很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比如《永州八记》《赤壁赋》和《岳阳楼记》。但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是借景抒忧愤之情,其兴趣还是在人文政治,而不是真正想要认知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本身的特性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注视自然的时候,也是返观内心,在自省,在借物寓意;而在米什莱们那里,注视自然,便是真正认识自然、阅读自然,并让自然来教育自己。”
把自然还给自然,把西藏还给西藏,这似乎一直是阿来写作中的内在愿望。他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文字中又无时不在地洋溢着和广阔天地的交流和私语。即便是那些科学美文,阿来也不忘把读者引向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比如,他写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时说:“从此,这个世界上便多了一种时时想把天空看得更清楚,更深远的人。”5.“我们的视线在穿越空间的同时,也正在穿越时间。”6他写藏族人的生活时说:“通过这些故事和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和激情。”7我想,正是阿来身上这种对事物的内部意义穷追不舍的精神,才最终使他的文字从平常走向了深邃,从轻走向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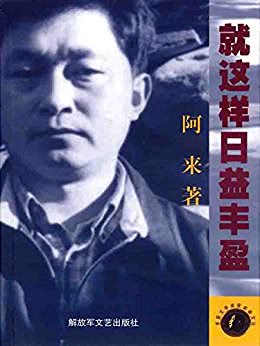
阿来原来是一个诗人,我们或许能从他对聂鲁达和惠特曼这两位伟大诗人的感激中,窥见他的写作秘密:
感谢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感谢音乐,不然的话,有我这样的生活经历的人,是很容易在即将开始的文学尝试中自怜自爱、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中国文学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8
“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这样的美妙言辞,已经很少有作家说得出来了。而正是因为少了“雄伟的存在”这一“重”的维度,才导致现在的文学越来越轻,越来越站不稳,以至沦落到了话语垃圾的悲惨境地。阿来曾经引用佛经上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和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9阿来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有声音的写作,这些声音,可能发自作者的内心,也可能发自山川和草木,因着有那个“雄伟的存在”,每个字都可以说话,每种生物都可以歌唱,关键的是,你是否有那个心和耳朵来倾听它。
这个声音,其实也就是好散文所需要的隐秘维度。它的存在,将使散文的内在空间变得宽广和深刻。而现在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作家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想象的空间;而一种没有想象的散文,必定是贫乏的散文。因此,我认为,好的散文,有重量的散文,它除了现实和人伦的维度外,至少还必须具有追问存在的维度(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何在)、超验的维度(和无限对话的维度,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和自然的维度(包括大自然和生命自然)。也就是说,只有多维度的声响在散文内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散文的价值空间才是丰富的、沉重的。阿来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散文,一种有声音的散文,也是一种重的散文。它的重,就在于他那干净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人生和存在的追问。
在散文界泛滥着太多轻浮和浅白文字的年代,让散文写作恢复一种重的向度,显然已经非常必要。

作家阿来
注释:
1.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文集》第八卷,第33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阿来:《离开就是一种归来》,《就这样日益丰盈》,第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阿来:《西藏是形容词》,《就这样日益丰盈》,第13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阿来:《西藏是形容词》,《就这样日益丰盈》,第136—13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阿来:《视线穿越空间与时间》,《就这样日益丰盈》,第15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6.阿来:《视线穿越空间与时间》,《就这样日益丰盈》,第15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7.阿来:《视线穿越空间与时间》,《就这样日益丰盈》,第29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8.阿来:《从诗歌和音乐开始》,《就这样日益丰盈》,第247—24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就这样日益丰盈》,第29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