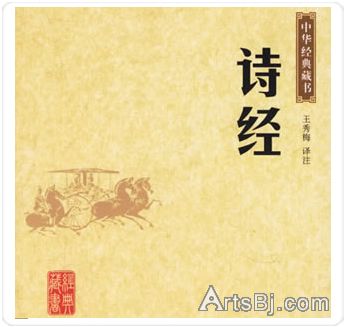
《诗经·郑风》里,有一首题名《将仲子》的诗。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
这是一个女孩子,对邻居家的二哥,屡次三番地跳墙过来,与她相会,向她示爱,实在不胜其烦,便求他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不要来打扰她了。古时,二十五户为里,有里墙围着,住户的院子,有院墙围着,见面的园子,有园墙围着。这位二哥,黑灯瞎火跑来,要跨越三道防线,免不了手忙脚乱,撞折树木,捅了娄子。
由此可知,在《诗经》的年代,墙就出现了。
这应该是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遗址证明,蒙昧时期,穴地而居,人类无需用墙隔开。只是有了怕别人眼红的资产,有了怕别人知道的隐私以后,墙才派上了用场。所以,严格地说,墙是私有制的产物。
通过这首诗,我们知道墙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挡的作用,使那个执着的求爱者,难以长驱直入;第二,保护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种植物,身处墙内,便有了相对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于她的父母兄长,究竟是认可他俩结合呢,还是坚决要拆散,墙外的那个邻家二哥,是休想了解到女方家庭的态度的。
据清人凤韶《凤氏经说·墉墙》:“古者屋下柱间墙曰墉,屋外四周墙曰垣,垣即所谓宫墙也。垣、墉皆得称墙,而墉不得称垣。”无论为墉,为垣,为墙,只要是能使空间一分为二的措施,都意味着内外的区隔,人我的轸域。实体的墙,如此;虚拟的“墙”,也如此。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作“Great Wall” ,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住了中国人建筑学的要义。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发数十万戍卒修长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朝历代的帝王,在这“墙”上没少下功夫。
中国人的筑墙,防卫外来者的同时,很大程度也是将自己紧闭住了。所以,四合院的要义,必垒四堵墙。这墙,就是居住者与外部世界的界限。王公贵族的府邸,高官显宦的豪宅,是用围墙围起的大型四合院;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墙、护城河围起的巨无霸四合院。老北京城,一个由无数四合院组成的城市,也是一个无数堵墙林立在你眼前的城市。北京城里,那磨砖对缝、敦实厚密的四合院,为什么所有的外墙窗户,既高且小?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门户,虽设常关?
由此可知,中国人造墙的目的,在于“隔”, 物质的墙,起到分隔、间隔、区隔的作用;精神的墙,产生隔离、隔膜、隔阂的影响。如此,四合院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了。第一,重门叠户,莫测高深;第二,内敛外藏,自我封闭;第三,狭隘局促,关门独大;第四,壁垒心态,害怕开放。这种内向的、自恃的、扃锁的、局限的居住方式,几代人、几辈子地拘束在这四堵墙中,久而久之,对居住者的思想、意识、观念、精神,会不会产生《淮南子》所言“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的影响呢?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逻辑推断,墙,这个东西,壁立于前,环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觉,哪来开阔的胸怀呢?
明清两代,之所以闭关锁国,自我隔绝于世界文明,畏之避之于时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以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国列强,与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墙的束缚拘囿,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何况,紫禁城的墙,更高,更厚,更坚固,更严密呢!
然而对长期生活在四合院的老百姓来说,这四堵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蛹在茧里,自我束缚,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僵蚕,成为蛹干,只有破茧而出,才能化蛹成蝶升华,开创新天新地。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