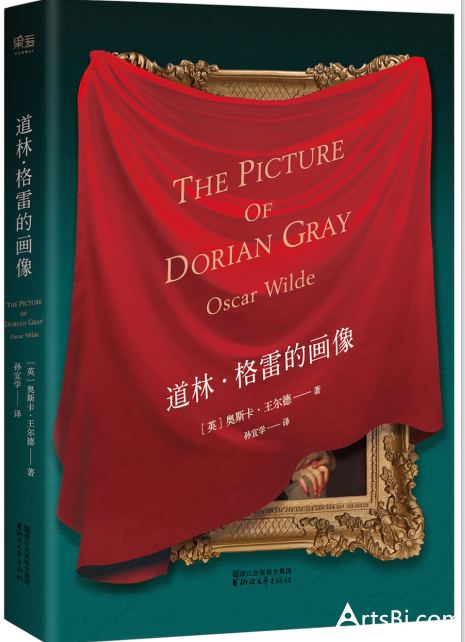
《道林·格雷的画像》
作者:奥斯卡·王尔作德
译者:孙宜学
外文书名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内容简介(产品描述):
少年道林·格雷相貌俊美,心地纯良。朋友霍华德为他画了一幅绝美的画像,而亨利勋爵的一席话让道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和美。他不禁感叹:“真悲哀啊!我会变老,但这幅画将会永远年轻……如果能反过来就好了!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不料一语成谶,道林不仅永葆青春,犯下罪恶也丝毫不改他纯净的面容,而画像愈发邪恶丑陋。当欲望得到放纵,罪孽覆水难收之时,道林欲杀死过去,举刀向画像刺去,一切都结束了……
编辑推荐 本版《道林·格雷的画像》由资深王尔德研究学者孙宜学老师翻译,译文忠实原文,优美流畅。 作为王尔德唯一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他艺术化的自传,和不幸命运的前奏。犯罪、惊悚、男主人公之间的暧昧情愫……这个构思精妙、想象丰富的故事背后是王尔德关于艺术、爱情和人生的洞察。王尔德广为流传的经典语录绝大部分都来自本书。 《道林·格雷的画像》于1891年出版后曾受到英国报界抨击:“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评论家们纷纷称道林·格雷为“恶魔”,但王尔德认为他是无罪的:如果不用为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我们每个人都会露出人性的恶。 当一场同性恋爱使王尔德官司缠身,《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罪证之一,最终他被判“严重猥亵罪”入狱两年。在一百年多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发现王尔德写在书中的一句话可谓该事件的最佳注解:“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
名人推荐:
在写作这个故事时我遇到的真正困难,是如何使极其明显的道德寓意服从于艺术和戏剧性的效果……使之处于合适的、次要的位置。——王尔德谈《道林·格雷的画像》创作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他是那么辉煌、壮观、摇摇欲坠。——《奥斯卡·王尔德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 当时的英国极拘泥于传统,人们一言一行都必须与严格的社会行为相符,稍微偏离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轨,连艺术与文学的原则都被弃之不顾,必须恪守社会规范。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王尔德决心以瓦解这种枷锁为毕生志向。——维维安·荷兰(王尔德之子) 上千年的文学产生了比王尔德更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没有一个比他更有魅力。王尔德唯一的问题是他的作品过于和谐,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博尔赫斯
作者简介: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王尔德一生创作颇丰,童话、戏剧、小说如今均已是文学经典。在他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世人将他的童话与安徒生相提并论,对他的剧作追捧至极,但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却因艺术观不被接受而备受争议。 当一场同性恋爱使王尔德官司缠身,这本小说竟成为罪证之一,最终他被判“严重猥亵罪”入狱两年。 出狱三年后,王尔德在巴黎一家小旅馆去世,年仅46岁。
译者简介:
孙宜学,博士,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海外汉学、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已出版学术专着10余部,编、译着30余部。 已出版作品: 翻译:王尔德《狱中记》 编译:《审判王尔德实录》《奥斯卡·王尔德自传》 着作:《凋谢的百合——王尔德画像》《眩晕与跌落:王尔德评传》 孙宜学教授将王尔德比喻成烈焰中炫羽的孔雀,华美、热烈而悲情。
试读:
第一章
浓郁的玫瑰香漫溢画室,夏日的微风轻拂花园里的树木,穿过敞开的门,传来阵阵紫丁香的馥郁,或是绽放着粉色花的荆棘的幽然清香。
亨利·沃顿勋爵侧卧在波斯毛布料长沙发的一角,像往常一样抽着烟,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根了。映入他眼帘的是蜜一样香甜、蜜一样色泽的金链花的微光,抖颤的枝条似乎难以承载它火焰般绚丽的花朵。飞鸟奇妙的剪影,时不时地掠过遮住大窗的柞蚕丝绸的窗帘,瞬间产生了日本画的效果。这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神情疲惫的画家,他们以必要的静态艺术手法想要表达迅捷和动感。蜜蜂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时而穿过没修剪的长草,时而不知疲倦地围着金色忍冬花打转儿,蔓生的忍冬花落满灰尘,静寂愈发压抑。从伦敦远远地传来模糊的喧嚣,像管风琴奏出的低音。
房间的中央支着笔直的画架,画架上夹着一幅全身画像,画像中的年轻人美貌惊人。画像前不远的地方正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华德。几年前,他的突然失踪曾在公众间引起极大兴趣,也招致了各色奇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着自己精心创作的清奇俊美的艺术形象,脸上浮起得意的微笑,似乎沉醉其中。但他突然受惊一般跳起,闭上眼睛,用手指捂住,仿佛要把某个奇特的梦锁在脑中,唯恐自己从中一下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幅,”亨利勋爵说,带着些许倦意,“明年你一定要把它送到格罗夫纳画廊去。皇家艺术学院太大,也太俗。每次我到那儿,要么人多得看不见画——那当然很糟糕,要么画多得看不见人——那更糟。格罗夫纳画廊的确是唯一值得送去的地方。”
“我可不想把画送去什么地方。”巴兹尔答道。他向后甩着头,奇怪的样子可是当年牛津朋友们的笑料。“不,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眉毛一挑,透过淡淡的蓝色烟圈,吃惊地看着巴兹尔。烟正从掺有大量鸦片的香烟中冒出来,升起奇异的螺旋形烟圈。“哪儿都不送?老兄,为什么?理由呢?你们画家真是古怪!不遗余力地去追逐名望,而一旦到手了,却好像要弃之不顾。你真是傻,因为世上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没人议论。这幅画像不仅能让你超越英国所有的年轻人,还会招致老年人的妒忌,如果他们还能动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嘲笑我的,”他回应道,“但我真不想将画送去公开展览,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
勋爵在长沙发里伸了一下懒腰,大笑。
“我知道你不会错过这个嘲笑我的机会,但尽管如此,我仍实话实说。”
“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在里面!我发誓:亲爱的巴兹尔,我不知道你还如此虚荣。我实在看不出你和画像之间有何相似之处。你面孔粗糙、僵硬,头发黑得像煤,而这个年轻的阿多尼斯,他看起来像用象牙和玫瑰叶制成的。啊,我亲爱的巴兹尔,他是那喀索斯,而你——好吧,当然,你有理智的神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美,真正的美恰恰终结于理智神情出现的那一刻。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夸张的形式,会破坏脸部的和谐。人一旦坐下来思考,就变得只有鼻子或只有额头,或者某种可怕的东西。看看那些需要高深学识的行业中的成功人士吧,他们真是让人极其厌恶!不过在教堂里的神职人员例外,因为他们不用动脑筋,一位八十岁的主教,一直说着他十八岁时人们教他说的话,结果,他自然而然总是令人极其愉悦。你那神秘的年轻友人,你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名字,但他的画像可真令我神魂颠倒,他从不思考,对此我深信不疑。他就是那种相貌迷人头脑空白的一类。冬天我们无花可看,他就该一直待在这儿;夏天也一样,夏天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来清醒我们的理智。别太自鸣得意了,巴兹尔,你跟他可是一点儿都不像。”
“你并不了解我,哈利,”艺术家回答说,“当然,我并不像他,这点我非常明白。说实话,若我像他,反而让我遗憾了。你为何耸肩?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才貌超群者往往背负宿命的悲哀,纵观历史,这种宿命总是紧随帝王蹒跚的步伐。我们最好不要与自己的同类有别。丑陋的和愚笨的人在世间往往占得先机,他们可随性而坐,看戏时大张着嘴。如果他们对成功一无所知,那他们也就不知失败的痛苦。他们过着我们所有人都应过的那种生活——没有烦扰、平庸无奇、心平气和。他们既不会毁灭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毁灭。哈利,你的地位和财富;我的才智,虽然价值不大;我的艺术,不论它们价值几何;道林·格雷好看的容貌——这些皆为老天所赐,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
“道林·格雷?这就是他的名字?”亨利问道。他穿过画室走到巴兹尔·霍华德面前。
“对,是他的名字,我并没打算告诉你的。”
“为什么不?”
“哦,我也说不清楚。当我心有挚爱时,我绝不向任何人说出他们是谁,说出来就好比一点点出卖他们。我愈来愈喜爱隐秘了,这样似乎能使我们体会到现代生活的秘密和美妙。最最普通的事,只要掩盖起来,就变得妙不可言。如今,我外出从来不告诉身边的人,如果说出来了,我就兴致全无。我敢说,这是一种愚蠢的习惯,但这样好像给生活增添了很多浪漫色彩。我想你一定认为我蠢透了,不是吗?”
“一点也不。”亨利勋爵说,“一点也不,我亲爱的巴兹尔。你似乎忘了,我可是已婚男人,而婚姻的魅力之一就是:它把生活中的欺骗变成了夫妻双方所必需的。我从不知道我太太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当我们见面时——我们偶尔会见面,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去公爵大人那儿——我们都会一本正经地讲些最荒唐的故事。我太太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事实上,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会搞混约会时间,而我却总弄错。但她发现我出去厮混也从不吵闹。有时我倒希望她闹一闹,但她呢,只是嘲讽我一番。”
“哈利,我不喜欢你这样谈论自己的婚姻,”巴兹尔·霍华德边说边慢慢地走向通往花园的门,“我相信你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丈夫,但你却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德行。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从不假道学,也从不做什么坏事。你只是摆出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罢了。”
“顺其自然才是一种姿态,而且是据我所知最令人恼火的姿态。”亨利勋爵笑着嚷道。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到花园里,坐在月桂树荫下的长竹椅上。阳光顺着光亮的树叶洒下,草丛里,白色的雏菊在风中微微抖动。
过了片刻,亨利掏出表,轻声说:“巴兹尔,我要走了。走之前,我还是要你回答一下我前面问过的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问,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你心里很清楚。”
“我不清楚,哈利。”
“好吧,那我来告诉你。我要你解释为何不展出道林·格雷的肖像。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已经把真实的原因告诉你了。”
“不,你没有。你说是因为在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啊呀,这种解释太幼稚了。”
“哈利,”巴兹尔·霍华德直视着他说,“每一幅画家用感情所作的肖像都是艺术家本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的模特。模特只是提供了一种偶然或者诱因。画家在彩色画布上所表现的是画家本人,而不是模特。我不想展出这幅画的原因在于:我恐怕在画中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勋爵朗声大笑。“什么秘密?”他问。
“我会告诉你的。”画家说,但他脸上流露出困惑不解的表情。
“巴兹尔,我可是满心期待啊。”他的朋友接过话,扫了他一眼。
“唉,实际上真没什么好说的,哈利,”画家说,“我恐怕你理解不了,也可能觉得难以置信。”
亨利微笑着俯身从草地上摘了一朵粉色花瓣的雏菊,一边端详一边答道:“我确信我会理解的。”他凝视着这个小小的、金色带白毛的花蕊儿,“至于信不信的问题,只要不可信的,我都相信。”
风吹落了树上的一些花朵,一簇一簇星状的沉甸甸的紫丁香在慵懒的空气中来回摆动。一只蚱蜢在墙上聒噪,纤细的蜻蜓扇动着棕色的薄翼,如同一条蓝线飞过。亨利觉得似乎都能听到巴兹尔·霍华德的心跳声,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事情很简单,”画家过了一会儿说,“两个月前,我去布兰登夫人家聚会。你是知道的,我们穷画家总要时不时地在社交界露一下脸,无非想提醒大家我们可不是什么野蛮人。正如你曾对我说过的那样,任何人,哪怕是股票经纪人,只要晚礼服配上白领结,都会博得彬彬有礼之名。好吧,我在房间里待了大约有十分钟,正敷衍那些体态臃肿、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和乏味的学究时,猛然发现有人正看着我。我侧过身,第一次看到了道林·格雷。当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自己顿然苍白失色。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感攫住了我。我意识到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纯粹的人格魅力如此令人迷醉的人,如果我纵容自己沉溺其中,那么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整个灵魂,甚至我的艺术本身,都会被它吞没。我可不想自己的生活受到任何外部影响。哈利,你是知道的,我天性独立,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一向如此,直到我遇到了道林·格雷。随后——但我真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释——有某种迹象似乎向我表明,我的生活已处在可怕的危机边缘。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命运为我储备了极度的欢愉和极度的悲伤。我越来越怕,转身离开了房间。我这样做与良知无关:这是因为我的怯懦。一心想着逃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巴兹尔,良知和怯懦原本就是一回事。良知只是公司的商号,仅仅如此。”
“我不相信,哈利,我也不相信你相信。然而,不管我的动机如何——也许是出于骄傲,我向来如此——我挣扎着走向门口,不用说在门口撞到了布兰登夫人。‘霍华德先生?你不会这么快就开溜了吧?’她尖声说。你知道她那奇特的刺耳嗓音吗?”
“是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只孔雀,除了美貌。”亨利勋爵边说边用他纤长不安的手指扯碎一朵雏菊。
“我不能摆脱她,是她提携我接近王族和拥有各种勋章的人,还有那些佩戴着夸张头饰、长着鹦鹉鼻子的年老名媛。她把我说成她最亲密的朋友。我之前只见过她一面,但她一门心思吹捧我。我相信,我的一些画在那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小报上已有如此评论,而这些评论则是十九世纪画作不朽的标准。我突然发现自己与那个年轻人四目相对,他的人格魅力如此奇怪地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我们离得很近,几乎能触碰彼此。当我们再次四目相对,我竟不顾一切地请布兰登夫人介绍我认识他。或许这称不上轻率,毕竟我们的相识原本就不可避免。即便没有人介绍,我们也会彼此交谈,我对此确信不疑。后来道林也这么说——他也觉得我们命中注定会相识。”
“布兰登夫人是怎么形容这个奇妙的年轻人的?”同伴问道,“我知道她善于几句话就把所有的宾客介绍一遍。我记得她把我带到一个一脸凶相、红脸膛、浑身挂满勋章和绶带的老绅士面前,就对我耳语起来。不幸的是,透过她那嘶嘶的嗓音,那位老绅士最耸人听闻的细节让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我只得落荒而逃。我喜欢自己去了解一个人。布兰登夫人待她的客人,完全就像拍卖师对待拍卖品一样。她要么什么都说,要么讲得事无巨细但就是不说你想知道的。”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