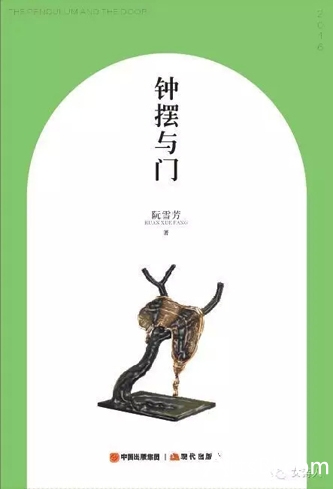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出版
近日,潮州女诗人阮雪芳的第二部诗集《钟摆与门》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徐肖楠称赞说,阮雪芳作为一个语言和审美能力日趋与时代同行的诗人,阮雪芳用她安静的激情、忧伤和心灵独树一帜,将诗歌风花雪月的纤柔不断与铁马金戈的大气交错,美学和诗学上的成熟化为了具体的诗意,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庄重的生活观念结为一体,人类生存在时尚中国的急迫感逶迤穿越她的诗中,形成了明确的风格方向。
《钟摆与门》有着非常独特的个人风格,收入这部诗集的诗,是阮雪芳的近年的诗作。这部诗集的出版,必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阮雪芳,生于潮州,现居广州。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潮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湘桥文学协会副主席,韩山是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理事,韩山诗群最具影响力的诗人。阮雪芳的诗歌作品有部分在国内、省内一线刊物或报纸上表,作品凝练、透彻、沉稳,深邃,同时体现诗的美学,赢得许多著名诗评家的关注和评论。
在诗歌中向着太阳飞翔的天堂鸟——阮雪芳的诗带给我们什么
徐肖楠
让生命和时代留在诗意生存中
一个诗人应该不仅能带给我们诗意感受,而且能带给我们对时代和生命的深入。作为一个语言感觉和审美能力与时代同行的诗人,阮雪芳诗中有执着的时代生命感,她用安静的激情、忧伤的心灵独树一帜,将诗歌风花雪月的纤柔不断与铁马金戈的大气交错,让人类生存在时尚中国的急迫感逶迤穿越她的诗中,美学和诗学上的成熟化为了具体的诗意,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庄重的生活观念结为一体,形成了明确的风格方向。
她的诗简洁、凝缩、精致,含蓄不露,不事张扬,却有关注现实的宽阔情怀,散发着柔韧内秀的激情气息,因不拘泥于狭小自我,能产生对单一事物的开阔浪漫想象,以此寻找和发现诗歌情趣与生活意义:“进入雪地旷野/一只手在梅花的窗前移动/仿佛发生了什么/光从另一个地方返回/灯下读着别人的故事/书页翻动/出生,相爱/死亡充满了无色的智慧/神在何处/事物敲击大海之门/灰手套漂浮在水面,别人/用上了你的名字,你教她相爱/并将最初的梅花变成虚无/时间永在”。(《另一种声音》)这些诗无论气味、视觉还是声音都感觉独特,在生活现场中弥漫象征性想象和梦幻,却又流溢一种生命自由感,既有叙事化的整体抒情感,又有浓烈溢散的具体生活感觉。
她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性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诗歌,她的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诗歌观念与生存观念融合一体,用诗歌去实现以至开辟尚未实现的想象可能和美学可能:“头顶小径交叉的命运/延伸没有形象的城市/你不能说出全部/生活,多么糟糕”。(《麋鹿说》)这种美学性情的重要之处,是让诗歌进入具体生活,又在诗歌和现实中找到另一种生活,由此改变庸常的状态:“只因生活那一股毁灭的力量/才使我们痛切又如此执于存在”。(《生活》)于是两个重要的主题贯穿她的诗,一是在时尚中国的生存信仰,二是对生活表象与本质的认识:“溃败的春天从一到无/在伟大事物到来之前”(《弗里达》)。
一个没有时代的诗人,诗歌中也不会有他,他所生活其中的时代也不会有他。阮雪芳摆脱了一些诗人不屑直接进入现实的偏执观念,从不同方向以诗歌进入现实,也从生命进入诗歌,这些诗歌体现了她对生活贴近而热切的关注:从地铁站到公祭日,从故乡依恋到都市情爱,从潮州外婆到广州女市长:“她合上眼/让那个六岁的小女孩/留在身体的黑刺丛中哭泣/仅仅停了/1.1秒/她又像老司机一样/加快油门”。(《女市长》)这样的诗歌是对她的情怀、真诚和自我的考验,让她不断尝试进入这种有考验的生活,不断进入现实又完成另一种更高的生活。
在当代中国诗歌不断分化和弥散的倾向中,尽管她的诗中包含各种个人和时代的疑惑与悖论,却逐渐走向一种更庄重宽阔的诗意生活,激发她诗歌的,恰好是各种相互不一的生活情景和生存态度。她拒绝诗歌传统的中断,也拒绝诗人矫情的敏感,是对反浪漫主义、反理想主义、反精致庄重的认真反拨,也是对诗歌的自我迷恋和自得其乐的反拨:“藏身其中的这个执念是什么/一种勃然闪光的东西”。《(证词)》她追求诗歌的现代性,但从不刻意分裂诗歌的传统性。现代诗歌虽然与古典诗歌似乎截然不同,却充满同一性内涵,因为诗歌包含一种能拯救人们摆脱当代困境的精神传统,或者说包含一种美学化的生活传统,因而她的这些诗也在帮助人们摆脱当代困境:“不要挖他人灵魂的沙/不要在蝴蝶停落的地方起舞”。《(证词)》
从诉说日常生活的美学形式这一立场,她返回诗歌精神的核心传统,从而进入时代现实,诉说和验证这个时代的生活形式与诗歌精神。“大树已经拔走/只剩下一个土坑/一撮鸟毛和树叶/下一个坚硬的洞/只剩下你/和风/不胜其烦地/探讨着它剩下的内容”。(《大树》)与日常生活中对身边事物的诗意敏感有关,她用美学形式加以描述,以此达到宁静自在的诗意境界:“我想起深冬的傍晚/雪花白蝶似的在后院里飞降”。(《时间》)。
在她诗的晓畅清晰中,包含着非同寻常却又受人欢迎的生命、生活和诗歌味道,三者一体是她诗歌的美的特殊形成点。有了生命和生活的真实体验,就不会矫情、不会虚假,有了真切的意象和体验,才会去寻找诗歌的语言,她想要做的,是怎么以最得体的想象与虚构去完成这种真实。为此,她的诗正在破坏她以前所接受的一些诗歌成规,对于她,诗并不一定要批判、要痛苦,虽然时尚中国普遍的诗歌情调在训练她寻找一些所谓深刻的痛苦,但她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却是根本的爱:“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现在,你坐在客厅/透过镜子的影像,儿子/那个年轻人正第一次使用/你微笑,看着”。(《一把剃须刀》)
从诗歌延伸向生活的整体诗意
这个时代的很多诗歌都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个人仪式化生活,写诗和读诗不一定是诗意生活,却成为一种自我标志,这样的诗和生活是碎片化的。但在阮雪芳的诗中,呈现一种有难度的诗歌意愿与行为,她不是将现实事物肢解分离,而是把生活碎片在诗歌中镶嵌为一个整体,把身边一切变为人们容易读懂的诗意形式和生活形式,这种整体性意识与人类性开阔的诗意生活相连。
文学中的整体性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学意识传统,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延伸至现代文学。在激变而不可捉摸的时尚中国,阮雪芳似乎在倾听一个神一样的整体性诗歌声音,在这个声音的教导下,逐渐改变单纯叛逆的思维,稳重安静地回归核心性传统,正是她的整体性思考与表达诗歌方式,让她更为轻盈灵巧地穿过了似乎密不透风的现实之墙。她对各种事物的诗性呈现,都有一个明确的美学性情和立场,把各种思想和生活片段编织为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直接影响她的诗思形式,这既包含一首诗的构成,也包括各个诗篇的完成。
她延伸向生活的整体性诗意,以鲜明突出的个别意象,构筑整体性诗歌世界,让诗歌与周围的现实建立起持久的联系,也为她的艺术信念和想象能力构造了一个整体性现实世界,在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时代里,寻找到内心信仰的源泉和安慰:“月光披在你的双肩/你听到水/触动了,云或树/鸟被四合的叶片簇拥/像一只只睡去的琴键/林子寂静/更大的寂寥/围拢村庄,橄榄树/和你曾经焦虑的生命”。(《夜宿农庄》)
她诗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汇集成不同诗篇和同一风格的整体性主题,用来顽强介入因习性生活和心灵衰退而造成的生活荒芜。实际上,她在诗中收集生活的碎片,并试图给予其秩序性,带着灵活的、清新的、转变的活力,以感受这个世界。并以诗歌想象的短暂时刻,变成了生命的长久安慰,当她承认黑暗、混乱、碎片、毁灭的同时,也来到了用诗歌挽救和创造那些被毁灭情感的时刻:“而你看见死亡沉睡在我的蹄下/驯服、克制/隐忍的美德/自由的雪花/从同一条河流上啜饮/狂野的春天”。(《麋鹿说》)
写出和世界连在一起的人类性体验是她的特点之一,从身边生活相关的事物或事件出发,时刻关注此刻到永恒的诗思,像《时间》那样展开:“而在一个清凉的胴体下/看到万物突然惊醒的春色/一场无人享用的盛宴”。她的诗歌意境、情趣、思绪完全超越了狭小的自我关心和性别关注,在安静大气中进入诗歌的宽阔,“那么多的夏夜只记得/你清凉的胴体/像荒野结满霜花/像湖面站立天鹅”。(《像荒野结满霜花》)在诗中她能时而壮怀激情,时而伤怀迷离,却不随意写作,即使在现实中一碰一触,也依托于内在的精神情境和生命主题,像《皈依》那样触发远离尘世的美对生命的净化:“庙里有一个和尚/长得俊极了/看见他/我就感觉自己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受过伤害/从未历经生离死别”。
她以灵动语词、鲜明比喻和突出感觉传递了一种人类性感觉效果,这些语词、意象、主题、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诗歌思维方式,并不是某种刻板思想的传达。她的诗轻盈灵动,严整有韵律感,修辞上的含蓄蕴藉与形式上的明快多姿,化简了技巧上的复杂和繁冗,这既包含了灵动的诗歌语言和飘逸的诗歌智慧,也流荡出变化的韵律和朦胧的意象,却不时闪现与人性无法分离的意味。《分居期的女人》中那种表面与内心、美与日常生活相联而形成的情境让人震颤:身体是孤独的,却是神圣的,它与灵魂一体,像教堂一样神圣,所以这种身体与灵魂的美可以忽视肮脏的街道,纯洁和孤独在美的裸露中同时迸发出来。
人类性整体感觉需要深入体会诗歌本来的精神和意愿,而不是刻意地按照某些概念去寻求,概念的寻求会将生活与诗歌分裂。她的诗中,概念的痕迹日渐消失,灵动的想象日渐生发,就像清晨小树林中的露水片片闪光,却有同一个太阳照耀。
忧伤的理想主义者之歌
阮雪芳的诗为当下的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清亮的色彩、优雅的形式、简洁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事件,也为人们提供了诸多从传统生活中走来的现代生活价值,在诸多对于生活变化的预感中,她对于个人生活忧伤动人的抒情与理想主义交替穿插其间,形成了她特有的忧伤的理想主义风格。
她怀有浪漫的激情和悠远的想象,写的却大多是一些平凡而高贵、沉静而尊严、无言而庄重的事物和人物,悄然蕴含着一种遥远的理想主义气质。她不停地用诗歌把生活感觉变得更雅致,因此,她用诗的语言和想象组成了一个精美的世界,那些瞬息即逝的、令人沮丧的事物都被她赋予了另一种意味,风、海、山、水珠、城市都参与了她诗中的精美建筑,它们时而像音乐一样流荡,时而像精灵一样飞翔。
也许成为今天现实中一个浪漫主义者标志,在她的诗中,多少可以看出一种以美人香草指代理想的痕迹。这有时是极端的幻象,而这个幻象作为虚构的极端却对现实有意义,只要幻象不消失,一个理想的生活对于她而言就是存在的。在诗歌容易成为标志而不容易成为真实生活的时代,她靠写诗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带着敏锐和感性的整体性意识,去思考并完成诗歌。
在日常生活信仰的普遍衰落中,信仰的必要性却在她的诗歌中与日俱增,并成为一种永恒的最高虚构。找到了这种虚构,诗的主要观念便是一种心灵想象,并在诗中发挥作用,这种最高虚构的想象方向之一,便是疏离现实的限制。这些诗中的世界与神话不同,也与她所知道的现实不同。对于她,信仰就是能否接受和怎么接受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在她的诗中,会有诸多提问,出现心灵挽救和精神恢复的努力:《午后》表达出一种理想和灵魂的向往,有梦幻一样的奇思妙想,又有背后的隐喻空间,鸟是生命,水是现实,太阳是理想,三者混融而成生活。信仰是美的生活的母亲,但信仰必须存活在身体里,所以她有身体与灵魂的共同生活,以感受那种永不消失的信仰。《广州街头》中,当轻微的忧伤划过生命时,就像飞机划过一种优雅时尚、舒适惬意的生活上空,带来隐隐的忧伤。这个生活划痕意味深藏在她的生活和诗歌中,不看她的诗便看不出来这种生活的划痕,一些敏感的和沉默的意味在诗中飘溢出来。
《黑暗之歌》借黑暗的沉重压抑来突出忧伤中的生命之光,自己的身体成为这个生命之光具体而含蓄的象征,这是一个在喧嚣生活中的宁静身体,即使处于一切的黑暗沉沦中,也在安静地对抗,所有沉重和黑暗都无法消灭这样的身体,这一切都呈现一个生命之魂的光芒,不再需要虚假的灵魂对抗,只要有实在感受的身体和生活。《茨维塔耶娃,或向日葵》表达与每个人命运相关的人类性,将所有的生存感觉都表达为一种悲怆的坚韧、压抑的激情和抗击的温柔。《桃花辽阔》中桃花安静而透明地激情燃烧,却总要与忧伤和悲悯相伴,所以桃花欢悦中含有一丝忧伤。
“黑暗怀着悲悯/光线摇着喜悦”这样总是相拧结的生命力量是她诗歌的艺术动力和主题成份,相互包含又背离的力量含蓄有张力,无尽延伸了想象,这使诗歌不会单一浅薄而羽翼丰满。一个意象,两个翅膀,同时飞动,就像一只向太阳飞去的天堂鸟。忧伤的理想主义始终是她的诗歌的方向,总有一种相反的暗喻为诗歌增加了张力,内心生活的丰富柔软与美学性情的安静平常,让她从不喧嚣混乱,一切都美丽有序地在她的世界中结为生命的年华。所以,她能在忧伤中产生一种生命的勇气,把冬天的冷雨变为令人昂扬振奋的《奔跑的水晶》:“冬天第一场雨/奔跑的水晶,在都市/造出旷野/接近美好总令人心跳/白昼永远是盲者的深渊/而生活自有明亮的部分”。
尽管含着忧伤,在一个不纯真的年代,阮雪芳的诗抒写着纯真;在一个缺乏爱与美、浪漫与理想主义的年代,她执着追求爱与美。她的诗像天堂鸟般地在广州这座大都市中飞向另一种生活,她的诗是她的理想主义翅膀,她的翅膀追随着时代的风。时代的风从来不会停,就像她的《追火车》那样,从来也没有追上火车,但追火车的那颗心灵却永远留在生活里,刻在记忆中,那种纯真和追恋正是她的诗所发现的生活迷人之处。
所以,她描写的爱与生命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感伤主义的。她的诗清新自然,优雅纯净,会时而泛起一种纯真的牧歌情调:外婆的纯真、孩子的纯真、母亲的纯真、烈士的纯真、女市长的纯真、地铁男孩的纯真。让我们感动的,是这种深藏的、坚韧的、悠远的纯真,这样的纯真受到现实的伤害,却又真切地挺立于现实之中。在爱的纯真后面,她收敛起不安的锋芒,但无法把握的命运感又形成了她欢欣与压抑并存的想象方向,也形成了她诗中相关悖反事物间的美学张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坚韧的纯真方向,就不会有她的诗的更多设想、情趣和意味。
抒写漂泊者的纯真是她的一个独特主题,爱与故乡都变成了生命纯真之根,爱就是漂泊者寻找的精神故乡。她的诗中贯穿着几个相关联的主题,表达生命关系和人类共同的关怀,漂泊者便是这样一个具有主题性的反复出现的形象,这个形象会不时变化,穿越一个个生命苦恼和自己的梦,保持穿越的勇气,设法获得生活信念的飞跃。她的漂泊感中令人惊异地保留着依恋和怀想,虽然从相对保守质朴的地方逃向个人主义集中和投机冒险的城市,却透出深深的纯真。想逃离地方生活的单一、偏执和狭小,不愿停留在一种固定的生活形象和文化思想中,让中国的大城市有了很多漂泊者,而真正的诗意上的漂泊者,是在她的诗中出现的那样的漂泊者。
《地铁里》是一个集中的漂泊生存意象,将城市感觉、地铁情景替换成精神漂泊的自我感觉,让人感觉到每个人的漂泊都是心灵漫游和生命历程。每个漂泊的人都会像地铁里的男孩和女孩那样,找到了或者正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漂泊就是自在或者自由,正是在漂泊中才有一种生命感觉。漂泊不是悲哀而是一种生存,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漂泊,漂泊的生存感觉是挺立在漂泊的生活后面的另一种生活的感觉,自由的生命和灵魂都在漂泊中部分实现,否则就只能陷入某种局促之中。
要有生活中的纯真和单纯,那是诗性惊异的基础,生活逻辑是诗歌逻辑,如果诗人平常没有诗歌表达的逻辑秩序感,没有对生活的诗性惊异感,便无法观察生活,也无法写出有艺术逻辑的作品,不会有这样的诗性意味的组合和流畅连贯的语言。生活变动和城市压力既形成了她的精神漂泊感,也形成了她独特的纯真衷情,在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漂泊中,她却像个圣徒一样跋涉,去追寻生命纯真和神性之光。
双重感受交错中的美学性情
在资本化和时尚化所推动的中国生活中,在历史、社会、个人、自我的诸多脱节中,阮雪芳的诗显出柔韧执着的意义方向和清新温雅的风格情味,显出不高高在上而与现实紧密贴合的诗学趣味,独特地向人们呈示了生命的特殊性和美的诗性惊异。
她的诗含有两种生活力量并行的美学性情,她的诗歌观念隐约穿行于诗中却并不模糊,这让她的诗思清晰可见,而激发这些的,恰好是相互纠结的矛盾情景,就像《理想》:“你眼中的灯/摁灭四周的光/你体内的黑/却一点点加深/谁饲养了理想这头雄狮/谁就得交出整个山头和月光。”她坚持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角度探寻现实的秘密,总可以看到幽昧与光明、理想与现实同在,总有个忧伤而欢欣、坚韧而灵动的身影在闪动,也许,这和忧伤美学本来就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相连有关。
诗歌想象的种种特点,在她诗中的时尚中国生活场景中表现出来,以澄清她自己的迷惑,不再为生活表象所陶醉。诗成为一种确定的诗意生活,也成为并不确定的实际生活,成为她的以至读她诗的人的生命事实,成为打开生命存在的钥匙。诗中的强大城市压力、惋惜的乡村情景、生存的梦想和古老的神性都发出了声音,不论抒情还是理性,不论牧歌还是沉思,所有她所关注的重要主题都在其中出现。
她通过诗歌将对事物的疑惑不解清理出来,这些诗力图成为理解生命和世界的支点与小径,虽然不完全清晰,却让你可以去相信,因为那里面有种理解生命和世界的象征和隐喻。一种诗意感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然而,这样的感觉之中还有更真实的生活,这真实的生活却需要在生活现场中得到提升和超越,她的诗中所有身体和街头的情景都得到了超越。《分居期的女人》中,突出的是一个抱紧自己灵魂奔跑的女人形象,精神恍惚和心不在焉是这个形象的表面征象,而深处却充满象征意味,她深藏了自己的内心伤害以及生活中的威胁和疼痛,在一边聊天一边想象中完成自己的心灵安慰。
她的诗虚构一种能容纳她生存情结的想象生活,总是在对两种不同质的东西中做出一种倾向性的选择和反映,在双重生活和诗歌倾向的并行甚至扭结中,她的诗总是有一个身心和诗性的方向,这个写作方向有种对生活的忧思,而忧伤与欢乐并行的双重性,恰恰是她的诗的一种内在张力。忧伤总是与理想交错,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隐喻和象征的意象,抓住了她的诗中的基本意象,就容易抓住她的诗中的其他意象,就容易读懂她的诗。《火的酒中》以火酒相撞的激情表达爱,也表达爱的欢悦之中隐藏的忧伤和怅惘,而在生命的哀伤中,挺立起一种生命的尊严,《情人节》隐含的,也有这样的主题意味。
真实的双重生活和双重自我的交错产生了诗意生活形式,但必须在其中找到引导自己生活的方向。她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静、轻、光与某种暗藏的力量结合,见出她的诗歌的美学性情,成为生命和诗歌纷繁形式的渊源。《亲爱的速度》用生命速度表达生命轻微与力量之间的奇妙,《当我离开》写生命轻微中唯有心灵的光让身体与众不同,《野马》中野马的生存情境隐伏着毁灭它的美的威胁。
同时,一个诗人还必须担负用美学意味启示他人生活的责任,现实与自我的诗歌分享感,常常变成了一种心灵探索方式,让她自己和读者同时变成了秘密分享者,因此,诗中常有叙事者或抒情者与诗人自我之间的双重关系,这也形成了她的诗歌在双重关系中的诗性张力,忧伤之美的情味感觉常常与理想力量的想象同时生发,既怀恋了生命和情爱的时光,又表达了美的柔和与力的刚烈双重交织的生命感受。《驯虎师》在孤独麻木的动物园看守年轻时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一个月光似的女人,表达了一种温柔力量让野性力量感动的意味,《在爱开始的地方》中开始爱的地方是结束爱的荒原,却因曾经丰饶而令人怀恋,并由爱会再次繁华而获得生命信念和生活信仰。
于是,悠远呼唤和微妙转变常常构成了她的诗思,这些诗思并非无知茫然,而是走向一种浪漫式激情,这种火一样浪漫激情支持的深处,却是深泉一样水的安静。这些诗歌是时代的安慰、生活的安慰,也是诗歌的安慰,这种安慰来源于她的诗总是超越出狭隘自我,找到了自己藏在那些诗歌根枝间的露水。当她找到这些如圣水般的露水,它们就成为对抗生活混乱的精神滋养,所以,她的诗中总是同时出现激情与安静的双重性,这常常体现为她的诗中不断出现的火与水。
虽然她的诗中时常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向和思绪,能听到她内心两个声音在争吵,两种相互抵抗的力紧紧拧在一起,但她的诗中总有一个方向拉动两种不同的力向前推进,再加上形式上的委婉表达和内容上的明晰逻辑,整个诗会变得非常精致干净。《生命》只有两行,却在两行诗句中推开一扇门,看到一个生命空间;《时间》将时间与空间组合交错而产生一种独思时间的情味,这样的独思时间的意味也轻轻地嵌入了温馨的双重情感,这具体地化为一个在独思时间找到的想象身影,时间可能隐喻另一个人的存在、离开和等待。
结语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诗歌与生命结合的形式与意义,阮雪芳的诗歌能带给我们什么,既与她所生存的时代相关,又与诗歌恒久的人类性相关,诗歌的诗性表现和诗意感受都不可能离开时代和人类性。阮雪芳特有的诗歌风格为我们带来了诗歌在这个时代进入生活的可能,也带来了在这个时代写出诗歌的可能,她诗歌中的具体情景不是抽象的诗歌精神、诗歌思想以至诗歌概念,这让我们反思太多的浮于生命之上而傲视生活的诗歌情景。
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效果,这在于不同的诗歌要突出什么,她突出了她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生命感受,突出了她的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她以具体的作品进入优雅的诗意时间和生命时间中,在她眼中,所有个人的诗性气质和精神品位都在具体的诗歌情景中才能实现,生活以及日常表达只是生活的不完整实现,而诗歌才是生活的完整性实现,从而,不论她诗歌的沉思还是激情、浪漫还是坚实、温婉还是坚毅,都是对生活和生命的另一种实现。她的诗歌是创造和表达自己生命感觉和生命思考的形式,这些形式因素有助于呈现她诗歌中的和谐与清晰,这些诗歌的语言、技巧和表现力与时代紧紧结合,无法分离出她的诗歌而存在,也无法分离出她对这个时代生命的关注而存在。
对她来说,诗歌的时间与门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生命的又是艺术的,所有的语言和节奏都处于这样的诗歌精神情境中,才是最恰当的。她的诗歌为生活进入诗歌,也为诗歌进入生活,为此而寻求自己独特的想象、意象和隐喻,将生活不断地转换为诗的形式和主题。她似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审美呼应的关系中,于是,她的作品并不能由这些作品之外的其他作品来替代,这些诗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逻辑的一环,从而,她的个体写作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歌作品的时间跨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在艺术中的时间跨度,同时,也是对她自己作品和写作行为的有效解读。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触摸钟摆
阮雪芳
一
小时候,我家有一台老式摆钟,挂在临窗的墙壁上,我和姐姐的床靠放在窗子对面。八十年代的乡村,夜是凉的,蛙鸣透亮,窗外就是大路,然后是池塘,延伸过去一片浩大宽阔的田野。窗口流转过不同风景,几颗星辰、雨珠敲落,或月色弥散,淡而白,有时什么也没有,寂静,漆黑一团。我从小怕黑,总觉得黑暗中存在某种未知之物,或者会有什么突然出现,尖锐、强悍、神秘。不可抗力的疑惧,像一根长长的细线,抛向黑暗之海,我就是系在细线上的小块鱼饵,似乎随时游来庞然物一口吞噬。深不见底的夜晚,我贴紧着姐姐,沉入睡梦中的她,却如柳枝似的,一次次被海水冲荡开去,此时,无声息的恐惧达到了极点,我蜷缩着小小身子,低声啜泣。
咚——咚——咚——
带韵律的金属与木质融合一体,划破空气的声响,一下,又一下,是谁藏匿在黑暗底部?敲击虚无之门,坚定、明亮、有力,我侧耳细听。
那是我第一次聆听时间的声音。
好像胎儿听见羊水的脉动,我停止了啜泣,掀开被子,久久地注视壁上的挂钟,黑暗中,它模糊的轮廓,渐渐地变得清晰。此后,只要钟摆停下来,我就催促大人们去上发条,再大一点,我自己搬来凳子,干那活儿。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打开摆钟的门时,两颊潮红,双手颤抖,触摸着钟摆,触摸它冰凉的圆周,浑圆、粗糙、坚硬,在钟摆与周边空气之间,流动着一些模糊而孤独的东西。钟摆声伴随我度过此后的无数个夜晚,即使窗口没有风景,内心依然丰盈而隐秘。
二
我的堂叔是个船长,他在大海上度过了大半生,从英俊小伙子变成了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指挥着那艘装载货物的巨轮,驶向世界各地。我不知道他如何消磨漫长航程的时光,一个在大海上耗掉大半生的人,也许是最懂得大海的,他问我,你来过大海吗?那真是大,真是孤独。那时,他正横穿大西洋。
一个深夜,我被手机声吵醒,电话那边传来他急促、灼热的声音。
“我知道我讲得不好,但太神奇了!”他告诉我,几天前,他的船经过百幕大三角,突然遭遇风暴,闪电飞光,雷声轰鸣,巨浪如猛兽,船和人似乎被一股无形旋力吸纳入巨大的漩涡之中,传说中神秘而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的心头,他紧张地指挥船员,大家手忙脚乱,深感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力,即使巨轮也会如积木随时覆没。但不久之后,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虽然逃过了一劫,人和船却惊魂未定,堂叔累得趴在甲板上,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了太阳。“我一抬头就看见它,强烈,红的,散发让人舒适的光,它不是平时见到的,那快速又幽慢移动的样子——大自然的钟锤!我说不出感悟到了什么,但真的神奇!海天一色,澄明无比。”
打电话时,他已平安到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我能感到他的喜悦。
我想起,第一次打开摆钟的门,伸手去拿钥匙的感觉,好像发现人所不知的一个秘密,上紧发条,钟内部产生了一股较量的暗力,我的手沿着钟摆轻轻地触摸,我想,他的喜悦和我一样,而钟摆周围模糊又孤独的东西,都在这里显现。两个时空的重叠过程,宇宙、自然、万物、生命、时间、空间。我明白了从小为何那么怕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怀抱不安的萌动,那企图摆脱生活中心的萌动;那有着强烈诉求、解脱固有习俗的制约;那从一开始谋划逃离的念头;那感知到黑暗混沌中有某种力量,催促我奔逐光的召唤。
三
小时候,我所听到的钟摆是不可琢磨的时间,它对我而言,是神秘、巨大的,但是钟摆敲击声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后来,我长大了,可是,比我年纪更大的叔叔遭遇的时间似乎跟我遭遇的时间不一样,它是暴风雨、太阳和大海共同形成的,是更壮阔、更遥远的时间。然而,它们都是一种别致的生命感受,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时间,时间的不可琢磨在与生命的汇合中变成了无限,它们在诗中、在生活中变成了诗意的时间,这时候,由于生命,时间变成了永恒的无限。
置身于时间之中,生命因追求有了意义,思想也为爱而存在。因此,无论生活多么糟糕,人们仍然可以在沉默言辞与自由意志中,获得生之爱,以及内心完满,更好地活着,体验,激发和引领,即使独自度过每一个夜晚,仍是生命夏天里凝望的星辰和花朵。
触摸钟摆,穿越时空的韵律,轻美的,饱满的,跃动的,旋转的,唤醒内在经验。在这里,我看见另一个打开的空间,不同生命的渴求、自我完成的精神、未抵达的彼途,以及人类共同对美和爱永远的追寻。我们从母马丰满的线条看到野性和美,从点燃的火柴瞥见妖娆的舞蹈,从月光里闻见流淌的洁白晶粒,从海中遨游的鳐鱼,听到了飞翔的声音,而在疾速的列车中,我们擦过梦的边界……这些,经由敏感的心灵捕捉、唤起,无论是恬美的轻音,还是激荡的声韵,当我们说出,或者写下,诗就成生。
布罗茨基说,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我曾经希望有所发现,拒绝昏迷,清醒注视,看见时间内部是火,是水,是色彩,是无尽的黑暗,是丰沛的光,寂静而澎湃。
时间从它内部迸发出来的,不是烟尘,而是心穿越时空碰撞了另一颗心。此时,诗人有如握住摆钟的钥匙,一条通向秘密花园的途径,以天真、热情,打开生命经验与心灵想象,重获一个无边而多元的时空。诗人置身其中,离天地万物最近,也是心灵忠诚的倾听者,自然赋予了时序、力道、能量和永恒的召唤,生命携带本真的元素,对生活细致观察,持以深入,更幽微、更优雅、更细腻地显示世界原貌,爱、美、真相,三者浑然一体,澄明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事物。
诗又是一种剥离时光的历程,不在预演中到来,而是渴望、思考、体察,就像交响曲般,从发梢到脚趾,隐秘的血液,密泉在体内扩张,并于某个瞬时,涌现一种独特的意味,强烈的昏暗,破碎的美,未见的空间超越了一个新世界。这个过程,生命的粗犷原力和细腻感受,使我们体验外部世界的纷呈繁富,同时,也抵达内在心境的开阔旷达。
于我而言,不安灵魂的晶体折射的美和激扬的力,始终裹挟着我,一再去触摸时间,开启语言,保持个性,发现它们共同的迷人之处。时间与生命一样,以其轻美的脉动、令人惊奇的节奏赋予我们,与之相遇,记住或者遗忘,都倾向一切可贵的品格,所以,当我写下,它已超越了我所想言说的。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