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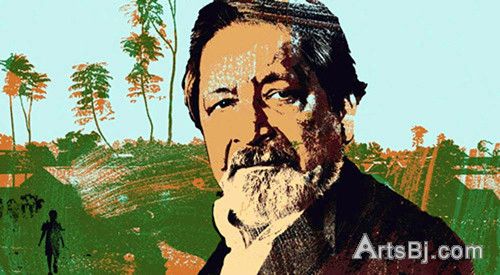
奈保尔出现在上海书展的某架轮椅上,群聊的轻薄显然不能代替因行走而书写下的身体印迹。我们曾透过奈保尔的小说来了解印度、东南亚还有拉美,以及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非洲。现在,让我们退回到作家的作品中,试图进入那个我们正全马力进军的、充满着“动物大迁移”旅游幻想的非洲,那片黑暗大陆,以及真正步入过其黑暗之心的人们。
我们对非洲的理解始终还停留在殖民者的视角。因为这片过于复杂,希腊人熟知的北非与撒哈拉以南完全是两个概念,东西沿海与内陆又截然不同,南非更是非洲最特殊的地方。
要消解非洲的“殖民性”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对非洲的殖民或“交通”从千百年前就已开始:阿拉伯人、印度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到今天的中国人,宗教又从穆斯林、天主教、基督教再到今天的佛教;从文化地理组成上来说,原始部落、民族国家、干旱沙漠、激流瀑布、黑奴贸易、民族解放,整个非洲大陆存在于无数种语言和文化、进步与退步、重建与毁灭之中,要找出完全不含“殖民性”的“非洲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与奈保尔的《非洲的假面具》不同,像迪内森的《走出非洲》或者海明威《非洲的青山》这样的作品,其“殖民性”特色就有些过重了。因我始终对“黑暗大陆”更有兴趣,对作为人的“动物性”的兴趣超过对其他动物与自然的兴趣,也更为认同从外部侵入非洲的殖民视角而非内部人类学视角(比如从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到巴利的《小泥屋笔记》)。所以每次当我思考非洲问题时,总是想着回到几个经典殖民作家,从奈保尔到康拉德,再上溯斯坦利和李文斯坦,用明确的人性来检验人性,用宗教来评价宗教。
早在1979年,奈保尔就写过一本与非洲有关的小说《河湾》。那本《河湾》的政治意味很浓,一个从未直接出面的总统的阴影一直笼罩全书,让人绝望。而这本《非洲的假面具》相隔三十年,奈保尔不再虚构故事,他的文笔也变得苍老而温柔。
《河湾》出版时就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写作的典范。其一,该书以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为背景。蒙博托为了去殖,而将刚果的国名改为扎伊尔。这也是当时的趋势。不料1996年的刚果内战后,国名又“返殖”地改回成刚果,颇为讽刺。所以《非洲的假面具》针对的已是一个彻底处于殖与非殖相互混杂的多元非洲。
其二,奈保尔本人背景比较曲折,作为一个出生在特立尼达多巴哥的印度后裔,先在英国接受了教育,后又游历各国,所以多以后殖民视角,直接而刻薄地揭示发展中国家一些尴尬场景。他不管在印度还是其他所写到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不受到欢迎。但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这又表明委员会对这样“印奸”写作的肯定。
在这篇笔记所要涉及到的奈保尔、康拉德、斯坦利和李文斯顿中,我只可能见到奈保尔。他有非常典型的印度人特征,说话温柔而谦逊,而内容却扎实有力。他说印度是一个“受伤的文明”,他自己的性格显然也是这个受伤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文明的牵挂,他大可以像旅行文学作家比尔.布莱森一样轻松游历,何苦写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书。
每次读奈保尔书的时候,总能体验到他沉重的爱。各国人民所共有的奴性、狡猾、无耻、凶残的品性,对于一个出身于底层、直面内心的敏感写作者而言,都再明显不过。他具有比一般写作者更诚实的品性,用诚实的文字来传递自己的爱。“除非经历挫折的考验,否则爱毫无价值”,奈保尔自己一次又一次对丑恶的揭示,倒正是对自己这句名言的注释。
已有无数人将奈保尔与康拉德做过比较。两者几乎相隔一个世纪,在这之间,非洲经历了潮涨潮落的变化。在康拉德时期,殖民是一个进行时态的观念。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在黑暗大陆上都有最直接的体现。在奈保尔时期,情况已经变得复杂得多。我们对非洲了解得更多,对非洲人也了解得更多。但“观看”非洲的知识与心态,不见得有多少进步。这是奈保尔与康拉德对观的基础。
奈保尔一直声称自己试图在非洲追寻“宗教”,这不是虚言。所有历史悠久,经济欠缺的土地上都会弥漫宗教气氛。奈保尔有他自己的宗教,过去几十年在各地追寻的也是宗教(比如他写非阿拉伯伊斯兰四国的那两本书),这次重访非洲,目的还是宗教。只是最终他看到了更多的所谓伪宗教:巫师神婆、灵药秘药、鼓吹演说。直面它们,揭露,驳斥,对于不管哪种宗教,都应该是最核心的护教精神。
波兰人康拉德的文化负担与奈保尔不同。他用英语写作比奈保尔晚得多,文笔也不一样,更显复杂。短短一篇《黑暗的心》竟然引来无尽阐释,几乎成为文学史的公案。他与奈保尔的背景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表达的触点非常相似。有人说能从康拉德的文笔中获得不同的感受,如鼓舞、安慰、恐惧、陶醉等,这正是康拉德本人与真实世界碰撞后的感受。胆怯、迷惘、不知所措、怨声载道,每个人在与非洲土著接触时都会遇到,奈保尔显然也遇到,只是极少有人能像康拉德那样自然写下来。
很多人喜欢分析康拉德小说中的象征意味,而这本身又是令人讨厌的殖民方法。康拉德提供了象征背景,又提供了殖民时代的非洲故事,却并不意味着要从批判殖民主义来阐释。他在水上漂流了那么多年,深知非洲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原始世界观和宗教观,我们对非洲人的凝视与非洲人对水牛的凝视一样,都缺乏一个共通的理解基础,只有凝视和记录这件事本身是有意义的。
在《黑暗的心》里,库尔兹这个形象总是被解释为堕落白人。他不择手段,他毫无“人性”,他“人格”分裂,他临死前的一句话又是含混不清的“The Horror!The Horror!”这句话所引申出的无尽阐释,几乎可以与耶稣基督死前说的那句话媲美了。可是真正将目光投向黑非洲,投向所谓的“黑暗之心”,思索非洲人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边界,思索热带病和疟疾对人性的塑造,思索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在这个特殊环境下的关系,结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得出。也许“The Horror!”反倒是一个最佳的答案了。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合作的象牙商人,更一般地看,就是斯坦利。他有一本书叫《穿过黑暗大陆》,非洲的黑暗性从此与他相联系。他的声名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堕落得极快,完全被脸谱化成一个不择手段对待黑人的美国白人。他当年寻找李文斯顿博士的经历早在30年代就改编成电影,但随着他的名声毁坏而遭人遗弃。一直到最近,随着他的书信解密,才有一些真正认真对待斯坦利的传记开始出现,比如Stanley: The Impossible Life of Africa’s Greatest Explorer。
我在读这本斯坦利传记之前,就试着把一些文献拼凑在一起,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文斯顿和斯坦利都是19世纪撒哈拉以南内陆非洲探险的两座高峰,无可超越。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历史古迹(在非洲谈论历史的话,又必须重新界定“历史”),一路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无数河流湖泊似乎也没什么(维多利亚湖总是在那里,非洲人早就知道了,你不去发现,也会有人发现),李文斯顿博士的传教成绩在非信徒看来也不算什么。可是他们确实改变了我们认识非洲的方式。
斯坦利领受报纸的任务去非洲内陆寻找探险失踪多年的传教士——探险家李文斯顿。他从桑给巴尔出发,一路往西,最终在1871年11月10日Ujiji的湖边遇到奄奄一息的李文斯顿,说了一句著名的“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我猜你就是李文斯顿博士?)。我总是脑补那一刹那,电光火石,我们寻找到与非洲的共通点。在我心里,黑暗之心就在Ujiji,如果有机会去坦桑尼亚,那里就是圣地了。
两人相遇那一刹那为何非常重要?而且斯坦利为何也要在他的日记里撕去了与李文斯顿相遇那几天的片段。李文斯顿没过多久就死在韦乌卢湖,我们现在只有通过斯坦利的《我如何找到李文斯顿》那本书来推测当时的情景。
斯坦利与李文斯顿对于非洲的情感与认识并不相同。李文斯顿是个传教士,认准目标后一辈子都投入在非洲。虽然他后期的探险工作必然与英国的学术研究,地理探险等相关,但最终的本色还是一个传教士。台湾有一本《深入非洲三万里》就是从传教士角度描述李文斯顿的传记。而斯坦利没有这个负担,不管早期参军还是后来为报纸写稿,进取就是他的天性。李文斯顿想寻找到尼罗河的源头,斯坦利也想。李文斯顿想寻找到一条进入非洲内陆的最快通道,斯坦利也想。最终李文斯顿没有做到的事,由斯坦利得以完成。
可为什么李文斯顿赢得如此多的荣誉,而斯坦利则要背负骂名?最直观的说法是,李文斯顿一辈子没有对黑人开过枪。他并非懦弱,他曾经猎杀狮子,左边身体一直有十多个狮子的齿印,由此赢得非洲人的尊重。而斯坦利治军严格,凡是碰到黑人叛逃开小差,总是毫不犹豫地开枪。他在从刚果河源头一直走到大西洋的路途中,“屠杀非洲人民”。此外他还为利奥波德二世服务,把刚果“出卖”给了欧洲人。
但这些文明人的“生死观”,“吃人观”放在非洲,本就站不住脚。李文斯顿与斯坦利走的不是同样轨迹,面对的不是同样部落,行走的经历,做事的目的也各有不同。李文斯顿一生充满传奇,九死一生,而且最后一次寻找尼罗河源头的探险中,众叛亲离,受尽了向导、土著人甚至印度随从的苦头。药箱被同伴带走,也直接导致他困于内陆。他的身体算是出奇地健康,这才在疟疾和各种热病的折磨下支持了那么久。
杀人和吃人并不是很稀罕的事。李文斯顿自己没有动手,但看到的不计其数,斯坦利也是。马文?哈里斯是专门研究过“吃”的人类学家,特别总结过“吃人”问题。他主要引用西班牙传教士在南美洲所见闻的吃人经历,那都比较早了,一般都是16、17世纪。可在黑暗大陆,一直到19世纪中期,李文斯顿和斯坦利探险时期,还普遍存在杀人、吃人的习俗。而且从李文斯顿的记录来看,非洲部落吃人吃得比南美同胞们“更丰富”、“更多元”,出于更多样的理由而吃人。
野蛮与文明存在着令人惊讶的时间差。欧洲人在15世纪之前不知道美洲,然后很快地将其“文明化”。而非洲大陆的一些情况,希腊人在公元前就很了解。可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尼罗河的源头,现在所谓“大湖区”,千百年来从未有“文明”人能够踏足。所以在南美洲基本“文明化”以后,非洲内陆还是保持着千年不变的“野蛮”。后来的人类学家总是试图消解“文明与野蛮”这样人为构建的对立。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对人和其他动物(如狮子、鳄鱼)的区分。可在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洲内陆,这个区分并不那么一目了然。
有人觉得Dr. Livingstone, I presume?体现了英语的优美,把斯坦利千辛万苦地寻找,简化为I presume。又有人说,如果我是李文斯顿,我一定会当场否认。斯坦利只是在找他和大众心目中的李文斯顿,而无人真正理解把一生都献给传道与黑暗大陆的李文斯顿。真相已经无人知道,我是觉得这两人的相遇和碰撞,传递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明人对非洲的体会。内陆非洲是个恐怖的地方,疟疾、猛兽、洪水、土著人,或者是今天连续不断的部族冲突,都随时可能要命。但李文斯顿和斯坦利都拥有无数当代追随者,都情愿默默无闻地把自己交给这片大陆。这当然是一种宗教情怀,与非洲原始宗教不同的宗教情怀,是我要回到殖民主义非洲视角的根本原因。
吉卜林有首诗叫做《白人的负担》,非常种族主义。我很喜欢他的立场,不妨用“人的负担”作为自己的定位,这也是我有兴趣阅读非洲的基本初衷。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