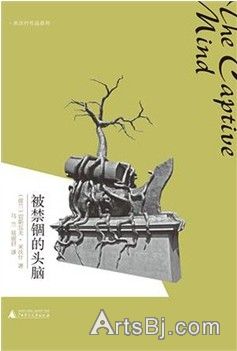
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是米沃什1951/52在巴黎写成,1953年正式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引发巨大轰动,从知识分子思想界波及整个社会层面。当然,主要的反思与争论仍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因为在一定程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一本有关中东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心路历程”的阐释性著作。
对比乔治·奥威尔预言性的《一九八四》,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更有内部的突破的意义。因为奥威尔身在英国,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极权主义统治,虽然他的天才的预见性帮助他在思维层面过上了一种类似的生活,但毕竟不是实证层面的。米沃什则不同,从纳粹到苏联,甚至这两者是反复摇摆,轮换着统治米沃什政治上的国家与生活上的土地,米沃什从内部结构上很清楚极权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与阿伦特站在历史的高地对极权主义的论述也不相同,阿伦特的意义是解构主义的意义,是政治哲学上的,具有祛魅的作用。而米沃什通过亲身经历与对周围的观察展示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受胁迫或甘愿成为整个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以至于失去了道德意义上的人性,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的沦陷与堕落。在本书的前言中,米沃什这样写道:因为,我观察的对象,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这个群体,首先是研究在华沙或者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起着重要作用的作家和艺术家群体。
米沃什描写的这些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很多在过去的某段岁月中正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战前,他们参加反对极右团体和反排犹的活动。在纳粹占领之后,他们把反抗转入地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抗文学与艺术的兴盛。当1945年,来自东方的“新信仰”占领华沙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呈现群体性的异化,那么,“新信仰”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雅斯贝尔斯提到是对“精神的奴役”。
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极权主义,不管其形态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斯大林的苏联--用米沃什的话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些主义之下,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从思想到行动都是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后一种的最恐怖之处正在于:通过列林与斯大林(而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真正做到对人进行精神上的奴役,使其相信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完全被掌握的,未来是完全被设计的,而这过程中的一切残酷便是可以容忍的,包括肉体的消灭;而掌握历史的便是“新信仰”。
这即意味着,来自东方的体制在自诩掌握了历史的钥匙的同时,也占据了道德与理性的高处,而一切反对“新信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人都是反国家、反社会、反领袖、反人民的,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进行思想和肉体的灭减。恐怖无处不在,意识形态鼓吹下的狂热让人与人之间处于谎言与背叛、监督与告密的紧张位置,伦理、道德与良知步入背影之中。
但这只是“新信仰”成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更加触目,来自人的主动附庸。对于苏联体制来说,欧洲部分人是信仰异教的,像波兰就是天主教国家,并且苏联体制本身排斥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为了顺利推行统治,对苏联而言异质的知识分子正可以大加利用。在反对纳粹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对右派极权主义的敌对态度让苏联认为这些异教分子可以逐渐过渡到“接受新信仰的正统伦理”。而对于主动附庸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危机在于害怕边缘化、被甩出政治正确式的历史前进的列车。米沃什并不否认自己也曾是这些知识分子中一员,也曾和“新信仰”体制玩起心理“游戏”(在第一章《“穆尔提-丙”药丸》和第三章《凯特曼--伪装》中都对类似心理进行了详细深入地分析),也直接提到了“只能用母语写作和出版作品”使其难以下定决心抛弃祖国而流亡异乡的芥蒂。
但,米沃什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亡,并写出了这本著作。1951年,米沃什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职位上出走,流亡。巴黎向来是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米沃什的出走,特别是这本书出版之后,他受到彼时巴黎左派代表性人物的攻讦,抨击他是在故意抹黑斯大林的苏联,而粉饰资本主义的美国。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使米沃什受到了欧洲左派的抨击,也受到了很多反苏联体制的人的批评--这其中就包括流亡的波兰侨民--认为米沃什在书中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没有道尽“新信仰”的残酷和绝对的强迫性),被“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米沃什可谓两头不讨好。
批评米沃什的巴黎左派生活在战后平和稳定生命及各种权利有保障的国家中,他们对苏联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蒙昧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他们并不知道奥威尔的预言实际上正在大范围的上演并有从东到西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正是最危险所在,也是米沃什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最重要的警示价值:极权主义离欧洲并不遥远。
1981年,身在美国的米沃什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思维制造出来的吸引力都还没有成为过去;相反,现在它们似乎还有上升的势头。……已经过去的这三十年的光阴,并没有消除这一现象顽强存在的深沉理由。”
《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思想性极强的不朽作品,见证了米沃什从一位诗人、作家迈向了思想家的行列。这短短的一篇文字远不足以道尽本书的精义。
(供生活家杂志,见杂志有删节)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