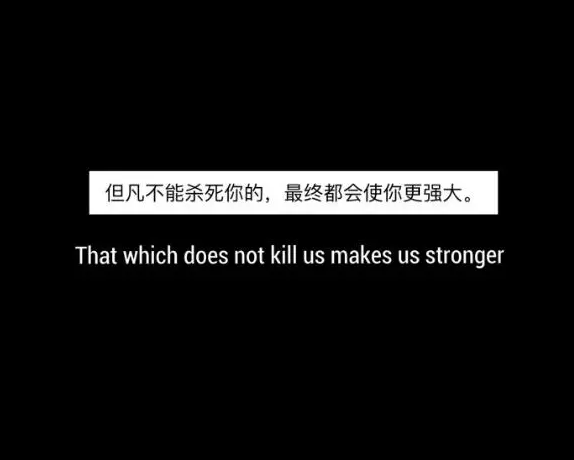
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个样,谁若感觉不同,谁就进疯人院。
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 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涌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
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
道德把人类驯化成了温顺的家畜。
较为相同,较为普遍的人,一向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下去。
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
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
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适于生活的世界,接受了各种体线面,因与果,动与静,形式与内涵。若是没有这些可信之物,则无人能坚持活下去!不过,那些东西并未经过验证。生活不是论据;生存条件也许原本就有错误。
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诚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
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葛,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
谁的思想过于丰富,谁就宁愿把自己变愚蠢。
成熟不过是个性被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圆滑了。
人们的懒散更胜过于他们的胆小。而他们所最惧怕的是任何无条件的诚实和坦白所可能加予他们的烦恼。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而且,这少有的个人还具备反对个体的群体直觉和良知呢。
平淡的生活,往往是最危险的。
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绝不能把不平等者拉平。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
人在哪里看不到意义,人就会否定意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