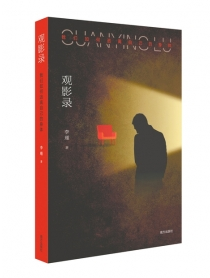
山东人李瑾在北京工作,每天通常坐地铁上下班。从家到单位往返三个小时内,他会在手机上看书敲字。上班一首诗,下班打磨一篇小说的节奏,他硬是把碎片化时间织补成诗集、小说集和读书笔记集。
2018年初,李瑾集中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人间帖》,另外一本是短篇小说集《地衣》,都是他在地铁上写的。不光在地铁上写,李瑾还会直接写地铁。在《人间帖》诗集中有一部分叫“地铁志”,收录了李瑾多首以地铁为主题的诗。李瑾也因此被称为“地铁诗人”。
三年过去了,如今这位“地铁诗人”又出了两本在地铁上写的作品集。一本是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谭诗录》,另外一本是2021年11月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观影录》,两部作品是“姊妹篇”。由于它们是李瑾乘坐地铁玄思的产物,所以文章短小精悍,流畅易读。李瑾以电影或诗歌为媒介,探讨人的“存在”这一终极性哲学和伦理命题。
《观影录》阐释人为什么需要电影
《观影录》是一部哲思类影评著作,副标题是“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李瑾通过探讨电影的不同侧面,阐释电影的生发、运转和价值问题,分析电影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电影等。
在导言和跋中,李瑾提出了创作这本小集子的初衷,提到童年的观影经历打开了自己审视自己的窗户,“一生中总会有些很随意的东西扎根内心深处悄悄改变着某种单调和乏味,电影便是其中一个:当谈到电影,这显然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是移动的面向外在的窗口,又是封闭的空间——那些冗长或沉重的故事总是在镜头的切换中进入终点。有时还会发现自己就是那个镜头,我们跟随着陌生的情节来到另外一种人生,这种体验会让人恍惚间认为身体内部还有个蠢蠢欲动的隐形人——电影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了无数种察知这个世界和自我的视角:我经历的不过其中一个,我之外尚有和人类总数一样众多的生活侥幸或遗憾地擦肩而过了。”
在李瑾看来,镜头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语言,电影不是表达或展示而是寻找和发现,即通过对人的时间性挖掘发现空间中不同面向的自己:“也就是说,电影虽然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实际上在讲述观看电影时的我们,亦即我们尚未清醒地认识自己,并对自己是什么充满了好奇——这就是电影的全部意义。”
在《观影录》正文部分,李瑾从50个“问题”角度诸如时间、困境、正义、自由、启蒙、现代性、视觉、空闲、消费、偶像、身体、身份、反派等,以基本相同的篇幅探讨了电影的不同侧面。李瑾认为:“电影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存在而非真实的东西,即便其在时间上永恒,但眼前或者瞬间又属于谁,这值得思索和追问。”正是这种追问催生了电影,也催生了我们对电影的观看和追逐。
附录一评论了《大独裁者》《摔跤吧,爸爸》等10部中外经典电影。附录二点评了《吾栖之肤》《决战犹马镇》等25部不同类型的电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点评虽然很简单,但一些并不具备艺术感染力的爆米花电影,李瑾都试图找出其中隐含的人性闪光点,这意味着在他心目中,电影和人一样固然有内涵上的鸿沟和差异,本身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附录三收录了李瑾和文化学者安歌的对话,他颇为忧虑地提出:“现代性赋予了我们很多,也剥夺了我们很多——如果连看电影即体验自己存在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就是不存在的,换种说法是这种存在毫无意义,因为我们都被程式化、工具化了。这个层面上,电影表达的或其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忧伤,一种人类自我缅怀的忧伤:人永远在追寻自己的路上,但看到的只是刹那间出现的光影。”
李瑾虽然引用了很多经典电影的对话,但是没有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甚至没有点出哪怕一部电影或角色的名字。李瑾说,“我的意思显而易见,不希望谁将眼前看到的文字和经他人裁剪的镜头/语义对号入座,这意味着我将电影视作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且正企图完成自己的‘人’而非其他。”
发掘电影和人自身的“伦理”关系
在李瑾看来,电影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方式和娱乐活动。普罗大众鲜少有不喜欢或没看过电影的,但很多人意识不到电影和我们自身之间的“伦理”关系。李瑾不是要告诉读者电影该怎么看,怎么挖掘其中的价值意义,而是引导读者对日常的人或者说对一个深度的“自我”进行再挖掘再认识。
在此意义上,《观影录》不是观影指南或拍摄操作手册,更不是指向“花边消息”的秘辛或猛料,而是一本需要相当知识含量和思考深度才能深入下去的思想类读物。李瑾说:“我们不厌其烦地进出银幕显然不是为了体验灾难或欣赏他人的喜怒哀乐——体验和欣赏必须成为现时状态时才是有效的,而是为了获得完整的自己。”不难看出,哲学性或哲思性是这部作品最鲜明的特点,也是目前影评中较为罕见的书写方式。
在和学者安歌对话时,安歌向李瑾提出一个问题:“《观影录》附录部分35部电影确实泄露了你内心的私密即个人的倾向和钟爱。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无论你看什么片子都津津有味,并试图琢磨些什么出来。恕我直言,你点评的一些影片大部分在严格的影评家看来都不入流。”
李瑾回答说:“电影既然是人反复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行动,显然和内在个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因为个我是唯一的、孤独的,他必须对身体内部的那个生命负责,故而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的方式。我当然知道这些影片并不怎么宏大,但必须对时间这个最大的他者有所交代,因此无论看什么电影我都保持思索,哪怕一两句皮毛之得,也算是和自我/时间对话了——众生皆苦,唯我自度,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某种意义上也是超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要对电影中的真理、规则亦即某种神话保持距离,喜欢本身就意味着成瘾性或者说规训。我的做法是,看电影不跟市场,不跟宣传,不跟评分,有时一部电影公映了十几二十年才会去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从来不看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么极端其实是刻意为之而终于无意,我最担心的是别人的评价影响了我。《百万英镑宝贝》获得第77届奥斯卡四项大奖,看名字我还以为讲穷小子发横财的故事,2005年赴美途中百无聊赖,点开机载影院看了,才知道是讲拳击手的。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教练法兰基和学生麦琪借助拳击亦即对方重新发现了自己——电影永远在讲人的自我寻找,无论美还是恶。”
李瑾坦言,他写《观影录》的逻辑基点是:“我们的悲剧在于,双手创造的美好的物质世界转眼就是我们的枷锁,我们用机器管理自己乃是最大的束缚和异化。”故而,他认为:“之所以将电影当作一种新启蒙,就在于人们在这种技术中发现了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人/生活——它允许我们抬起头来观看,并告诉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存在:原来,冷冰冰的工具理性中,还包含人和可以观看、享受的喜怒哀乐。”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