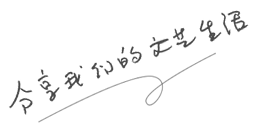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世上有两种美:一种是由直觉直接触发的,一种是通过习得。而将这两者合而为一,并进行融合改变,则将会呈现一种有着极为复杂丰富性的美,而这种美,即是所有艺术评论家都在积极寻找的美。”
——保罗·高更

Lot 113
保罗·高更《花园一角》
1885 年作
油彩 画布
71.8x55.9cm.
来源
艺术家自藏
Emile Bernard收藏
法国 巴黎 私人收藏
Bernard Lorjou收藏
亚洲 私人收藏
展览
2015年10月28日-2016年2月21日“Gauguin: Racconti dal Paradiso”Mudec文化博物馆 米兰 义大利
出版
《Gauguin: Racconti dal Paradiso》 Mudec文化博物馆 米兰 义大利 2015年(图版,封面及第3页)
附法国 巴黎 Wildenstein Institute开立之原作保证书
估价待询
《花园一角》创作於保罗.高更艺术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为了从一名业余画家和商人转变为一名职业画家,高更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而这幅画便意味着这一阶段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高更对新的地点和题材的探索。这幅作品创作於1885年的夏天,画作是在诺曼底周边完成的,或许就在瓦朗日维附近。此时,恰是高更颠簸、辗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平和、宁静的一刻。
——凯特琳·阿德勒 2016年
1848年,高更在巴黎出生,幼年时在秘鲁的四年时光致使在他最初的记忆中,始终潜伏着一个向往蛮荒异乡与原始之地的热梦,而这也径直影响了他在艺术观念上的终极取向。秉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天赋的才华,高更成为一位渐受嘱目的业余艺术家,未受学院式技巧的磨链,反而是他突破传统技法的动力。1883年巴黎发生金融危机,银行倒闭,尽管辞职的举动遭到了他在艺术上的精神导师——毕沙罗以及妻子的极力反对,对艺术的挚爱仍让高更在三十五岁时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股票经纪公司工作。高更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的抉择中,後来选择了理想,最终从业余画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创作中去。高更必然对於收入上的落差有所考虑,但却对与此後将要付出如何巨大的代价毅然始料未及。1884年,一直靠存款维持生计的高更一家不得已举家迁往卢昂,数月後又辗转前往丹麦投奔岳父。次年,因妻子家人诟病高更无法养家而产生不睦,促使高更只身带着儿子克洛维愤然返回巴黎。这一时期的接连遭遇让高更逐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主义心生厌恶,同时也激发着他对此前崇尚的印象派艺术开始有所反思。1885年的作品《花园一角》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保罗·高更
数年中所经历的都市生活的冷漠与残酷,加之天性中本能的孤傲不觉让高更陷入到对城市的叛逆和腻烦之中。因而,巴黎对於他而言,更像是一座毫无生气、沈闷而又压抑的围城。他曾说过:“我最想做的事便是逃离巴黎,巴黎对可怜的人而言像是沙漠!”1886年,艺术家最终选择前往地域偏僻、民风淳厚、未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侵袭的布列塔尼地区阿旺桥村,为了创作出心之所向的世界,而前往一个朴实清净之地。如今看来,高更对於朴素异乡的渴望在1885年达到巅峰,同样也是在这一年,高更显然是在城市幽闭一角的所谓花园中投注了相当充沛的、意求“出世”的饱满情绪。为此,高更刻意选择了一个未经人工修剪、洋溢着原始野趣的自然景观作为描绘的对象。
高更的四季花园
春

保罗·高更《花园一角》 1885 年作
夏

保罗·高更《Rue Carcel的花园》 约1983年作 丹麦 哥本哈根 丹麦国立美术馆藏
秋

保罗·高更《马丁尼克风景》 1887年作 英国 爱丁堡 苏格兰国家画廊藏
冬

保罗·高更《花园雪景》 1879年作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国家美术馆藏
高更早期的绘画带有实验性,也很拘谨,令人联想起在巴比松画派影响下毕沙罗的作品。《花园一角》中,高更在保证画面完整性的同时,着意於营造一个多层次的花园空间:远景中繁盛茂密的树林,中景中数枝隽秀灵动的花木,以及近景中零星点缀的花草。郁郁葱葱的树林被塑造成以深绿色为主色调,同时在局部辅以由深至浅三个层次绿色色度的和谐过渡,在迸发出大自然的风韵灵动之余,也映照出阳光照耀下不同绿色交相辉映的视觉效果。零散的枝叶、野花,连同那裸露在外的砖红色泥土,裹狭着盛春初夏的独特芬芳,在罅隙中透露出少有人惊扰此处的、狂野而又不乏神秘的气息。

Lot 113《花园一角》局部
从再现技法上看,此时的高更似乎不再以印象主义所标榜的“自然主义”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所强调的也不仅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格调的主观印象,同样也诉诸於实实在在的感官体验。为此,尽管在此画色彩的构建上,高更依然参照了印象主义所主张的、光影之下色彩的多变性,却转而倾向於将印象中的世界加以凝固和确定,并逐渐抽离出一种更为纯粹的形式,後来决定到南太平洋法国的塔希提岛居住时终至大成。正如同他所说的:“不要过份临摹大自然。艺术是一种抽象,根源於大自然,藉着作梦而由自然衍生,比起自然更多来自於创造。”在此之後,印象主义艺术中对於线条、色块的有意散乱和解体逐渐消失,高更将笔触放松、变宽,采用单线勾勒以及平涂着色的手法,形成层次分明的强烈色块,平面化结构的表达方式影响了许多後世的艺术家。
在画面主题的选择上,《花园一角》显示出艺术家对於印象派作品常见主题以及对於中产阶级理想生活方式的刻意疏离。在《花园一角》中,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於诸如咖啡馆舞会、草地午餐、歌剧院里的贵妇、泛舟湖面的休闲时光,甚至是阳光下穿着洋装、撑着阳伞的金发女郎都统统消失不见,画中所展现的、非人工化的自然风光让人们得以暂时规避现代社会中充斥着的种种虚荣、罪恶以及残酷现实。显然,在高更那里,他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罪恶之源在於文明,只有到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之地中才能找到孕育人类最为原初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只有在那里,才能寻到现代艺术得以真切滋养的源泉。因此,可以说从《花园一角》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更艺术创作进程中的重要转型已经开始。
《花园一角》曾由同为艺术家的埃米尔·伯纳德所收藏,伯纳德是“分隔主义”和“象徵主义”的代表人物,更是梵高和高更的挚友。伯纳德与高更相识於1886年的夏天,两人在隔年重逢时一见如故,迅速成为知己,虽然高更较伯纳德为年长,但年龄的差距并未阻碍他们的友谊。他们双双寻求新的表现力量,主张艺术应具备有力、率直而普遍的相同象徵,以舍弃细节及特徵,并经过压缩的感觉,强烈而集中地表现印象、观念和经验三者的综合。高更因此而走出了印象派画家那种琐碎的光影、固定短暂景象的意图、以及对文学借喻的逃避。可以想像高更在赠与《花园一角》给伯纳德时,两人感情肯定处於巅峰,代表说这件作品在高更心目中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足以见证他们的友情。可惜好景不长,在高更名气越来越大的同时,两人因阿旺桥画派领导者归属而引发争吵,他与伯纳德的友情未能延续。对於高更而言,作品《花园一角》承载着他在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上得以觉醒的开始,并接续着他在此之後创作中对於蒙昧未知国度的无比痴狂和对於主观艺术表达的无限执着。而这些,无疑在由学院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西方艺术史地图上具有着维度走向上的转折意义。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