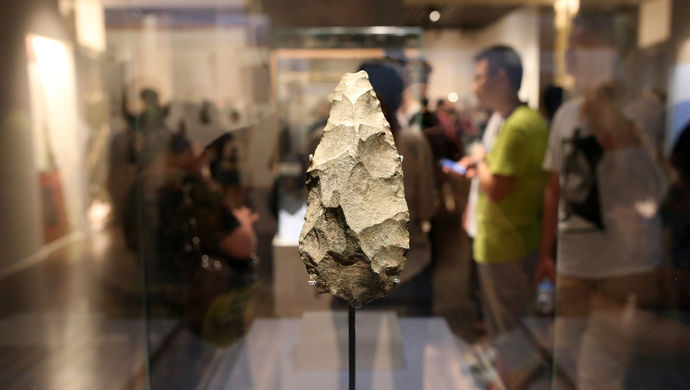
轰动沪上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已经落幕,但关于展览的思索并未结束,甚至正在开始——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正是这一年度上海文化大事件的价值所在。
在知名策展人、著名艺术史专家巫鸿看来,百物展之所以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并没有大谈历史,而是教人们“怎么看”。
个中诀窍,用更浅近的话来说,就是“讲故事”。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
满怀憧憬地踏入博物馆,期待获得鲜活有趣的知识。但结果是,眼前的展品琳琅满目,展现的是一个丰富的世界,但是依然遥远,甚至更加神秘。
明明走近了物理距离,结果却拉远了心理上的距离,你收获的只有莫名的挫败感——到头来,博物馆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旅游景点,满足的只是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到此一游”的虚荣。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是因为观众没文化才看不懂?还是因为博物馆没有讲好故事?
如果这一现象成为普遍存在,那么势必难以归咎于前者。相反,后者需反躬自省:是否做到了向公众好好“讲故事”?
“透露着一股傲慢”
丽贝卡·卡其是一位独立策展人,几个月前,她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艺术专家加布里埃尔·内尔博士参观了中国的某家博物馆。
“昏暗的展厅透露着股傲慢,馆藏大量珍品陈列在密闭的展柜里。展品旁皆附有标示告知眼前的展品内容——例如:‘花瓶,南宋,12世纪’。”丽贝卡这样描绘自己在博物馆的所见。
尽管文物不可谓不精美,馆藏不可谓不丰富,但离开博物馆时,两位专家满腹怨言:“我们怀抱着了解中国陶瓷的期待踏进博物馆,但我们的大脑却被极其专业和碎片化的信息轮番轰炸:‘鸟纹陶罐’‘石岭下型’‘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800年左右’……没有解释鸟纹的意义,没有介绍石岭下陶器的特点,甚至也没有指出马家窑的位置。”
加布里埃尔有些恼怒:“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应该关心这个罐子?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些东西?”
丽贝卡的抱怨则更加理性:“展览从头到尾都没向我们解释这些藏品的重要性。我们离开博物馆时,没能更加了解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我们见到的陶罐或许曾被横冲直撞的军阀窃走;又或许,旧时它曾用作国内战争各派之间重缔和平的物件。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博物馆却保持缄默不语,我们便永远没有机会听到它们的故事。”
展品不会自己说话,如何讲述故事?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展览文本。一张张铭牌,一段段介绍文字,以及说明性的图表等等,不仅承担着解说展品的重任,更是重要的沟通桥梁,时刻引导着在观众与展览之间建立欣赏、感受、理解的关系。
但在不少博物馆,观众看到的大多数铭牌,只是程式化地交代了文物的名称、年代、材质,而吝啬于提供更多的信息。
业内人士坦言,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博物馆的通行做法——把展品的信息点和知识点进行整合,按照类别进行博物学编排,“就物论物”地呈现。
在专业人士眼中,表述简洁,保证了学术上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但在观众眼中,寥寥数语的说明文字,枯燥无味,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点。看多了,更变成了密集的碎片化的信息轰炸,只会让人疲惫和乏味。
一条注释的距离
“我们业内有一个术语,叫作‘博物馆疲劳’”,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硕士、独立博物馆教师陆天又解释说:“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会逐渐出现精力耗竭、注意力涣散、认识活动机能衰退,产生疲劳感。通常,游客参观一个半小时后,这种‘博物馆疲劳’就会发生。”
在“博物馆疲劳”中,腿仿佛铅锤一般沉重、脚又酸又疼,是一种生理现象;而脑袋像塞满棉絮一般昏沉,则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正如丽贝卡和加布里埃尔的参观体验,即使展品再“高大上”,只要从展览中的任意细节感受到博物馆的“傲慢”和“吝啬”,参观者的热情就会被打击于无形之间,接下来的参观便越来越索然无味。
有时候,这种“打击”只需要一个字就能实施。
“比方说,参观古代玉器、青铜器、陶瓷时,常常看到一些冷僻字,像盨、簠、卣等等。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连读都读不出来。这时候多么希望边上能有个注释,哪怕是标个拼音也好。这应该对展览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就偏偏没有,只能从下面的英文说明中勉强猜。”
陆天又的这种感受并不属于她一个人。一个观众和一件展品之间,往往就这样隔着一个拼音、一条注释的距离。这些微小的距离不断累积,终成为宽宽的鸿沟,将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阻隔在外。
让人反感的叙述
丽贝卡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她疲惫地经过展厅时,无意间注意到了一只不起眼的银制器皿。一旁的标识告诉她,这只老旧的杯子曾经一次次盛满啤酒,还顺带讲述了荷兰酒文化中的一些趣事。
“我脑中立刻‘看见’了‘权力的游戏’一般欢腾的场面。虽然这不是历史事实,但重要的是,它让我沉浸在了中世纪的荷兰。”
自称“非业余博物馆达人”的沈辛成,本科时就读北大考古系,课余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担任讲解员。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接待一位外宾,讲完一圈之后她说,你们这个博物馆比有些所谓的世界大博物馆强多了。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博物馆的生命力未必在于‘家当’有多丰厚,而是取决于你的叙述。”
传统博物馆的叙述方式类似于学术报告:分型定式,把东西按照时间序列、考古学标准码放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任务就完成了。
沈辛成分析:“考古学的类型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然非常重要,那是给研究打底子的;但是作为一种面向观众的叙述,这是不合格的。”
学术研究的过程应保持严谨,但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不应过于刻板。
在这点上,沈辛成对震旦博物馆相当赞赏:“虽然没有国宝级展品,但整个叙事非常带劲。它不仅教审美,还给你全方位地展示玉器的制作流程,详细地一步步拆解给你看。你一旦对玉器的生产工艺有所了解,就不会仅仅执迷于那些玉器的价格有多高昂,而是更全面地领会了一个手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个神秘的东西就落地了,亲切了。”
作为讲述者的博物馆
如何“讲故事”?
“故事”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在日前结束的“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精品展”上,展出的49通明代吴门书画家的手札旁都标记了文言文原文,并翻译成白话文。
展览现场,有一封文征明写给妻子的《致妻札》。“银两够不够用”“不要与大哥计较”“棺椁有没有砌好”……看到大才子对老婆的“殷殷嘱咐”,参观者无不会心而笑。
“绝大多数参观者都是看不懂草书的。这次提出加原文和译文,有些专家还觉得没必要。但对博物馆来说,这种讲述方式必须转变。”在上博教育部主任陈曾路看来,这个小举措对上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进步。
在上博馆藏中,这49通手札的文物价值并非是最高的,但经过学术性的梳理和挑选,再翻译成普通观众能理解的白话文,当它们互为映照、以一个整体出现时,俨然成为还原当时吴门名士的生活与艺术的最佳载体。
展览期间,上博还特邀上海评弹团,用传统曲艺和吴侬软语把手札的内容演唱出来,并进行了网络直播。这次多媒体融合的跨界创新,自然也是博物馆想要“讲好故事”的尝试。
在上海,不少博物馆已经形成了“展览+讲座”的“标配”,借助专家的专业性,对展览进行更好的阐释和导览。而在国外,博物馆更倾向于借助志愿者这样的普通人,把“故事”讲得生动、动情。
沈辛成曾走访美国80余座博物馆,并写成名为《纽约无人是客》的“博物馆地图”。
在美国众多博物馆中,沈辛成对一些社区博物馆印象深刻。“这里的志愿者就是附近的居民。他们讲解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自然充满感情。”他们也是这个展览中的展品之一;而展览也通过他们的讲述,具有了深刻的感染力。
如何展示一只牛蛙
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理想展览,究竟什么样子?
陆天又推荐了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旧文《如何展示一只牛蛙》,作者是纽约动物学会会长威廉姆·G·康韦。在这篇被西方展览业奉为“行业圣经”的文章中,康韦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梦想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展示”。
在这里,没有人造的展室,只有真实的自然环境,参观者可以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到牛蛙栖息地,隔着隧道的玻璃幕墙观赏到牛蛙在水下生活的场景;
这里的展示生动而清晰:曲线墙面和立体模型展现牛蛙与生物圈的关系,把牛蛙和它的“亲戚”放在一起,令观众了解蛙类的概况。“牛蛙进化史”用手绘方式演示从单细胞动物到人类的生命进化过程;
在一间名为“池塘春夜”的大厅里,静谧幽暗,香蒲发出沙沙声,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将参观者带入下一个主题“牛蛙的鸣叫功能”。
展览馆内播放名为《牛蛙世界》的影片,讲述一只野生牛蛙从卵到死亡的生命历程。考虑到孩子的注意力,影片时长控制在12分钟内。
虽然技术条件有限,但展览并没有忽略互动游戏,孩子们按个按钮,就能根据牛蛙的外表猜猜它的栖息地。
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展览,涉及牛蛙的生殖、生长和发育,食物与天敌,特殊的适应性和感觉器官,跳跃与着陆等方面;
这也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展览,说明牌特意设置两种高度,深浅不同的内容分别提供给父母和孩子,提高父母的参观乐趣——提升他们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这也是一个有温度的展览,最终指向的是“明天你的池塘里会有牛蛙吗”的反思。
“虽然康韦讲的是牛蛙,但这种‘讲故事’的态度和方法毫无疑问适用于任何一件展品。”陆天又说。
从“物”到“文”
如康韦所言,“讲故事”不仅有“术”的层面,更是某种理念和使命。
博物馆能否讲好故事,取决于博物馆对“讲故事”的理解。如果博物馆能自觉地以此为己任、为使命的话,那么所有的难点都不成为难点。
其实,最早的博物馆,与“讲故事”并无关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搜罗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主要用于观察和研究。私人收藏国有化,这便是博物馆的由来。
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水生的研究,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1970年代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博物馆功能的界定,“收藏”“保管”“研究”“欣赏”是其中的关键词;1970年代以后则着重强调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博物馆应该为社会服务,面向受众。
“过去,博物馆高高在上,是‘文化殿堂’、‘历史宗庙’。但在这个时代,博物馆不能继续高傲。”在陈曾路看来,这种定位和心态的变化,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之前,时局动荡,大量国宝散落于民间。这一时期,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从民间搜集失散国宝,以国家的力量保护起来,供更多人了解、研究历史。此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设施建成使用,文物工作重点从收藏转向展示。再后,“以人为本”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博物馆的理念也在同步变化。
陈曾路将其概括为“从物到文”;“我们说的‘文物’,过去侧重点在“物”上,现在则是‘文’。以前我们的眼睛里是价值连城的瓶瓶罐罐;现在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瓶瓶罐罐里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
世界上最棒的地方之一
“我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时,最大的干扰往往来自家长。‘哎,你听呀’‘哎,你看呀’‘哎,你记住了伐’‘哎,你回去要写作文的哦’……”陆天又感叹。
其实,我们走进博物馆,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愉悦,在这种愉悦里培养兴趣和审美。
“上海人常常说,一件东西过时了,‘好进博物馆了’。潜意识里,博物馆还是一个收藏古董的仓库。”陈曾路说。而沈辛成则开玩笑说:“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一生来两次的地方。一次是孩子时候被家长带来;第二次是自己是家长的时候带孩子来。”
历史原因使然,人们走进博物馆时往往自带敬畏感。在那些“一生只去博物馆两次”的人的概念里,博物馆仍旧是一个庄严的课堂,一踏进博物馆,就应该进入信息接收的状态,时刻准备着从一个严肃刻板、但永远正确的老师那里获得知识的灌输。
“博物馆是人的记忆,而不是物的记忆。”正如陆天又和博物馆的结缘——3岁时,她跟随父亲陆又青参观了人生中第一家博物馆,此后便成了博物馆的常客。不记得博物馆里有些什么,只记得在这里留下的欢笑。当时她就认为,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之一。
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做一个静心的聆听者和用心的对话者?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