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认为葛任就是贾宝玉,瞿秋白就是贾宝玉,应物兄也是贾宝玉,无数贾宝玉都在不同的时代中处理着知识人和时代的关系。《红楼梦》的续集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续写

图/姜晓明
昨日重现
李洱在鼠年春节前回到了河南济源。他准备在老家待到正月十五,他的奶奶要在那天过九十五大寿。新冠病毒改变了这样的计划。他在大年初三匆匆回到北京。他如今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家里的垃圾,然后等待着垃圾再次落下。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陪孩子上网课。“疫情对下一代是一种教育。”李洱说,“他们以前生活得非常轻,现在他们认识到了生活重的一面。”
跟李洱再次进行电话访谈,才想起去年12月1日在北京第一次访谈时,武汉已经有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李洱彼时奔波于各地,参加活动,有公事,也有私事。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出行最为密集的时段。
他患上了急性咽喉炎,12月上旬的几天,他出席华东师大和上海作协的活动,讲话声音低沉。晚餐时,他都喝的果汁。有医生通过他的太太告诉他,医院里有类似SARS的病毒被发现,让他小心。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李洱在三个月之后思考。“当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后,都没有料到之后会蔓延到这种地步。遗忘的机制在起作用。”
华东师大的北山讲堂上,李洱回忆了翻越枣阳路校门的时光。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83级的学生。他进入大学时,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耀目之时。这座城市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80年代最重要的群体之一。“80年代,所有中国人都是进化论者,都认为明天比今天好。思想开放,日新月异。”李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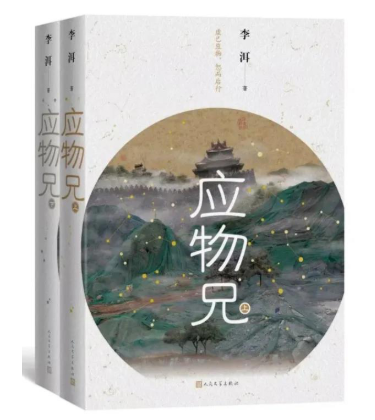
80年代的一个场景在李洱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甚至把它写进了《应物兄》里。“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他的到来让人们激动不已。李先生到来的前一天,应物兄去澡堂洗澡,人们谈起明天如何抢座位,有人竟激动地凭空做出跨栏动作,滑倒在地。”这个场景发生在1988年的虚构的济州大学。而在非虚构的1986年的华东师大,李泽厚的到来是那个时代的轰动事件。那是一个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的时代。我在十年前采访过李泽厚,他说,“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走走。”而他2014年到华东师大“伦理学研讨班”开坛授课,更是一件罕事。他已经多年没在大学讲课了。“前年李先生又到上海某大学演讲,李先生刚一露面,女生们就高呼上当了。她们误把海报上的名字看成了李嘉诚先生的公子李泽楷。”这是《应物兄》里的另一段文字,几乎是当年新闻的再现。
李洱在华东师大忆及这段往事,彼时在场者津津乐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李师东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在颁奖前见到应物兄,我说你写李泽厚老师在华东师大讲座,我在现场。没错,就说了不到一刻钟。那是1986年。应物兄很得意:我没瞎写吧。”现在,朋友们喜欢直接称李洱为“应物兄”。
在上海,李洱似乎一直在虚己应物之中。上海历来是一座“码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话和吃饭。黄浦江有两岸,人也有不同的麦克风和杯盏。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台子上讨论他,这可能说明了他的人缘,他的平衡能力,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船在江上,你要看到两岸的风景。马在山中,你要看到两边的山峰。”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黄平是研究李洱的80后年轻学者。《应物兄》的结尾,应物兄被车撞倒,一个声音从天上飘来:“他是应物兄。”黄平觉得这句话拆解了以往的二元对立,将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向前再推一步,塑造出第三重的自我:局内人自我。李洱在1999年12月的《局内人写作》中解释过这个概念。黄平把这叫作“第三自我”。
李洱喜欢加缪。黄平说,“作为李洱最热爱的作家,加缪可以被视为李洱写作的思想背景。”
疫情当中的一个午后,我和李洱在电话里聊起了加缪和《鼠疫》。这让我想起李洱将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午后的诗学”,那是一种连接正午和夜晚的写作,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收敛。这还让人想起加缪说自己的思想是“正午的思想”。
李洱最近没有读加缪和《鼠疫》。他倒是在2014年的一次关于加缪的读书会上说过,“他(加缪)写出这个城市在面临这样一种疫情的时候,整个特征,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他的结尾写得非常精彩。我们认为非典结束就胜利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就很少再想。”这句话像谶语。2003年过去17年之后,这一切重来了一遍。

加缪是李洱喜欢的作家 图/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已知和未知的日常
回到12月1日的午后,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李洱为了说明奥登对于诗学的拓展,背诵起了奥登的《怀念叶芝》:“但是那个午后,却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唯一/流言的午后,到处走动着护士/他身体的各省都反叛了/精神的广场空空如许/寂静已经侵入大脑的郊区/感觉之流溃败,他成了他的爱读者//如今他被播散到一百个城市/完全交付于那陌生的友情/而在明天的盛大和喧嚣中/掮客依旧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咆哮/穷人面对苦难依然寂然无语/当蜗居的人们某一天想起自由/他们会想起这个午后/想起他倒在一个凄冷阴暗的日子/并且在迥异的良心法典下受到惩处/一个死者的文字/要在活人的腑肺间被润色。”他背得非常投入,沉浸在奥登的诗句中。
“奥登为什么怀念叶芝?因为在叶芝之前,在现代派诗人那里,诗歌是自我的抒情。到叶芝这里,他提出诗是和自我的争论。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废话,和自我争论产生的是诗学。到了奥登这里,又往前发展了,跟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李洱边背诵诗句边穿插着解释,“但这太难了。”如何反思知识,如何让知识进入小说,进入文本,这是他要思考的问题。《应物兄》是他在一部中国小说里大面积处理知识的尝试。
在上海的饭桌上,他同样被要求背诵《怀念叶芝》。他患有咽喉炎的嗓子没能就此推辞。他在大家举起的手机中,将几天前背诵过的诗句又重复了一遍。
李洱曾经说起过话筒。一个人历经阻难,一步步走到话筒前,举目皆是手机时,还能否保持住自己?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考验。我们握有话筒的时候,该发出什么声音?
疫情之中,有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录一首诗来表达对抗击疫情的支持。他没有在提供的选项里做选择。他选择了甘肃支援湖北医疗队一位护士弱水吟写的《日常》:
雾霾,阴雨
五天里,潮湿和凄静
冷和毒,泪和伤
这些灰暗的词
多么希望你们远离
在宾馆自我隔离
没有时间,没有日期
没有声音和空气
写材料,心理干预
将一百颗畏惧的心安放在各自的手心
将颤抖,恐惧,哭泣和绝望
和那些沾满的毒一起丢进垃圾
一个人的房间里
划分半污染区,清洁区
洗手,洗手。口罩,口罩
强迫改正一切恶习
现在,谁都知道毒是蝙蝠的错
而防毒的罪是那么轻描淡写
十七年前的毒我还记忆犹新
今天是昨天的翻版
而毒却不是昨天的毒
它的狡猾是人惯出来的
强传染也是人溺爱的果
深夜,我最想做的
是给藏在洞穴里的蝙蝠
穿上钢铁盔甲
刻上武汉两个字
让所有的刀刃无处下手
让所有的牙齿难以啃噬
李洱把这首诗称为“新国风”。“‘风、雅、颂’中的‘国风’,是来自民间的诗词,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风貌和深情。老百姓的心声,平白如话,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修辞。”李洱说。
李洱将这些诗句转发到朋友圈。他转发的一些文章,配有犀利的文字。在电话里,我再次说起《鼠疫》的结尾。李洱坦白地说,他在《应物兄》里写到济哥的时候,就是受《鼠疫》结尾的影响。济哥是《应物兄》虚构之地济州消失的一种蝈蝈,后又获得重生。李洱想表达希望所在,同时也想表达,这是某种病毒式的存在。
在李洱成名的《花腔》里,他直接写过病毒——巴士底病毒,这种虚构的源于法国的病毒经由一条狗传到了中国,书中主要的人物“蚕豆”被此病毒感染,差点死掉。而到了《应物兄》里,巴士底病毒以知识的形式又重新出现了一遍。知识和人在李洱的小说里正在连成整体,形成庞大而繁复的体系。
《应物兄》里,邓林说:“老师们肯定知道葛任先生。葛任先生的女儿,准确地说是养女,名叫蚕豆。葛任先生写过一首诗《蚕豆花》,就是献给女儿的。葛任先生的岳父名叫胡安,他在法国的时候,曾在巴士底狱门口捡了一条狗,后来把它带回了中国。这条狗就叫巴士底。它的后代也叫巴士底。巴士底身上带有某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染上这种病毒,人会发烧,脸颊绯红。蚕豆就传染过这种病毒,差点死掉。传染了蚕豆的那条巴士底,后来被人煮了吃了,它的腿骨成了蚕豆的玩具。腿骨细小,光溜,就像一杆烟枪。如果蚕豆当时死了,葛任可能就不会写《蚕豆花》了。正因为写了《蚕豆花》,他后来在逃亡途中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日本人杀害了。”
这段话可视作是《花腔》和《应物兄》相连而成的某个结点。葛任是《花腔》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所写的《蚕豆花》,是寻找小说谜底的核心线索。读懂了这些文字,才能进入李洱小说的语汇节奏。李洱仿佛给自己的小说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最核心之物是什么?是真实吗?或者什么都找不到。洋葱需要读者动用智力去剥开,所以读他的小说并非轻松之事。
《花腔》后记里,李洱流下眼泪,“几年后,我终于写下了《花腔》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主人公之一,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如今的法学权威范继槐先生,对人类之爱的表述。范老的话是那样动听,仿佛歌剧中最华丽的那一段花腔,仿佛喜鹊唱枝头。但写下了‘爱’这个字,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的雪花,此刻从窗口涌了进来,打湿了我的眼帘。”
李洱在写《应物兄》的后记时,也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将眼泪写到后记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樊晓哲亲眼看到了这些眼泪。她站在桌边,看到李洱正在修改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我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身形音节上是不是合衬。刚刚念完非常简短的第一段,我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我看到一个热泪盈眶的李洱,这是认识十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如此动容。”
这其实跟李洱平时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差距。他在人前表现得更多的是健谈和幽默。李洱不太喜欢说自己的个人经历,说的大多跟书有关。比如在某天早上一开门,发现责编刘稚站在门口,要他签下新书的合约。比如还是在与新书合同有关的饭局上,他没有答应在作品未完成之前签字,他说不希望“商品”成为自己写作的牵绊。他会说起饭局之后,出租车司机错将他送到另外一个小区。酒后走不动路的他在路边就睡着了。醒来之后,他的笔记本电脑没了,那里有他并未备份的《应物兄》电子稿。公安局帮他找电脑的那几天,他的头发陡然变白不少。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应物兄》写了13年。13年里,这部像戈多一样难以到来的小说,让许多人都快忘记了。“《应物兄》删掉了135万字。”李洱看着我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批评家黄德海到我家里,说让他看看那些被删掉的部分。我打开电脑给他看。他说,你真的写了这么多字啊?我们以为你在玩行为艺术呢,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应物兄》,想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言知行合一的难题和困境。”这是李洱告诉樊晓哲的话,樊晓哲转述给了我。
李洱用13年的时间琢磨这个问题,力求准确。他欣赏阿赫玛托娃的一句诗:步步都是秘密,左右都是深渊,脚下的荣誉,如同枯叶一片。“左右都是深渊,要无限逼近真实,多写一句就是假的,少写一句就不够真。”
永恒的贾宝玉
在北山讲堂旁的一个房间里,李洱在忙着给几大摞《应物兄》签名,我跟黄平在旁边说起《花腔》。黄平仿佛是历史悬案的调查者,他像侦探一样发现李洱小说文本里那些和历史的对应之处。比如说,葛任的原型是不是瞿秋白?还有那本叫《逸经》的杂志,在小说里刊登了《蚕豆花》,在现实里刊登了《多余的话》。黄平追文索字,找到了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洱则说,《逸经》完全是虚构的杂志名,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杂志。“黄平告诉我时,我被吓到了。”若如此,这将吓到所有人,一本虚构的杂志在现实中登载了同名杂志相似的内容,换了谁置身其中,都会被吓到。
黄平并不如此认为,“李洱老师不承认啊。”李洱在几米之外,边签字边说,“我不承认。”
李洱在很多场合对黄平的研究表示过赞许。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就说到了黄平是极少数注意到《花腔》与贾宝玉之间有联系的研究者。“他看到了《花腔》里的大荒山和青埂峰,这些之前被读者忽略了。”他觉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作品获得了这样的读者,一部作品才算真正完成了。
李洱认为葛任就是贾宝玉,瞿秋白就是贾宝玉,应物兄也是贾宝玉,无数贾宝玉都在不同的时代中处理着知识人和时代的关系。《红楼梦》的续集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续写。而如何续写《红楼梦》,才是合适的呢?
因为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提起《红楼梦》,不断有人拿当代人续写的《红楼梦》给李洱看。“这些书写得非常好,我一时分不清是当代人写的还是高鹗写的。”李洱说,“我就问,作者有没有写实的小说。有的还真拿来了,但完全不能看。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能用续《红楼梦》的方式来续《红楼梦》。”
在北山讲堂,李洱讲起了施蛰存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肉身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舌头变成了舍利。他并不纯粹,他带着情欲。“一个能像玄奘一样留下舍利的高僧,在我们的印象中,一定跟肉欲没关系的,跟权力没关系,但在鸠摩罗什身上,外界的一切诱惑跟他都有关系。”
李洱用感冒的嗓音艰难说话,就像是鸠摩罗什在凉州城里表演吞针。鸠摩罗什把很多根针在众人面前拿出来,一一吞掉,但最后一根针没吞下去,卡住了,没人看见,他用手掩饰,巧妙地从舌头上拔出了针:你看,我全部吞了下去。
把现实比作针的话,舌头说出了很多传统。舌头忍受了现实中的苦难、情欲和折磨。每根针都是对自己的诫勉和惩罚。“为了保留一口气,我要把这根针从舌头拔出来。我保留了这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小说。”李洱在说鸠摩罗什,也似乎在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小说家们。这是《鸠摩罗什》结尾的“针”,也是《花腔》结尾的“爱”,还是《应物兄》结尾从远处飘来的“声音”。肉身与灵魂在那一刻“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这是李洱提出的疑问,这也是他的小说。
除了《鸠摩罗什》,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将军的头》,处理的仿佛是久远的故事,但仍令观者觉得新鲜。施蛰存用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方式写了最流行的小说。高僧的语言完全是现代的语言,不是高僧的语言。“这是最现代的戏仿。”李洱觉得这表明了施蛰存的写作是在场的。施蛰存的写作可以介入到当代写作的所有问题中来。用《红楼梦》作类比,就是他用不是《红楼梦》的方式续写了《红楼梦》,贾宝玉在现代获得了新的肉身。
“小说家就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小说家生活在词与物的罅隙之中,从词与物之间狭小的空间穿行而过。”李洱坐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他的言说在某些时刻会进入诗意的情境,让台下之人为之着迷。
他的师承
与李洱的电话访谈在现实的疫情和小说的文本之间来回切换。在某些时候,会忽然融为一体。他对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非常感兴趣,那是一颗“洋葱”的核心。他忽然说,“葛任的代号就是零号啊。零号就是趋于无,让他消失。零号是巨大隐喻。代表了一种像气溶胶一样的东西,若有若无,似有似无,感觉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关心新闻,会对其中的进展情况做自己的分析。
在李洱看来,写作者可以分成感性和理性两类,还有一类是知性,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感性的作家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得好。“加缪和库切显然不是这样的。”李洱说,“库切是加缪之后最重要的思辨型作家。”
“你自己是哪一类?”我问他。
“我大概也是知性吧。”
李洱欣赏库切的《耶稣的童年》。耶稣在《旧约》和《新约》里是两种形象。耶稣的形象是变化的。库切思考的是耶稣在此时代,会是怎样的形象?在库切的笔下,耶稣的故事成为了现代移民的故事。《旧约》、《新约》和现代的土壤连接成一体。历史从源头流淌到了现在。
“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化源头开始思考。”李洱说,“我们在半世俗半宗教的儒家体系里,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如何跟知识相处?”这个问题在李洱的思考里,可以具象为——贾宝玉不断换了肉身。那个出现在现代社会的“耶稣”,就像是出现在李洱小说里的“贾宝玉”。
李洱在澳大利亚悉尼图书馆开讲座的时候,库切去听了,李洱事先并不知道。李洱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发现下面有个人长得像库切。库切听完就走了。李洱问澳大利亚人,那人是不是库切。随后,他看到库切走出图书馆,“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非常孤寂的背影。”
“我写库切的一篇文章,估计他看到了。”李洱说,“我写过一篇《听库切吹响骨笛》。”
这篇文章曾被作为上海市的高考语文模拟题。“我想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
阅读题在此处提出了问题——如何理解“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李洱。“‘经验的熟悉’是指这里面所说的革命者的形象。‘文学的陌生’是指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处理。在我们的小说里,革命者的形象往往是高度简化的。”这是李洱的答案,不知是否符合标准答案。
在《花腔》里,李洱试图重新认识“革命者”。他的新历史主义式的写作尝试让他被视为先锋作家。他在先锋作家们驶入经典区域时,最后跳上了列车。
有一次,李洱和苏童都在香港,一起吃饭。李洱拿起酒杯,说,童兄,我敬您一杯酒。苏童说,你把酒杯放下,我是你叔叔。文学有辈分的。从此,李洱就叫苏童为“童叔叔”。
李洱读大学时开始写作,那是所有人都想成为诗人和小说家的年代。文学是所有人的梦想。“别的系的学生都想转到中文系。文科最好的学生都在中文系。”他开始读一些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作家的作品,比如博尔赫斯。在此之前,他只知道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小林多喜二。
1986年,马原到华东师大讲课。作为学生的李洱现场提问,你的小说和博尔赫斯有什么关系?马原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马原下来后跟格非说,你们有个学生很厉害,问我和博尔赫斯的关系。
那是文学的正午,现在是午后,“那种朝气蓬勃的、对生活有巨大解释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午后是一种复制的、慵懒的、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光。”
午后的混沌状态中,李洱似乎一直保持清醒。他总能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说起那些曾经写过的句子。“《花腔》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谁说的。有一次,我在路上走,一个翻译家打来电话,跟我商量某一句话的翻译。我不需要翻书就能脱口而出,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这段话的语调是什么样的。我不是吹我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是想说明,当初的反复推敲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李洱说,“我想,很多读者其实都能从主人公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命运。”
作家路内曾经说,我算了算,李洱写《花腔》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这怎么可能呢?
动笔写《花腔》这么一部繁复的作品时,李洱32岁。
“之所以写《花腔》,跟自己家人的经历有关。”李洱的家人中有去过延安的革命者,这让他对中国的革命史有了不一样的关注。
李洱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爸爸是中学语文老师,爷爷对中国历史地理非常熟悉,有人说他爷爷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这让他跟别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不一样。他有一个接受外来知识的窗口。他从那扇窗口到达了今天。
尾声或开始
李洱在朋友圈转发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疫情中的讲话。默克尔在电视上说,“我深信,当所有国民都把这项任务切实当作分内之事,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因此请允许我对你们说:情势严峻,请务必认真对待。自德国统一以来,不,自二战以来,我们的国家还从未面临这样一次必须勠力同心去应对的挑战。”李洱则觉得,从影响的范围来看,这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2008年,默克尔访华时,曾把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默克尔多次访问中国,不止一次接见过李洱。“她会摸摸你的衣领,表示一下问候。”李洱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李洱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目前只有《石榴树上结樱桃》。电影拍完之后,剪辑修改了五年。他在单向街书店看过一次,看的时候想走,被人拉住。之后,他在美国一家电影院又看过一次,在场的观众只有五个人。李洱跟苏童说起美国的情状。苏童说,我跟你一样,我在美国看《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院里也是五个人。
2008年,在被默克尔接见之年,奥运之年,原本是喜欢看体育节目的李洱计划完成《应物兄》的时间,他没想到收尾时,又过去了11年。他已人至中年,有了孩子,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应物兄》围绕着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办而展开。他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中国大学里还没有儒学研究院。如今,到处都是。“我跟朋友们说,我刚开始写的是未来主义小说,写的时候变成现实主义小说,写完之后变成了历史主义小说。”李洱说罢大笑,这是他的经典笑声。
李洱看重时间对人的影响。他会说,人老了之后,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掩饰善与恶,人本性的一面呈现得更为真实。“晚年写作”是少数作家才能达到的状态,在中国则少之又少。中国的小说更多的是青年小说。甚至在篇幅上,中国小说大多时候只能写好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好的情况,又少之又少。年轻一些的时候,李洱觉得年轻人经验不足,放得开,可以更大胆地写一些东西,没那么多顾虑。现在,他会觉得,有感情,有生活,有履历,有知识背景,有稳定的价值观,才能把长篇小说写好。
他欣赏李泽厚那种“晚年写作”风格,这是一种写作状态,不再受情绪左右的写作状态,文章的逻辑,会过滤掉情绪。“他(李泽厚)做到了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先不论其观点如何有争议,至少他的才气、感觉和理性的思考,达到了极致的均衡。”李洱说。
李洱从书架上翻出一本施勒格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给我看。施勒格是德国浪漫派重要的思想家。李洱钟情于这样的分段思考和碎片化写作。李洱的小说本身就是某种碎片化写作的呈现。他的小说里有其他作家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密集的小标题。
李洱喜欢哲学。他的文字里经常闪现对于哲学的理解。他喜欢看那些哲学功底深厚的评论家的文字,比如同济大学的王鸿生。王鸿生看了《应物兄》,改了一个字,即将现象学中的那句“面对事实本身”改为“面向事实本身”。“‘面对’只是面对一个对象,‘面向’是目光看到了现象学背后。”
李洱的手机响了,朋友打电话邀请他去重庆参加一个活动。他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太多。他对此感到头疼,安排不过来。“以前作家写完小说很舒服的,刚刚倾吐完,甚至会享受那种孤独寂寞和欲望满足之后的匮乏感。”
彼时是2019年12月1日的北京,现代文学馆,户外下雪不久,有积雪覆盖。摄影记者在巴金雕像旁的空地上给李洱拍照。他说起了巴金雕像的来由。四下无人,安静清宁,虫子们也都蛰伏了。当我们再次谈起这一天时,一切都已天翻地覆。前些天,李洱跟批评家张清华通电话的时候,张清华说他正在看《鼠疫》,还打趣说,里厄(《鼠疫》里的主人公)是不是可以音译成李洱啊。熟悉加缪的李洱,随即在电话里给张清华背诵起了《鼠疫》的结尾:
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