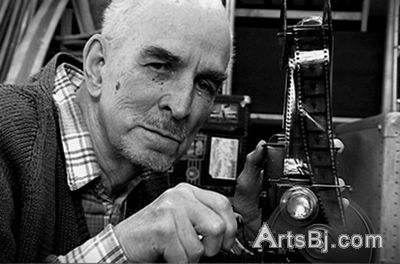
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第一次看伯格曼的电影时就说:“他已经做了我们做梦都想做的事。他写电影,就如同作家写书。不过他用的不是笔,而是摄影机。”
另一位新浪潮电影大师艾力克·侯麦在谈到伯格曼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第七封印》时说:“这是一种在艺术中刻画了时代——这里是中世纪——特征的素朴,这个时代的精神为伯格曼成功地加以把握,没有为卖弄学问所糟蹋,由于他那无可比拟的艺术才华,它才能将那些启发他灵感的圣像画的母题转换为一种电影语言。他向我们呈现的形象与形式从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永远原创的成果。他的艺术是如此天才,如此新颖,以至于我们由于对其中的问题的质疑以及从不间断地寻求答案而忘记了艺术。很少有电影能提出这样高的目标,更少电影能这样完满地实现它的野心。”
波兰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基耶洛夫斯基心目中的电影圣人殿堂是由伯格曼、费里尼与塔尔科夫斯基三位构筑的。他说,他梦想达到的境界是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只有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与费里尼的部分作品已经达到了。而“它(指伯格曼电影的张力),连同其他东西,正是银幕上的魔术诞生的地方:作为观众,你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因为你正处于一个由导演直接呈现给你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如此连贯、如此完备、如此简洁,以至于你被它裹挟而去,感到它的那种张力,因为你意识到了人物之间的紧张。”
“欧洲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之一、有“第七艺术的魔术师”之称的费里尼则说,“这部电影(指《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伯格曼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他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幻觉,这是一种深奥的幻觉主义,它能够以一种欢快的方式呈现问题重重、令人不安的现实。伯格曼与我惺惺相惜。”费里尼心目中的另一位伟大的同行是黑泽明。他曾经邀请伯格曼与黑泽明赴罗马拍摄《三个爱情故事》(每人拍其中一个),终因黑泽明的健康原因而未果。
而伯格曼本人却说:“电影,虽然有着复杂的诞生过程,对我来说只是我对我的同类的说话方式。”同类?——是的,他指的就是我们人类。
人们用尽了赞美之词来描绘伯格曼的形象,但是,我认为最恰当的方式仍然是:看呀!它们就在你眼前;看一看他的电影。如果你认为是好的,继续看下去;如果你没有任何感觉,那就算了——你或者是无可救药的,或者不是我们的同类:也许是超人?
或许最贴切地界定伯格曼的电影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例如,当美国电影评论家萨缪尔斯于1971年9月10日终于获得伯格曼的采访许可时(伯格曼极少接受采访,晚年是例外),他的第一句话是:“伯格曼先生,我想从一个相当概括性的问题开始:如果要我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说明你在电影导演中的卓越地位的话,我会说,那是因为你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从别的艺术门类中那些伟大人物那里已经熟悉了这些事情,可是人们却很少在电影里做到这一点,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你的高度。”
这就是人们对伯格曼的基本评价:他使电影成为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与戏剧并驾齐驱的艺术门类。
如果要用两个关键术语来概括20世纪伟大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传奇一生,那它们一定是“魔灯”与“影像”:它们恰好也是伯格曼的自传与回忆录的标题。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