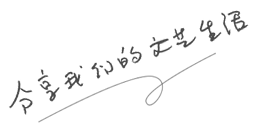作者:Robert C. Morgan 翻译:张岚
金康容先生出生于韩国,是一位在韩国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
作为艺术家,金康容在拥有自己独特视角的同时,在对画面本身的表达上也与韩国的绘画传统保持了一致,自朝鲜时代后期起韩国的绘画史上就一直存在着对于抽象空间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西方世界曾出现过的现实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流派,他更倾向于是一位当代艺术家,就像Seo Bo Park(朴栖甫,韩国当代著名抽象艺术家)和Hyong Keun Yun(尹亨根,韩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一样。
当很多西方的评论家欣然将金康容先生精心雕琢的作品归类于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时,我却觉得作品中天生带有的亚洲文化因素不容忽视。即便如此,我在对这些被金先生称为“现实+图像”的作品阐述时候,也不能说完全不受西方艺术领域的影响。在我研究这些“砖墙”和“立柱”的时候,很明显地,我发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Piero della Francesca(彼埃罗.德拉.夫朗彻斯卡,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和Uccello(保罗乌切洛,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以其艺术透视之开创性闻名)作品处理手法的影子,我陷入了沉思,试图解释这是何以发生的。
换句话说,这些砖块创作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这意图应当是艺术家选定的一个主题,进而来对其进行表达,而在这之前,艺术家本身并不知道作品会以何种形式呈现。金康容先生的作品既是精雕细琢的画面,同时又是对画面延伸出来的空间和想象的阐述。
表面上看,金康容先生是在利用数学的精确手法来描绘他作品中每一块转头的光与影,事实上,完全不是。他将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和数学上的精确手法和笛卡尔哲学融会贯通,形成一种直觉般的基本概念,这概念就是来源于佛教观念中的冥想。
西方绘画史中一直有作画过程中清除心里一切杂念的传统,金先生对此也颇有兴趣,有时候,作画前完全处于没有任何想法的状态,这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绝对的专注。如果在他的作品中你什么也看不到,那就走近一些,看艺术家用笔的技法,这比只看到砖头要好多了。从金先生的视角看,这些作品是关于空间和想象的,所以也可以说,画面是空无一物的。最终,这些空间和想象在画布上被表达成佛教里所说的“四大皆空”的境界或者是驱除一切杂念的“空灵”的观念。对于金先生来说,这就是冥想的意义。这些作品就是这种过程的见证。
在西方,有一种从相反角度看问题的传统,而不是像东方文化那样,看一个问题不同的两面。西方评论者抱着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更倾向于赋予所有文化同样的商业价值意义,当代艺术也难逃脱在层出不穷的国际双年展中踏入全球化的征程。这也促使一部分艺术家试图抓住艺术的捉摸不定,急切地寻求表达。
亚洲国家似乎很受这种潮流的影响,但是艺术岂是轻易用一种形式或一种观念就可以表达清楚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金先生的作品既不是对什么事物的简单完全的呈现也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应该是在两者之间。这之间的空间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认为“有即无,无即有”,即虚空反而就等于世间万物得以循环不息的无限能量。
一句话,我相信这些作品是非凡的。我相信它们在以特殊的方式考验我们的感知能力并鼓励我们将绘画看作是一种视觉的认知。我喜欢的绘画理念是,艺术家应当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艺术应当是对生活感悟的一种表达。就像象征派诗人马拉美所说,“分享想法是创造,但给想法下定义就是摧毁”。
在这里,我不想在观者还没有看到这些画时就妄下评论,观者自然有自己的看法。马拉美的诗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影响观者有可能产生的任何想法,这比我现在就全盘托出我心里已有的所谓的这些作品的真谛要有意义多了。
我会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他带我进入一个用冥想的方式来表达空间概念的世界。如果17世纪法国Claude Lorain(克罗德洛林,法国17世纪艺术家)的寓言是值得信任的话,那么绘画需要一个想象的窗口。洛林和金先生相似,他们都用一种手段,既没有消除虚空,静寂,也达到了内心追求自然和谐的目的。
最初接触金康荣先生“现实+图像”作品时的情形已不甚清晰,第一次看到画册上那些栩栩如生的砖头令我困惑不已。我看到了什么?成堆的砖头?但这些假象又是如此令人信服。这些绘有普通砖块的难道只是对普通砖块的一个简单呈现?如果不是,那么它们试图表达什么?政治意义?或者是对一种视觉手法的阐述?难道是想唤起人类历史上一种秩序或混乱的意识?还是想呈现战争和自然灾害中产生的建筑的两极或瓦砾?什么是他们真正的意图呢?从金先生的作品中我问自己的问题越多,我越发现了自身的很多问题。而一个真正在艺术评论上有所建树的人,是一个随时可能被绘画里的新的表达和发现唤醒的人。正如当我审视着这些不寻常的,略有些神秘感的作品时,它们开始渗入我的意识,我的现实感,甚至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这一角色。
一开始,我认为我这种自我质疑很正常,合乎常理。我在一种平衡,自身和其他事物之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但结果是度徒劳的,至少结果和我想要的方式不同。这是一些以砖块为主题的创作,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砖块只是一个想象,一个进入另一个世界——绘画世界的想象。
表面上来讲,这些作品中除了光,阴影,和用沙子和粘合剂混合而成布满画面的或散乱或整齐排列的颜料以外,空无一物。金康容先生并不是观察这些转头而作画的。整个的构思都在他的脑中,这画面是他头脑中的眼睛所看到的。他从画布的左上角开始作画,然后扩展到整个画面,然后在右下角结束。实质上这并不是一个作画过程,而是一场触觉的演出。
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摒弃一切杂念,集中想象看到了一面“砖墙”。艺术家在处理每一个笔划的同时都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光线和阴影的缝隙都是基于艺术家通过记忆产生的心理意识。艺术家所创作每一块砖头都是基于他对外部世界观察所得而形成于头脑中的意识。每一个砖块都是意识的产物。每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形状,都来自于再平淡不过的简单调制的颜料和细沙。他创造了一个虚空的空间,一个被称作“砖头”的可见的虚空空间。这不是蓄意而为的,没有事先精确地构算,只是一个砖头堆的大体的概念和无数的组合和顺序排列。 也许你会认为画中的每个栩栩如生砖头形象起了作用,也正是它,促使了这种触觉的飞跃,实现了一种超越了真实的觉察力和存在感。
金先生的绘画不仅仅是一种画法的重现或者从属于某种西方的绘画主义形式(就像教科书里说的)。这些作品几乎完全没有颜色,这样毫无颜色而言的图像就这样出现在了属于它们的准确无误的地方。就像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结构主义思想家)说的那样。换句话说,金先生已经把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实质性的高度。它促使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也许,是用一种东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绘画。在某些方面,这种新态度和东方哲学密切相关,尤其在传统审美观上。金先生的作品所带来的创造性,不仅只是理论,也有很深的理论和实践的根基。
你也许觉得这些作品的感觉和佛教颇有些渊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有些晦涩难懂。但是,如果你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最有他们一定会以自身的具有一种高超的复杂性的形式而脱颖而出。他们和塞尚的静物不同,同样和立体主义或者毕加索或者巴洛克也不同,当然,同1909-1911年间的那些作品更是不同。
有些人或许会更在意技术层面的东西,没错,金先生技法一流,但是在绘画中,技法并不是脱离想法和感觉而单独存在的,所以只在意技法未免有些限制。作为一个韩国艺术家,金先生清楚这些限制,他明白他的作品不仅是一种高超技法的展示,而更是在探索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一些对于现实来说更开放的东西。他探触到了这个无限的世界里的人类精神世界,就像很多杰出的大师所做的那样。金先生把自己特有东方的艺术文化深深渗透入自己的作品,并使它突破进而超越了一切限制。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可触可感性更甚于只被作为遗产来继承和观摩。他在这些人们因为文化而有感而发的创作中被清晰地看到和感觉到。对于金康容先生来说,文化引导着形式,并直接为艺术家的所感所知提供源泉。所以达芬奇的艺术和Hokusai(葛饰北斋,18世纪日本浮世绘艺术家)的不一样,波洛克的和毕加索的也完全不一样。
对于很多人来说,选择砖块作为绘画的主题未免略显单调,简单来说,是这样的。画面的含义看似一目了然。就像立体派艺术家,颜色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表达。作品往往是关于形式,空间,或者说,是关于虚空的表达,并且他们在用一种极其清晰和精确地手法来表达。所以这些作品一书中注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罗伯特.摩根先生是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纽约普瑞特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发表并发表过数篇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同时还是一位策展人,大学讲师。)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