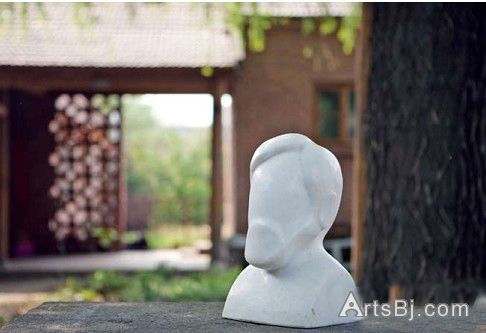
宋庄美术馆此次策画的“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群20周年纪念特展”(以下简称“我们”),用非常自然和本体的方式呈现了宋庄艺术家的面貌。选择“自画像”形式,一是为了更多呈现曾经在宋庄生活过的艺术家的本人形象,二来是希望有机会让大家停一停,观照自己的内心,和自己说说话。“我们”不单纯是一次自画像的展示,它的意义是通过一个个在场的艺术家对自我的陈述和表达,描绘地域的文本,文化的文本,甚至社会的文本。参与此次展览的约有710位艺术家,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牌艺术家,也有我们可能看一眼名字会忘记的艺术家。但是,将展厅里面悬挂的710余幅肖像画全部看完以后,会发现完全忘记艺术家的名字,名字在这个展厅里太不重要了,重要是那一幅幅形态各异的自画像。是一次很难得的完全无功利的、实体性很强的展厅。
宋庄美术馆馆长方蕾在描述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宋庄20年时说:“宋庄的意义从各个角度都被阐释过,在宋庄生活的艺术家有5,000,7,000人,作为个体,他们每一个人完全不同,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都太特别了,我找不到用更好的方式来呈现他们。”方蕾在展览前言写道:“有你们,才会有时间,才会有历史”。展览用展示艺术家自画像的方式,避免掉入可能会带有政治和道德潜在因素的策展方式。方蕾说想用这种方式让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有一个20年的party。但是,在展览筹备过程中的几个细节却十分有意思,一是,展览的通知发布是在2013年年初,到9月份的展览布展,艺术家有6个月的充分准备期,并且对所有的艺术家没有门坎,只要生活在宋庄的即可,宋庄美术馆预计参加的人数是2,000人,但最后呈现的710人左右。二是,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问一位没有参加的艺术家未参展的原因,对方答:我女朋友不让我参加。通过这两个展览策画过程的细节和最后呈现的人数,加上我们之前通过媒体对宋庄的了解以及宋庄整个这20年的变化。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一丝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与刚开始进入宋庄生活的艺术家在心态上完全不同。以“我们”展览为契机以及比较这前后艺术家心态的转变,似乎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近几年艺术家对生存、身分认同以及群体意识的变化。
从艺术家生存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年轻艺术家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和难测,市场就像是他们面对最严酷无情敌人的挑选。艺术家之间的生存竞争也越发激烈且无形,面对这种竞争,年轻艺术家在潜意识中会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并且性价比最高的生活方式来应对这个局面。选择居住和创作在宋庄,可以被看成是一项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相对居住在城里的高成本和激烈竞争,这里有相对可以喘息的机会,不用去过急的面对高生活成本的压力。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从开始画画开始,相对于上一辈艺术家就更有市场意识。但这种市场意识难免会让年轻艺术家迷失一段时间,被过多的功利所缠绕,从参加宋庄美术馆“我们”展览中可以看到,一些年轻艺术家在一开始就会预判这样的展览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回报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参加这个展览实在不是好的选择,或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艺术家的市场意识有些偏颇,但是对展览价值的判断本身就带有的功利色彩,那这种潜移默化的功利意识难道不会被带进具体的创作中吗?相对最早进入宋庄的艺术家,现在宋庄可以说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进入城里(主流)的缓冲地带。方蕾对笔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展览,我收到了很多来自艺术家的回馈,一是,后悔自己没有参加;二是,没有认真对待自己自画像的。其中就有艺术家说,通过这个展览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以及所面对的社会。”通过这个展览,有的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面对700多张有名气的或没名气的艺术家的自画像,在分不清你我的环境下,或许退回到无功利性的创作中才是最有意义,也是自己唯一可以把握的。因为当作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很难说这个作品是功利,或是无功利的。展览将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身份和作品相分离,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可能会少了一次对艺术家社会身分和作品是如何被分离的经验,如此多的自画像同时被放在一起,观众在乎的并非艺术家是谁,而是这一张张画像。这可能是有人后悔没有参加“我们”展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体制的变化,对于当代艺术家身分的认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相对体制内画院画家的身份的实体认证,现在对艺术家身分的认同变成一种社会的默认或是说群体认同。而生活在宋庄的艺术被外界和媒体冠以“宋庄艺术家”,这是一种社会的默认态度。对于这一称呼,似乎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都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可能如上文所说,社会意义上的艺术家身分干扰了你。但有一点,拒绝被定义一直是当代艺术的核心。然而“宋庄艺术家”这一称呼的内在涵义就在社会系统中被统一化了,“宋庄艺术家”这个统一标签不知道什么时候与“农民工”这类的标签有共通之处,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引起了生活在宋庄的一部分艺术家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标签是外界强加的,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总结,背后隐藏着对当代艺术的不理解和不了解,满布着矛与盾的陷阱,他们不属于这类宋庄艺术家的范畴。最早进入宋庄生活的艺术家更愿意以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选择来确认艺术家的身分,确实最早进入宋庄的艺术家选择了与体制内完全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也如最早进入宋庄的批评家栗宪庭所说的那样:“艺术不重要,自由的生活才是重要的事。艺术家把职业化的生活方式作为聚集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作为一个艺术家决定走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道路,尽管这种自由和独立不能保证其艺术品格的自由和独立,但生存方式会给艺术创造带来影响,而且整体的看艺术家的职业化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看,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试验。”与这些勇于开辟道路的艺术家相比,后来进入宋庄的艺术家进入的原因变得相对复杂。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对身分的认同,宋庄生活非常的私密和个人化,做任何事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行为,这有时候,也是很多人诟病这些艺术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这里更容易获得社会对艺术家身分的认可,也更能获得外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理解。生活在这里可以不用去理会别人怪异的目光,不用去面对家人对自己生活的干涉,在对父母如何解释自己在做的事也变得相对容易。得到这种艺术家身分的归属感,在走向理想的道路上更加理直气壮。在宋庄20年的发展,到2005年之后,大量艺术家的进入不光是在单纯的等待机会,更重要的是找到艺术家身分的认同感,这相对于之前的艺术家来说是这不是来宋庄生活和创作的原因。
随着宋庄的艺术家数量增加,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大的群体,分层也更加明显。在宋庄中心广场有座7层塔形的地标雕塑,自上而下的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铁、锡、泥砂,大家戏称它为“土生金”。但其实生活在宋庄的还有一部分原宋庄农民,中国的农村是群体意识特别强的小型社会和经济体,村民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互相关联,也是彼此生活所依存的对象。费孝通所着的《江村经济》一书,细致的分析了中国乡村邻里之间的生活依存关系。而在宋庄,艺术家的到来,完全让拆解了个人对群体的依存关系。早期选择进入宋庄的艺术家有一方面原因是想脱离圆明园画家群体的束缚,圆明园作为一个画家群体的聚居地被外界知道后,艺术家的个人生活不断地被打扰,方力钧等人选择离开改入宋庄就是为了脱离这一群体效应的影响;但事与愿违,没想到宋庄现在成为更大的群体。后来进入宋庄,虽然面对的环境虽然和之前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保留了对群体影响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相对保证自己思考和创作的独立性,这也是艺术家一直在追求的。我们看到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质量就是:保持与群体影响的对立性,这让当代艺术保有批判的特质。但是这种对群体的距离感是否是建立在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群体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呢?是否一直在更新这种认识呢?如果没有,会不会让这点对群体的距离感落入盲目自信而对外界和群体不屑一顾的沼泽中呢?
方蕾在同笔者聊到邀请艺术家参加“我们”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事,既有大牌艺术家不愿意参加的现象,也有刚进入宋庄的年轻艺术家不愿意参加的现象。似乎大家都在规避一种可能会被定义为“群体”概念的可能。尽管“我们”展从开始就在力图规避这种可能,力图以最基本的方式呈现每一个个体的不同,但依然在筹备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误解。方蕾说到:“即使到最后展览只有一个人参加,我也照样展”。多么令人起敬的态度!这种方式会不会引起对个人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认识呢?通过群体来照映一下自己也未尝不是件坏事,未尝不是一种保持群体距离感的方式。这关系到艺术家如何看待自身与群体的关系,简单的对抗或是拒绝或许是一种lower的方式,既使是成功的艺术家有没有胆量将自己与其他艺术家放在一个平台上来比较。栗宪庭说到:“关于艺术的历史,大家通常会说到“大浪淘沙”,这里说的“大浪淘沙”,指的是时间过去了,留下的金子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沙子和金子混杂在一起,被大浪里挟着的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而将来尘埃落定,被大浪淘出来的,肯定不是以往历史中的那些经典和“金子”。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