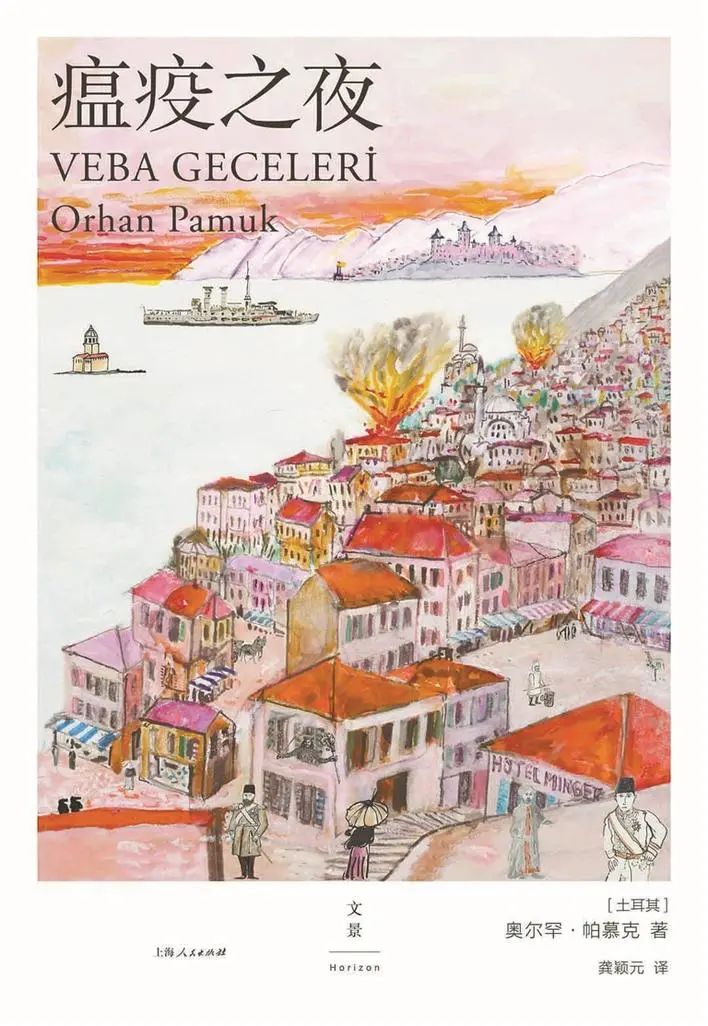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加缪在《鼠疫》的扉页中引用了《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话。穿越几个世纪,这句话犹如箴言或者神谕,用来形容奥尔罕·帕慕克的全新力作《瘟疫之夜》竟然如此恰如其分。
瘟疫主题下的继承者
《瘟疫之夜》是帕慕克酝酿了40年、潜心创作5年、长达40万字的史诗大作。帕慕克写这部小说时,现实世界中还没有发生新冠疫情,如同宿命推动文学家前行,他用自己的笔完成了现实与虚构的交错。通过1901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偏僻行省首府、地中海上一个虚构小岛——明格尔岛的故事,把太阳下的事抖落出来晾晒。各色人物在面对瘟疫和灾难时何以自处?如同正在进行的历史,它拥有深入的指涉和层出不穷的混乱,指向所有集权国家的痼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正填满历史的每一个角落。这部作品记录下整个人类的恐惧、无措、绝望、懦弱、尔虞我诈与英勇、奋不顾身、追求自由以及浪漫。
明格尔岛上的一砖一瓦皆浸透着帕慕克的真挚感情与无与伦比的叙事艺术。鳞次栉比的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建筑、民族混杂交融的集贸市场,威严的总督府大楼、各具特色的教堂与清真寺。虚构的城市通过作者的笔,一砖一瓦地建筑起来,读者身临其境地穿行在明格尔岛的大街小巷。而擅长绘画的帕慕克甚至为架空的岛屿绘制出了详细的地图,展示出他自由穿梭虚构与现实的精妙文笔。如同一幅包罗万象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同时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末期的全景图,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而一场瘟疫打破了这座小岛的宁静。
瘟疫题材所催生的恐惧与绝望历来是文学中最重要的母题。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圣经》,其中包含大量关于瘟疫的描述,例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而作为文艺复兴重要标志的薄伽丘的巨著《十日谈》始于佛罗伦萨的大瘟疫;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是帕慕克公开承认的模仿对象,1655年伦敦大瘟疫被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呈现了威尼斯瘟疫下的爱欲生死;加缪的《鼠疫》则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暴发瘟疫后,人们在荒诞的现实下守望相助彰显人类无私无畏精神的赞歌;黑塞在《纳齐斯与戈德蒙》中通过中世纪瘟疫背景表达禁欲与享乐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的深刻冲突。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中瘟疫都是作为一个背景,却极少透过瘟疫本身的层面,从人们面对瘟疫和灾难时的心理体验、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视角去深入挖掘这一题材自身的丰富性。
作为历史小说的《瘟疫之夜》,是作者最投入最用力最深刻的表达。帕慕克既作为瘟疫主题下那些前辈先贤的继承者,充分汲取这一主题的养料,又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客观地带领读者深入瘟疫下的世间百态:上至苏丹、总督等权贵阶层,中至贵族、富商巨贾和各国领事代办,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面对瘟疫和隔离措施、消杀行动时的切身感受和心理变化;进而引出权力斗争、腐败与贪婪、自私与偏见、勇敢与奉献,更进一步探讨多民族融合的困境、宗教与政治博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现代医学与防疫制度在传统社会如何推行的可能性等包罗万象的视角。确实当得上探索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的赞誉。
作为侦探小说的《瘟疫之夜》,可以看作是帕慕克对自己的继承。我们知道作者此前的作品《黑书》和《我的名字叫红》都是披着一个侦探小说的外壳,进行庞杂又匠心独运的复调叙事。这部小说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作为悬疑推理的部分进一步弱化,犹如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只是作为引子引出小说更深远的戏剧冲突与隐喻一般的讽刺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直处于暗影之后却掌握整个土耳其帝国生杀大权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忠实粉丝,他要求前去主持防疫工作的努里以福尔摩斯式演绎推理法而不是严密的侦查实践去追查邦科夫斯基帕夏及其助手遇害的真相。犹如一个莫大的讽刺,苏丹表面上推崇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作秀式地设立现代防疫机构以及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来断案。而这些行为不过是要给人一种苏丹锐意进取、支持改革的幌子罢了。
作为爱情小说的《瘟疫之夜》,只是整个故事的点缀,却充满了温柔、同理心与卸下面具后的无力与脆弱。本书主要描写了三段爱情故事:来岛上指导抗疫的帕克泽公主与驸马努里;明格尔岛总督萨米与独居寡妇玛丽卡;公主的侍卫青年军官后来成为明格尔岛独立先驱的卡米尔与泽伊内普。帕泽克说:历史故事越浪漫就越失真,而越真实也就越不浪漫了。而他却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三种爱情:长相厮守细水长流的爱情、轰轰烈烈追求自由又逝若流星的爱情、相互取暖寻得片刻欢愉又彼此慰藉的爱情。在死亡与恐惧肆虐的明格尔岛,爱情始终能给人坚持下去的勇气与希望。
突破自我的局外人
《瘟疫之夜》还有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点。譬如对恐惧和无知的探索往往都是一针见血:有些人因为想象力匮乏而并未感到恐惧。在整整二十一年光景里只能靠想象来认知外部世界的公主看来,这些想象力缺失的人几乎没有构想未来的场景并因此感到愉悦或悲伤的能力。瘟疫袭来之后,富人商贾由于在物质和信息上占有天然的优势,纷纷出逃,挤满了能够营运的商船,甚至还发生了被封锁在明格尔岛外国战舰的击沉的悲剧。而岛民没有弃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他们对瘟疫步步逼近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无法设想灾难的场景。而无法想象灾难本身也就导致了灾难的降临,导致历史不可逆转地展开。
岛上复杂的宗教与派系斗争没有给抗疫带来丝毫真正的助益而时常沦为政治博弈的闹剧。帕慕克深刻地指出:与其在慌乱中草率行事,还不如仔细观察周遭的一切,再去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有抵触情绪。而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本地宗教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愚昧与荒诞,一边用迷信的方式消极抗疫,一边通过护身符的幌子大发其财。帕慕克也只得无奈地说:经文纸和护身符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是在困难时期,这些东西可以避免民众陷入信仰危机,甚至还能给他们某种力量。
正如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描写的一样:一旦在街上“自由”了,然后又会怎样呢?害怕和恐慌会和瘟疫本身一样毁灭这个城市。帕慕克在安排了明格尔岛独立之后,防疫的可持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并导致了接踵而至的政治混乱和抢班夺权的闹剧。隔离措施被破坏殆尽,明格尔岛陷入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人们似乎获得了“自由”。最终却在三次政权更迭和付出巨大的新增死亡病例的教训之后,各方才达成共识,同舟共济,逐步扭转局势,遵循科学防疫策略,渐渐走向疫情的终结。
清代大家赵翼在他的《题遗山诗》沉吟: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帕慕克始终以冷静的笔触,深刻的思想,手术刀般精准的切入角度,为我们呈现了1901年的瘟疫之夜下的六个月虚拟与现实交汇的历史。每每让我们脊背发凉又感同身受。在新冠疫情仍然肆虐的当下,尤为难能可贵。
帕慕克曾经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谈到:每个作者写的每一本书,都代表着他自己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人的小说,可以看做他精神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过了就回不去了。一旦小说的弹性终结了,你也就无法再动它了。《瘟疫之夜》既是帕慕克继承自己讲故事的天赋,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构中交织前行;又是作为突破自己创作手法的局外人,把时代精神、文化冲突、恐惧与希望熔于一炉,让我们作为新冠时代的亲历者,紧紧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经脉,摒除偏见,更好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与终将平息的内在与外在的冲突。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