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前的1870年8月27日,黑格尔诞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世期间思想即已经产生巨大影响。恩格斯曾对他不吝赞美,称他为“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跨时代的作用”。(《马恩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72页)
可时至今日,国人谈到黑格尔时,却已经觉得陌生和遥远。但他的思想从未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而依然在现实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成为后起的思想的契机和生成之基。如20世纪30年代科耶夫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精神现象学》的研讨班,以其对黑格尔的欲望、死亡、主奴关系、承认、历史终结等概念的提炼和独特的解读,赋予了那些直接和间接参加他的研讨班的梅洛·庞蒂、巴塔耶、雷蒙·阿隆、拉康、萨特等法国思想家以灵感和生命。而前些年福山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红极一时,其基本观点其实也是科耶夫化的黑格尔的深描和当代回响。

黑格尔
当然,黑格尔对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至为深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影响了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的思想。而百多年来,他的思想同样也直接影响过中国现代学人的思想。如同他的主奴哲学影响过法国的哲人一样,他的这一思想同样也影响过中国的哲人,“新儒家”唐君毅就曾援引他的著名的“主奴关系”,呼吁国人应该具有“主人之认识”,文化的自信,摆脱“奴隶意识”,不必以“他者”对自己的文化艺术的“承认重视”来确定其有无“价值”以及是否“承认重视”。这或许是“文化自信”最早的黑格尔式的理论表述。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更愿意来谈论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不是学术界所重视的《精神现象学》,希望在当下这个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波诡云谲的历史关头,通过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观来理解现实。为了加深这一理解,我想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反合”的形式来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即首先谈论作为“正题”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其次,对可作为其“反题”的巴塔耶的“普遍历史”予以介绍;最后则把当下的中美关系作为“合题”来进行具体化的探讨,从而达到既可理解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又可理解现实的目的。
一、作为“正题”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出来的讲稿,因为是讲课所用,所以言谈生动,没有过多艰涩的概念,加上谈的又多为具体的世界历史事件,给人以深入浅出之感。但是,这本著作并未因平易近人就失去其价值,相反,却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所在和最好的入门书籍。或许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学者最早翻译出版黑格尔这本书的原因。对国人来说,《历史哲学》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就是在这部书里,黑格尔对中国“黑”得最厉害。他不仅认为中国人因为缺乏财产的所有权而自暴自弃,自贬自抑,没有荣誉感,喜欢撒谎,还认为因为中国的统治为家长制,所以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都得听命于皇帝这个“大家长”或“父亲”的决断,皇帝也因此成为国家的“中心”,在宗教、学术、文学上都是“教主”或“至尊”。而受人尊崇的孔子思想也无甚高深之处,其《论语》多为“道德箴言”,不过是在重复一些正确的废话。在科学上也同样流于平凡,中国人因缺乏“主观性”和“内在的独立性”,没有一个“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一切又都以国家的“实用”为标准,所以虽然貌似很尊重科学,却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精神,所有的“民族性”也只是“模仿的技术”而已。但中国人却因此而自大、瞧不起欧洲人等。不过,考虑到黑格尔这些言论都是两百年前的看法,可以不必过苛,但是他还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因为中国很早就开始固定不变,没有进步,却让以五千年文明而骄傲的国人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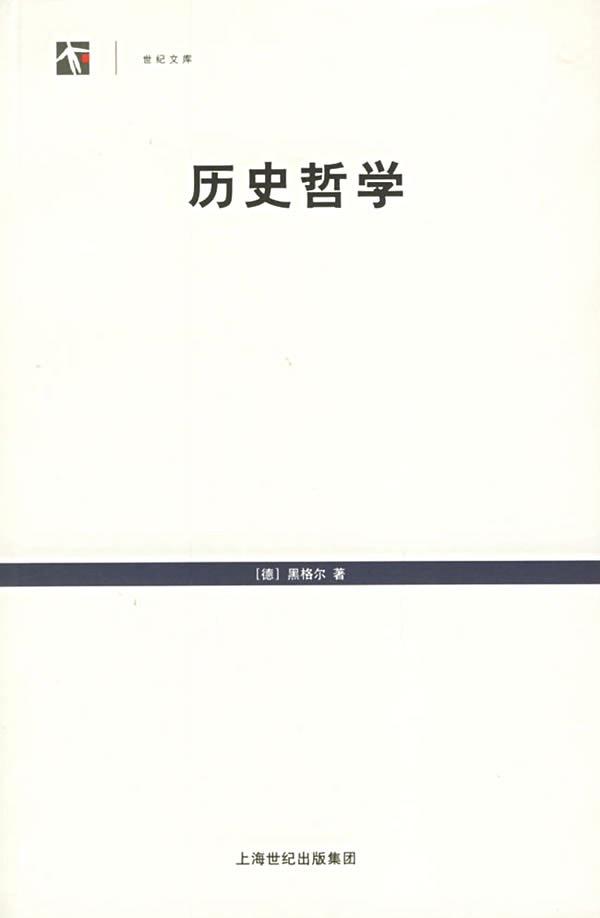
那么,黑格尔为何有这样的看法呢?他所谓的“历史”或“世界历史”到底是什么?
因为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各种事件的编年和累积,而是用“理性”去审视“精神”发生的进程的“哲学的历史”。而所谓“理性”,就是宇宙的“实体”,也就是最高的存在,它既是宇宙展开的动力,也是宇宙发展的内容和目标,因此,既体现在“自然宇宙”的各种现象中,也体现在作为“精神宇宙”的“世界历史”之中。“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页)而这一“合理的过程”或者说符合“理性”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世界精神”展开的“必然的路线”。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或者“世界历史”就是“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也就是“自我意识”,它依靠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但“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有条件的或者“理性的自由”。把《历史哲学》翻译为英文的学者约翰·西布利认为,这种自由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一是从外在的各种人造的社会束缚中解脱出来,只服从自我认可的法则;二是从内在的兽性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自我不再被盲目的欲望所支配。换句话说,历史就是这种“自由”通过世界逐渐展开并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个人也好,民族也好,都是其工具或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真正的自由。
从这个前提出发,黑格尔勾勒了一幅壮丽的由“精神”的开展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画卷。从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东方各国,到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再到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依次递进,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而他的《历史哲学》因此也是人类认识、追求和获得自由的伟大的时空之旅。正是以人们对自由的意识程度为衡量历史发展的线索,黑格尔才认为处于东方的中国只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现在看来,黑格尔当时对中国的批评或许并不为过,因为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嘉庆道光年间,尚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西欧等国已经开始迈上了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之旅,而这种现实的差距对黑格尔当不无启发。
二、作为“反题”的巴塔耶的“普遍历史”
如果说黑格尔描画的世界历史是一场由理性统摄的严肃而坚韧不拔的精神之旅,那么,巴塔耶所构想的“普遍历史”则可称之为由非理性的祭祀、奢华的放纵、盛大的节日等场面连缀而成的五光十色的连环画。而之所以选择巴塔耶的“普遍历史”作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反题”,是因为巴塔耶的“普遍历史”就是受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启发所构建的。

巴塔耶
不过,巴塔耶的“普遍历史”却对黑格尔建构“世界历史”时奉之为圭臬的“理性”嗤之以鼻,他认为理性固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但是理性同时也对人与生俱来的更为根本的动物性予以残酷的控制,使得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且,理性产生于使人脱离动物世界的劳动世界或者实践世界,其本质就是一种算计,所着眼的是未来而不是当下,并且常不惜牺牲现在的需要以满足未来的需要。为此,理性刻意压制了人们的非理性的动物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诗意、笑、醉、狂欢、奇迹等的追寻,而巴塔耶认为这正是黑格尔的哲学所缺失的部分。所以,他不仅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理性的发现作为历史前进的方向,相反,他把人对理性的反抗作为历史展开的动力。
当然,对理性的批判只是巴塔耶的“普遍历史”的一个内在的线索,他的“普遍历史”实际上具体建立在其“普遍经济学”之上。犹如黑格尔将理性称之为宇宙的“实体”,巴塔耶在《被诅咒的部分》一书中所提出的“普遍经济学”同样以宇宙为尺度,不同的是,他是以其间循环往复的“能量”为“实体”,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来说,这种“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太阳,而太阳带给我们的能量总是超过生存的需要,但这多余的能量我们却并不能保存,最终都将流失或丧失。这个原理对于每个社会系统来说也是一样的,每个系统都会产生除维持自身运行之外的多余的能量,而且不管是否心甘情愿,也必须将过剩的能量及时予以消耗,否则过剩的能量将会导致社会系统因超负荷而崩溃。据此,巴塔耶以社会对于过剩能量的使用方式为准,把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社会形态区分为耗尽社会、企业社会、工业社会等类型。在他看来,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是耗尽社会,前者如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等,通过献祭和夸富宴把过剩的能量消耗殆尽,后者如中世纪的欧洲,通过教会庞大的神职人员的供养和国王及贵族的奢靡的生活消耗了过剩的能量;当时的中国同样如此,其过剩的能量主要通过大量的人口和庞大的政府官员予以消耗,也即把过剩能量用于非生产性的活动之中。而企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则是积蓄社会,也即将过剩的能量予以积蓄用以军事的扩张或者工业的扩大,后者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但巴塔耶也提醒,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是为了应付工业社会的到来所采取的积蓄形式。而这就是巴塔耶所建立的“普遍历史”。
巴塔耶虽然没有把理性供在普遍历史的神龛之上,但他同样强调人对自由的追求和享有,他把黑格尔的没有奴性的“主人”转化为像国王一样拥有自主权和尊严的“至尊”,而人生存的本质就在于对于这种“至尊性”的不懈的追求,哪怕只拥有一时片刻,也在所不惜。巴塔耶认为,至尊性的获得就在于对于过剩的物质财富的无偿的不求回报的花费。所以,小到饭后的一支香烟或者疲惫时的一杯啤酒,大到从金字塔的修建,纪念碑的竖立,大型竞赛的举办,乃至战争的发动,均可归人此种追求至尊性的活动之列。而人也好,国家也好,就在此种消耗行为中获得至尊性,赢得荣誉与高格的享受。
三、作为“合题”的美国与中国的“和解”
但巴塔耶以诗意的非理性对黑格尔的散文式的理性的批评虽然有其道理,但却不能完全抹杀理性在人类历史展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此他自己也承认,人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而由人作为材料,手段和终极目的历史当然也同样如此。所以,无论是黑格尔在“世界历史”中对理性的高扬,对精神及自由的鼓吹,还是巴塔耶在“普遍历史”中对人的非理性的消耗行为的赞扬,都是“合理的”。
或许以“史”为鉴,则可以换个角度审视当下的现实,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纷争。如果以巴塔耶的眼光看的话,现今的中国就是个耗尽社会,因为多年的生产导致的能量过剩,使得中国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采取非生产性的活动来消耗过剩的能量,这其中既有各种大型的基建工程,从高速公路到高铁,载人航天,奥运会,高端的国际会议,富丽堂皇的庆典,以及“一带一路”等,都是其“表现”。而当下的美国却是个斤斤计较的积蓄社会,力图采用各种手段积蓄能量,并努力将其过剩能量投入生产领域,以加强其生产能力和能量。而如今的中美冲突,也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冲突。但是,这只是近年来的情况,巴塔耶曾经指出,二战后的美国之所以对战后的欧洲重建实施“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各国,其真实原因也即在于美国的能量高度过剩,不得不及时“放电”以避免系统超负荷而崩溃。与之相对,当时的苏联却是个积蓄社会,因为要应对工业社会对能量的巨大需求,所以不得不把所有过剩的能量投入到生产中去。而中国为了建成工业社会,之前也是个积蓄社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后,才终于变成了耗尽社会。美国却又逐渐再次转变为积蓄社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景。
黑格尔曾讲过悲剧的“和解”问题,那就是悲剧的各方所代表的都具有“实体性”,或者真理性,但都是片面的真理,各方因各持己见势必发生冲突,而在冲突中终于认识到各自的“合理性”,最后达成“和解”。这种“和解”当然不可避免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各方并不认为自己会损失,或者说,各方并不把自己的损失当回事,也许,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历史的教训就是没有教训
黑格尔有句话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什么教训也没学到。他的这句话常被用来对于人们不吸收历史教训的批评,但其实这么理解和使用偏离了黑格尔的原意,黑格尔并非要批评这种现象,而是认为,历史是“灰色”的,而“现在”却是“生动和自由”的,不可能用历史的规则去套今天的现实:
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历史哲学》第6页)
今天也同样如此。而黑格尔还曾讲过,世界历史的英雄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亚历山大也好,拿破仑也好,虽然戎马一生,但对自己的真正的使命却并不知晓,他们只是“绝对精神”的工具而已。也许,今天的世界历史英雄和他们并无区别。
所以,我们谈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也好,谈到巴塔耶的普遍历史也好,都只是“过去的”历史,而将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他对于理性的强调,对于自由的向往,却可以在今天给我们提供可能的参照。而让人唏嘘的是,黑格尔于1831年死于一场霍乱。这在新冠依然肆虐世界的今天,似乎给人更多的感慨,甚至有同病相怜之感。最后,让我再征引黑格尔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历史哲学》,第10页)
2020年8月26日匆草于五角场。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