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作为系统论的代表,他将社会及其不同分支领域视为纯粹由交流构成的诸社会系统,主张一种激进建构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激情的爱情》是他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卢曼的社会理论整体框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从学术生涯伊始,卢曼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了“爱情”为授课主题。
卢曼认为,西方的爱情语义学自16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形式变化,反映了造成人格性亲密性日益增长的社会分化。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过去的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间接地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本文节选自该书译者范劲的译序,归纳了什么是卢曼心目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爱情秩序。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什么是卢曼心目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爱情秩序呢?卢曼的整体思路可总结如下:
1.以性的共生机制为物质基础,将当事人诱入罟中,欲罢不能。性的标志最容易将人格和社会情境区分开来,有助于在公共场合中发现人格性爱慕的苗头,因此能代替风雅承担爱情的启动功能。身体关系是最好的简化机制,它能比友谊更有效地将伴侣双方和周围环境隔绝,换言之,将他们隔离在大多数复杂性之外。在当代的爱情关系中,性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需要更有力的化简工具。但在另一方面,由性展开的人类关系的亲密内容恣肆繁杂,必须将其纳入亲密交流模式中,否则会造成持久的干扰、不堪承受的负担。爱情也体现为性的理想化和系统化。
2.以爱情为引导性“意义”(Sinn)。卢曼的“意义”系指超出当前意义的“指引盈余”(Verweisungsüberschuss) ,同理,爱情作为“意义”的特点是在系统关联中建构,同时却又超越此系统关联。意义不是某个高悬的理念,卢曼所讲的意义和世界、视域同义,这个世界视域随着建构行为本身而增长,同时包含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已有的和未来的视域。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曼的爱情包含了理想化和悖论化两个动机。爱情随时超出自身,这是理想性的一面;而恋人必须将自我建构的世界视为真实,又是悖论性的一面。
3.现代爱情以偶然的启动机制取代理性考虑和风雅技术的启动机制。偶然被植入符码之中,象征选择的自由,机会的无限敞开,提高了恋爱的成功机率。主动引入不确定性,是为了对冲爱情交流的不确定性,而无前提的偶然开端,更提升了爱情作为“无中生有”的交流成就的人生价值。
友谊中的委身他人是为了自我的双重化,而自由爱情只跟个体人格相关,在委身他人的同时仍保持自我同一。但是爱情中的个体人格同样是偶然的,绝非某种固定的质性(如果是这样,爱情就可以通过“道听途说”实现,而无需见面)。实际上,恋爱者的人格是在交互作用中建构的。有交互作用在,就有作为依托的人格在,人格(悖论性地)既是建构的根据又是建构的产物——“人际间互渗入恰恰意味着,另一方作为恋爱者自身体验和行动的视域,使恋爱者作为我而在,离开了爱情这一我在(Ichsein)就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是在偶然相遇中成就了两个偶然的人格,恋爱在事情维度上就是两个偶在的悖论,悖论成为“事情本身”,需要在交流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展开自身。
4.行动和体验的悖论性共在场(Kopr?senz)是爱情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行动和体验分属于不同的交流系统,一种属于社会系统,以实在情境为导向,一种属于心理系统,以想象中的实在、以对于(对方)想象中的实在的想象为导向。当行动和体验同时出现在一个事件中时,共识性整合是不可能的,偏偏爱情就是要实现这一不可能的整合。二人交互作用的核心就是行动和体验的同时发生:他者被爱的体验,引发了自我的爱的行动。如果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体验为观察和行动的理由,而不分辨后者的想法是否荒唐或自私,人们就知道他陷入了爱河。简单地说,A将B体验为被爱者,将自己体验为恋爱者或行动者。A对B的体验必须直接引发A作为恋爱者的行动,否则就无法将自身体验为恋爱者。如果B现在体验到A爱自己,而且将此体验也作为自身的行动来体验,则B也是一个恋爱者。
5.爱情的另一基本问题是在瞬间中安排永久。瞬间和永久共在场,意味着不同时性(过去、现在、未来)的同时化。永久不仅是幻象,更是爱情的形式,凡真爱都是永久的,真的恋人都会使用永久这一形式——不过必须在“瞬间”的媒介中。因此瞬间和永久的矛盾在交流中不成为问题,对交流不构成障碍,反而造成了交流的有效性,这就是爱情系统中媒介/形式的交替形式。真爱情永远是瞬间,永远是永久。一切的关键只是,交流本身要继续下去,拖延下去。人们只能用时间来实现永久的形式,在时间中思念永久,保存瞬间。
系统论道出一个公开秘密,交流需要时间,以便和交流相连接——“需要时间来进行下一步操作,以便能呆在被标记一边,或跨越构建形式的界限”。意义由时间而实现,证明“互渗”和“永久”两个虚构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虚构。但这不是对时间的简单消耗,恰相反,交流即时间,恋人以无休止的谈话、口角、戏语制造了“自己的”时间。理解了这一整体思路,如何将悖论去悖论化,让处于双重偶在中的恋人的处境可以忍受,答案就清楚了——那只能是时间,而非任何一种超越横向(体验和行动)和纵向(瞬间和永久)悖论性共在场的先验层次(理想)。服从符码的理想,做伟大的恋人,只意味着将悖论无限推延,爱对方意味着永远愿意再忍受片刻的不可忍受,和对方一道制造同时又忍受悖论。因果性归因的难题不可能由一个过程之外的抽象理念,而只能由时间这个最具体又最抽象的理念来解决,换言之,爱情的困难只能由爱情本身的延续,由继续使用爱情这一媒介来克服。中国“难得糊涂”的古老人生智慧,在这里得到了精确的理性化表述。难得糊涂不仅包含了忍受悖论、不放弃悖论的悲剧精神,还表现了中国人享受悖论的乐天性格。
6.这后两个问题的中心化造成了卢曼所提倡的“问题导向”,从理想到悖论到问题的符码转换,就是让爱情作为自由秩序的本性越来越清楚地呈现,爱情最终显示为依仗性的引诱、爱情的引导而实现的自我秩序建构。问题导向就是学习导向,每一次亲密性忍受都是一次学习——学习如何更好地忍受!问题是向着未来的,即不是向着过去的理想,而是向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敞开——爱情真正的魅惑在于,它能敞开世界的未知空间。很少有人想到,没有悖论逼迫,我们又怎么会暂时放弃自身,片刻地走出一己的逼窄世界。真正爱过的人,才知道忍耐中暗含的学习机会。
耐心而坚韧的“敷衍”,是爱情语义学发展的顶峰阶段(尽管卢曼不愿这样来表述),即问题化的阶段。问题导向即操作导向,操作中才有系统存在。这种操作绝不简单,其中包含着一种无法实现而只能无限接近的理想性,即理解性地体验,按理解性体验去行动。
卢曼把交流过程分为三个选择行动:一是信息的选择;二是传达的选择;三是接受或理解的选择。信息和传达的实现者是“他者”(Alter),理解的实现者是“自我”(Ego),但理解并非理解所传达的内容为何,而是理解到有信息传达给我,但同时也理解到,这个传达来的信息和传达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区别的,即是说,理解了选择一和选择二之间的区别,因此接受者的选择内在地包含了前两个由“他者”做出的选择,它是三个交流行动的综合,将三个行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操作”(Operation),因此接受者才是自我,是第一位的,而信息的采集者和传达者是他者,是第二位的,这和通常的交流理论和日常经验正相反。这等于说,怀疑才是交流的基础,你在接受的同时在怀疑,同时还知道对方知道你在怀疑,因为怀疑将交流推进、维持下去,交流成功的标志就是不确定性的维持。这种关系的极致就是爱情的亲密关系。爱情“不可交流性”和信息选择与传达选择的区分无法实现有关,因为在爱情场合,“假如信息过热,传达也不可能冷静”,换言之,信息和传达都不是根据社会通行的选择标准,而是服务于恋人的勾心斗角、交替测试,以至于堵塞了交流。
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更需要理解的努力:理解对方的体验和行动与其环境的关系,理解信息加工的特殊方式,并进而理解自我描述的弦外之音。他者的理解负有一项艰难任务,即让自我忘掉作为芸芸众生的客观事实,在二人世界内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个体性就体现在系统/环境、信息/非信息、自我描述/实际情形等多重差异上,而个体性也让多重差异变得可以容忍。凭这些差异,恋人从芸芸众生中自由地选择了对方,凭这些差异,恋人能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唯一选择,而且因为尘寰中只有自己能做出这一“绝对”正确的偶然选择,这个选择也就证明了、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换言之,彼此帮助对方从匿名建构的世界脱颖而出并获得个体尊严,就是现代爱情的神奇功效。不仅如此,在对方中承认不可化简的多重差异,接纳对方体现的多重差异,就相当于用对方的眼睛(差异标准)在看世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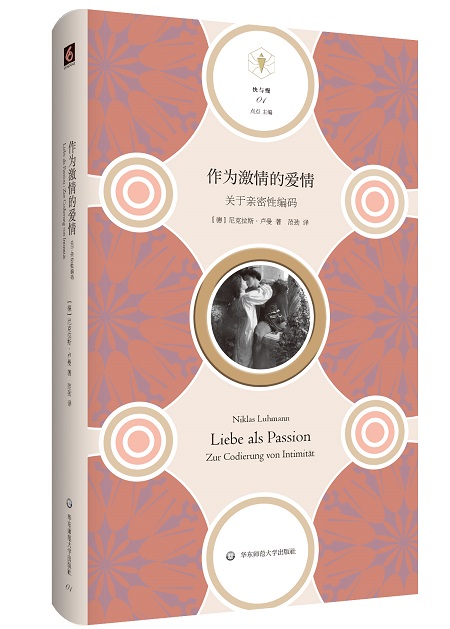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德] 尼克拉斯·卢曼著,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