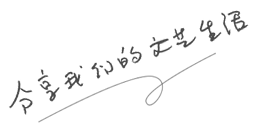越剧《织造府》,李晓旭分饰剧中的贾宝玉(左)和曹雪芹(右)
南京市越剧团创排的越剧《织造府》作为“金陵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较之前两部——《乌衣巷》和《凤凰台》,更具“新质”特征。在厚重的历史底色上,以不拘之态作诗韵皴染,成为该剧主创的品质追求;而与当代审美对位的舞台呈现,则是观众乐于接受这一“诗化演绎”的重要缘由。
全剧开端立于一个巧妙的构想:曹雪芹写下《红楼梦》前八十回,“偏是后四十回,增删十载,呕心沥血,不能定稿”。于是,他重返金陵,在小厮帮助下再进“织造府”。面对曾经盛树繁花的老宅,“这是织造府,还是大观园?是少时旧梦,还是笔底春秋?”曹雪芹的踌躇迷茫作为一个重大戏剧悬念,引发观众强烈的观演兴趣,也为剧作家的感性创造提供了一条通达的路径——曹雪芹在离开旧宅二十年后,为续写《红楼梦》而来,为安顿书中儿女而来,在昔日府邸,他将看到什么?想起什么?怎样直面似梦似幻虚实交叠的境遇?怎样决断内心的彷徨?这些悬念大有文章可做,而这一切在剧作家罗周看来,既是当代人对“曹雪芹笔下为何只有八十回”这一历史悬疑的回应,又足以为这部作品插上想象的翅膀。
戏剧结构规整是越剧《织造府》的一个重要特点。罗周写昆剧大体遵照“四折一楔子”的体例,而越剧不拘泥于此,“多场次”通常是传统越剧的结构模式,越剧观众对这种“重场戏”与“过场戏”合理交错的方式十分习惯。在编织这部着意于诗性表达的作品时,剧作家以第一场“入书”和第六场“出梦”作了结构上的“首尾呼应”,中间四个场次分别以春、夏、秋、冬命名,从整体布局看,既不失越剧艺术特点,写意、诗化的追求也得到了妥帖的归置。
作为整部剧的主叙事单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肉头戏”,春、夏、秋、冬四个场次分别对应一位主要人物。笔者以为,这一设置至少在两方面体现出剧作家的成熟思考和编剧技巧:其一,人物色彩与四季所提供的情绪色彩有相当的匹配度,尤其对于中国观众,这种文化符号深入人心,是直观的,有直接的渗透作用,不需过多解释就有一种天然感染力,而人与自然的勾连,本身就带有十分鲜明的诗意特征。其二,对这样一部线索庞杂、人物众多的戏剧,以四季转换来解决情节大幅度跳跃的问题,不失为高明机巧之举。它所采取的叙事方式不是铺展式的,而是高位聚焦:焦点从无情的四季流逝,直接对应人物命运的变幻无常。其间,无须过渡,没有裂痕,观众也不会感到情节跳跃、行为突兀。四季流转,悬空笔墨,每一单元都是一个人物的独立素描,情感底色则是极富隐喻的四季景象。剧作家做到了这一点,并凭借这一点挥洒出磅礴诗意。
我们似乎看到,在每一场次,抑或独立单元,剧作家都有意识地布设一个戏剧转折,相对完整地完成对相应人物的工笔描画,哪怕这一“完整”带有剧作家自身的诠释,但心理逻辑、行为逻辑整体上是可见、完整的。反观传统戏曲,通常是按照起、承、转、合来设计场次,单个场次不承担人物心理逻辑的完整性。从这一点看,脱胎于《红楼梦》的《织造府》的现代性就相当明显了。有关“行游书中”“穿过翰墨去见你”等主观设想、美好诗境,寄托于此,得到了比较切实的逻辑支撑。
如第三场“夏·品茗”是曹雪芹与宝钗、妙玉对话,核心是曹雪芹的“三问”。薛宝钗在回答“三问”时,把“清雅志不俗”“不信金玉良缘结夫妇”的心理表现得颇为真实,虽不同于传统认知中藏愚守拙、听任命运摆布的“宝丫头”,但谁又能说这个“人间清醒”的薛宝钗不是真实的人物?末了一句“啜苦咽甘,当真好茶”,不失为剧作家在人物素描上的点睛一笔。又如第四场“秋·夜宴”,从“击鼓传花”到曹雪芹脱口而出的“佳期不再”,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戏剧转折——从钟鸣鼎食之家肉眼可见的铺张繁盛,到清朗秋月被命途阴云笼罩……这一切发生在极为紧凑的时空里,准确说,发生在曹雪芹与贾母的对话间,从舞台的“满”到舞台的“空”,剧作家把中国传统诗歌中“乐景写哀”的手法运用得既得心应手又不露痕迹。
把“春”“冬”两个场次留给心有所托的曹雪芹和林黛玉,可见“宝黛关系”在剧作家心中的重要位置。而这一点显然没有偏离传统的“红楼故事”,反映出在叙述“不一样的红楼故事”时,剧作家对“度”的考量与拿捏得当。在“春·葬花”一场中,曹雪芹问林黛玉有没有读过《红楼梦》?二人纠结于《葬花吟》“究竟是出自我笔下,还是你随口占偈”这一类细节,很好表现了“贾宝玉的形、曹雪芹的魂”这样一个虚虚实实的设置。应该说,剧作家这种对审美原理的超越与改造非常睿智,也非常有趣,让人们对一部熟读的《红楼梦》产生了不一样的阅读兴味。遗憾的是,这一强调艺术虚构的巧妙设计,在其他场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没有让它成为这部剧独有的风格贯穿始终。
“绛珠还尽眼泪,归返上界”堪为剧中最依循诗韵表达的一笔。在“冬·泪尽”一场,我们清晰看到了剧作家十分严苛的审美追求:水一地,月一轮,宝、黛荡舟湖上,互诉“前世缘、今生续;今世缘,来生续”,深情而浪漫。偏这一刻,岸上隐约传来嘈杂的“抄没”之声,让人顿悟,眼前的一切无非是镜花水月。笔者以为,这样一种艺术处理,是当今舞台艺术的一种全要素呈现——对文学意蕴作出诗化演绎的同时,并没有淡薄厚重历史背景的交代。情起情灭、兴败缘由,哪些需要重墨渲染,哪些则简笔勾勒,剧作家笔下取舍有度、恰到好处。如上文所述,该剧每场都设有一个转折,此时的戏剧性转圜出现在林黛玉化身为一株绛珠草,消失在一派镜花水月中,似乎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作品一改原著中林黛玉悲悲戚戚、清清冷冷的结局,无论从理性层面还是感性层面,观众都能接受。黛玉留下一句“情之所至,便是永聚”则似有意针对开篇时曹雪芹的一番困顿,以解扣方式回应了“聚易写,散难写”的文人心结。也许,这就是曹雪芹内心的顿悟与重回“织造府”的全部所得。一部充分诗化的戏剧演绎到这一步,其多义性自然生成,我们亦可以把它看作是当代剧作家,站在今天戏剧舞台上的一次独立发声——
戏剧舞台上的曹雪芹望着魂牵梦萦、始终不能释怀的“众姐妹”隐入茫茫白雪,有如众仙归位,喊出了积郁已久的心声:不删了,不改了,不写了,《红楼梦》八十回够了,足够了……全剧以此收煞,笔者想,其创作目的已基本实现,剧作的现代性也随之凸显。
越剧《织造府》的诗化演绎和全要素呈现,在其他艺术环节也同样表现得十分出色。导演翁国生在积累了大量舞台实践后,对如何拓宽戏曲美学边界有了更深的认识。他通过多个维度让我们看到其导演手法之老到、戏剧语言之严谨、舞台构图之精美、视觉形象之丰富所达到的新的境界。《织造府》是戏曲的,更是越剧的,同时也兼容了大歌剧、音乐剧,乃至中国舞剧的审美元素。最重要的是,导演风格与剧作家的诗性追求形成了深度衔接,在艺术感觉上取得了高度一致。作为主演,曹雪芹的扮演者李晓旭实现了越剧小生行当的突破性创造。这个角色是有难度的——人物状态不断切换,又不能像《乌衣巷》《凤凰台》那样更多借助戏曲程式化表演,完全要靠走心、入神、深度刻画来完成角色任务。李晓旭的角色完成度非常高,她把曹雪芹的深沉、贾宝玉的清朗演绎得十分到位。尤其她的“毕派”唱腔,顿挫音之饱满、下滑腔之丝滑,在多层次塑造人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剧声腔的丰富多元、流派传承创新的艺术魅力,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原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处调研员)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