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保罗·奥斯特近期推出了大部头小说《4321》。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弗格森展开的四条平行的人生,四个弗格森在不同的城镇长大,有着不一样的知识激情、感情生活和社交圈,他们如影子般彼此映照,相互阐释,也走向不同的人生境遇。
据说,同为劳模作家的村上春树在纽约布鲁克林见到奥斯特后,曾说过“能见识保罗·奥斯特,是我此生的荣幸。”
如同许多精力无限的创作者一样,保罗·奥斯特有许多“分身”:作家,诗人,编剧,翻译,电影导演……并且每个领域都作出了成绩。这倒是暗合了奥斯特的小说风格:没有确定性的世界,换一个名字就可能延伸出不同的人生。
奥斯特的青年时代并不顺遂。与许多初入文坛的年轻人一样,他经历了无数次退稿,生活困顿,怀疑自己根本不是写作的材料。他的早年经历,在中文出版时以《穷途,墨路》为书名,很好地概括了奥斯特早年间的心路历程。
如今的奥斯特已经功成名就。不过,某些时刻,他或许也会想到:如果他真的具有非凡的棒球才华(奥斯特的学生时代曾为此疯狂),如果当初的他放弃了写作,如果他依然痴迷诗歌……那自己现在的人生将会是怎样?只是人生没有如果,无论一个人会经历怎样莫测的命运,他的人生是无法走回头路的。我们只能为此感到深深的困惑与震撼。
奥斯特从未停止对于人生的反思。在64岁时,他出版了随笔《冬日笔记》。冬天,是适合思索与回忆往事的季节。我们所经历的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已经成长,但仍时刻充满彷徨、困惑与无助。许多事情只有经过时间的磨砺,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意义。正如他在这本书中所写:“多年以后,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思想随笔是灵魂的直接碰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斯特在以佩索阿式的笔锋进行时间的反刍,记录内心醒悟的瞬间。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总是迷失,总是朝错误的方向出击,总是原地转圈。你一生都苦于无法在空间里找到自身的位置,即使在纽约,最容易穿行的城市,你成人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城市度过,你也经常遇上麻烦。无论何时你乘地铁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假定你登上了正确的列车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布鲁克林方向而去),一旦爬上楼梯到了街上,你就会特意停下一会儿搞清楚周围方向,但你仍然会南辕北辙,东西不分,甚至当你试图战胜自己,明白你的缺陷会让你走向错误的方向因此去纠正错误时,你还是会做你试图去做的事的反面。该向右的时候往左,该向左的时候往右,你依旧会发现正朝错误的方向移动,不管你已做了多少调整。
忘了在林中独自跋涉吧。几分钟内你就绝望地迷了路,而即使在室内,只要你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建筑中,你就会走错走廊或乘错电梯,更不用说更小的封闭空间,像餐厅,因为你只要在有超过一个就餐区的餐厅上厕所,你就会在返回途中不可避免地转错弯,最终要花好几分钟才会找到你的桌子。
大部分其他人,包括你的妻子,有她总是正确的内在的指南针,似乎总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四方。她们知道身处何方、曾在那里以及要去哪里,但你一无所知,你永远会在这一刻迷失,在吞噬你的每个连续瞬间的空无之处,不明白真正的北方在哪儿,因为对你而言四极并不存在,从来不曾存在。至今为止这还是个小缺点,谈不上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那并不意味着不会有那么一天,你意外跌下悬崖边缘。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你的身体在小房间和大房间里,你的身体在上楼和下楼,你的身体在池、湖、河、海中游泳,你的身体在泥泞地里曳行,你的身体躺在空旷牧场高高的草丛间,你的身体走在城市街道,你的身体费力地爬上小丘和大山,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舒展在沙滩上,骑行在乡村路上,走过森林、荒原和沙漠,奔跑在煤渣跑道上,在硬木地板上跳上跳下,站着淋雨,踏进温暖的浴缸,坐在马桶上,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待,乘电梯上上下下,在汽车和巴士座位上扭动,不撑伞在暴雨里步行,坐在课堂里,浏览书店和唱片店(安息吧),坐在礼堂、电影院、音乐厅里,在学校体育馆与女孩跳舞,在河里划独木舟,在湖里划船,在厨房桌前吃饭,在餐室桌前吃饭,在餐馆吃饭,在百货商店、家电卖场、家具店、鞋店、五金店、杂货店、服装店购物,站着等待领取护照和驾驶执照,背靠椅子、腿搁桌上、在笔记本上写字,在打字机前弓着背,不戴帽子在暴雨里走,进入教堂和犹太教堂,在卧室、宾馆房间、更衣室里穿衣脱衣,站在自动扶梯上,躺在医院病床上,坐在医生检查台上,坐在理发师和牙医的椅子上,在草地上翻跟头,在草地上倒立,跳进游泳池里,在博物馆里漫步,在操场上运球、投篮,在公园里打棒球和橄榄球,感受走在木头地板、水泥地板、瓷砖和石地板上的不同感觉,脚才在沙、土、草上的不同感觉,但最主要的是在人行道上的感觉,因为每当你停下来思考你是谁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个在行走的人,一个终其一生走在城市街道上的人。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你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以为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以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的人,而随后,一件接着一件,它们都开始在你身上发生,与发生在其他每个人身上一样。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无可争辩的是你不再年轻。一个月后的今天,你将满六十四岁,尽管那不算太老,不是那种人们会视作耄耋之年的岁数,但你仍然忍不住想起那些没能活到你这个年纪的人。这便是一例或可永不发生、但实际上已发生的事。
上周暴风雪时扑面而来的风。冷得刺骨,而你在外面空荡荡的街上,讶异于自己竟在这样猛烈的风暴里出门,然而,就当你努力保持着平衡时,有那种风带来的狂喜,有看见熟悉的街道变成一片模糊的纷飞白雪的喜悦。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你看不见你自己。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是因为有镜子和照片。但在广袤的世界里,当你行走于人类同伴之间,无论是朋友、陌生人还是最亲密的爱人,你自己的脸对你来说是隐形的。你可以看见自己的其他部分,臂和腿,手和脚,肩膀和躯干,但只能看见前面的,后面的都看不见,除非你把大腿弯成合适的角度,才能看见腿的反面,但看不见你的脸,永远看不见你的脸,而最终——至少对别人而言——你的脸决定了你是谁,是你身份最根本的事实。护照里没有手和脚的照片。
甚至你,如今已在你的身体里住了六十四年的人,都很可能无法从一张单独的脚的照片里识别出自己的脚,更何况耳朵或手肘,或某一只眼的特写照片。在整体的背景下你才觉得一切很熟悉,但一样一样分别拍摄时,则完全是匿名的。
对我们而言我们都是异国人,假如我们对于自己是谁有什么意识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们活在他人的眼中。想想十四岁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吧,在夏天快结束的两周里,你在泽西城为父亲工作,你加入了一个小团队,修理和维护他和他的兄弟们拥有并管理的公寓大楼:粉刷墙壁及天花板,修缮屋顶,把钉子敲进方寸之间,掀起破损的地毡。和你工作的两个人是黑人,每间公寓的每个房客都是黑人,这个街区的每个人都是黑人,而在连续两周只看见黑人面孔之后,你开始忘记自己的脸是不是黑的。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脸,你在周围人们的脸上看见你自己,而渐渐地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你根本就不再想到你自己。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为了做你做的事,你需要行走。行走带给你词语,使你在脑海里写下这些词语时听见它们的节奏。一只脚向前,随后另一只脚向前,心脏的两次鼓声。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臂,两条腿,两只脚。此,然后彼。彼,然后此。写作从身体开始,是身体的音乐,而就算词语有涵义,有时可以有涵义,涵义也是从词语的音乐开始的。你坐在书桌前,为了写下这些词,但在脑海里你仍然在行走,始终在行走,你听见的是心的节奏,心的跳动。曼德尔施塔姆:“不知道但丁写《神曲》时穿破了多少双鞋。”写作,作为简单的舞蹈形式。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你的生命已经归还给你,你的心脏复原了正常跳动,而最好的消息,是你懂得了死亡不再是你会害怕的东西,人之将死时,他的存在会变成另一区的的意识,而他有能力接受。或者说你是这样想的。五年之后,当你的恐慌症第一次发作时,那种突然的、野兽般的发作撕裂你的身体,令你倒在地上,你却一点都不平静,不接受。那时你也想你快要死了,但这一次你恐惧地嚎叫,比你生命力任何一次都害怕。其他区域的意识原来不过如此,于是你静静地离开了泪谷。你躺在地板上嚎叫,撕心裂肺地嚎叫,因为死亡在你的身体里但你不想死。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多年以后,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害怕——但你害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害怕。离家的前景使你陷入一种极端压抑的焦虑之中。想到要与女朋友分手无疑比你想象的更令人难过。你希望一个人去巴黎,但一部分的你害怕这样的剧变,于是胃部紊乱开始把你撕成两半。你总是这样。无论何时来到岔路口,身体就会崩溃,不管是单核细胞增多症,胃炎还是恐慌症,你的身体总会承担你的恐惧以及内心斗争的主要影响,承受那些大脑不能或者无法抵抗的打击。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荒诞的死,无意义的死,五年前你的头撞地时朝左偏上几英寸也你也可能这样死去,而当你想到人生告终使这些荒诞的死法——跌倒在楼梯梯级上,从梯子上滑下,意外溺水,被车撞倒,被流弹击中,因为收音机掉进浴缸而触电——你只能总结道,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留下一些死里逃生的印记,每个成功活到你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已经避过了不少潜在的荒诞而无意义的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你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过程里。更不用说,无数其他人曾面对更糟的情形,不曾拥有过日常生活的奢侈,比如战斗中的军人,战争中死去的平民,被独裁政府谋杀的受害者,以及无数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洪水、地震、台风、瘟疫。但即使是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人,相比我们这些没有遭受类似恐惧的人,也一点没少受日常生活变化的影响。
舞者们与编者们轮流,运动中的身体之后跟着词语,美之后跟着无意义的噪音,快乐之后跟着厌倦,而在某刻,某样东西开始在你内心打开,你发现自己正越过世界与词语间的罅隙,越过将人类生活与理解或表达人类生活真相的能力割裂开的峡谷,而至今仍令你不解的缘由,突然穿越空旷无限的空气令你充满了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而到了演出结束的时候,你不再才思枯竭,不再为过去一年里一直怀疑所累。

Mike Diblicek唯美黑白风光摄影
你也想算算去往这些地方旅行途中的小时数(也就是说,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但你不知道如何开始,你已经没法算清在美国有过多少次旅行,记不清你有多频繁离开美国,去往国外,因此你永远无法算出一个确凿、甚或大约的数字来告诉你生命中有几千个小时是在两地之间度过的,从这儿到那儿再返回,那些你花在乘坐飞机、巴士、火车及汽车上的大量时间,努力克服时差影响所挥霍的事件,在机场等待登机的无聊,站在行李转盘边等待箱包从坡道滚落时那要命的沉闷感,但对你来说没什么比乘飞机本身更令人不安了。
每次步入机舱便会将你吞噬的不知身在何处的奇怪感觉,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穿越现实的非现实感,离开地面如此之高,你开始失去自身的现实感,就好像你自身存在的事实正缓缓从你身体里流出,但这是你为离家所付的代价,而只要你继续旅行,再加的这儿和某处的那儿之间的无名之地将继续成为你所生活过的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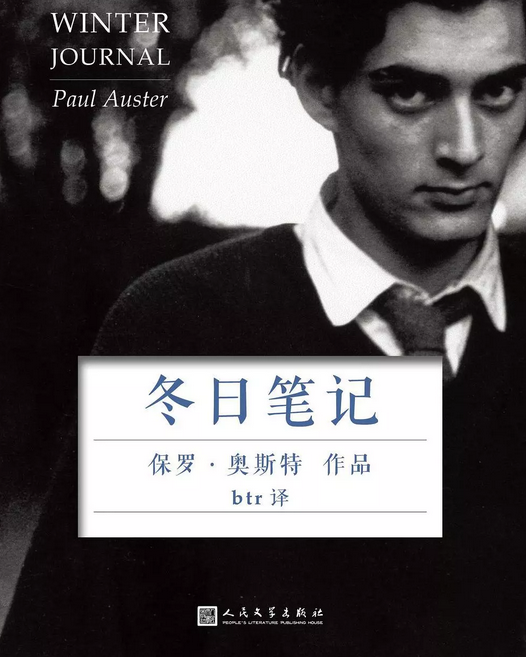
摘自《冬日笔记》,[美] 保罗·奥斯特 著,btr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