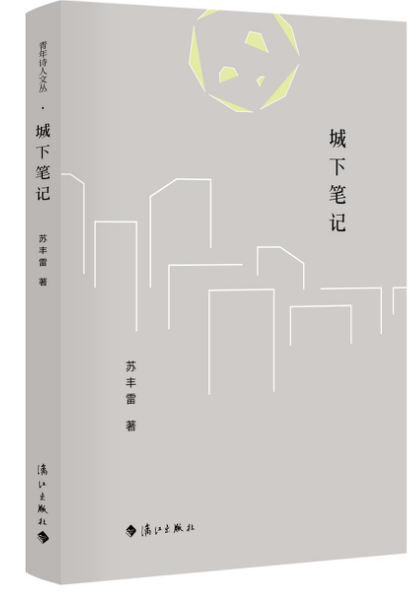
书名:城下笔记
作者:苏丰雷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ISBN:978-7-5407-8511-6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包装:精装 页数:232
开本:32开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
作者真诚记录了大学毕业后十年间的经历、观察和省思。这批随笔,或记叙“趣事”,或主题思考,或对生命难言之痛的幽黯表达,皆是作者沉浸生活的即时性书写。作者直面日常生活,念念不忘将反思和审美注入日常生活,使自我更加健康、美善。

【作者简介】
苏丰雷,青年诗人,1984年生于安徽青阳,原名苏琦。2014年与友人共同发起“北京青年诗会”。2015年入选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曾出版诗集《深夜的回信》。现居北京。
【推荐语】
苏丰雷的《城下笔记》,可以说是诗人十余年来的社会学观察日记,一部带着个体体温的诗性社会学散文。苏丰雷散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以诗人的敏感,在粗砺、残酷的都市日常生存中,酿造和保守甘辛自知的灵魂汁液,而且,他非常关注他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到来与远去,生息与光影,以及他们的灵魂状况的变化,呼应着严酷底层生存中,孤单社会个体的主体间性的呼吸与奥援,疏离与重建……因此而超越了那些一般意义下的散文体敷衍与写作。——回地(诗人、译者)
诗人苏丰雷的随笔集《城下笔记》记录了他十年间的生活日常与所思所感。“城下”,连同书中《山上笔记》的“山上”,显示了他观察、思考和书写时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位刚刚步入社会的当代青年的“惶然录”。他所历经的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文化出现大变化的时期,有时他被迎面遭遇的逼仄和匆促挤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还能像卡夫卡所说的那样,“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的命运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下”零星浮现在脑海里的困惑与期冀。他沉入喧嚣的人群中,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了对这个时代的见证。——张桃洲(文学批评家)
这部笔记有着像书的封面一样流动的暖灰色文字,舒缓的忧郁中又透出些许的明亮,细碎的小事里夹杂着自语的唠叨。城下,自然有小人物的一层意思,有街巷从内心伸出体外的际遇、情绪,以及怪兽般高楼大厦折回心中的滋味和叹息。小人物褒义自己的尊严、理想、道德,用微弱的个体散射光和热。当然,褒义的还有行住吃睡间的烦恼、惶恐、迷茫和愤怒,还有爱。小人物记下这些就自足了,大事物乃至大词大话在这里都是不兼容的。这是一种相对于深沉深厚的“虚薄”,虚薄到透明,去了拿捏,素面众生,自己也自然地写出了自己。——卢文悦(剧作家、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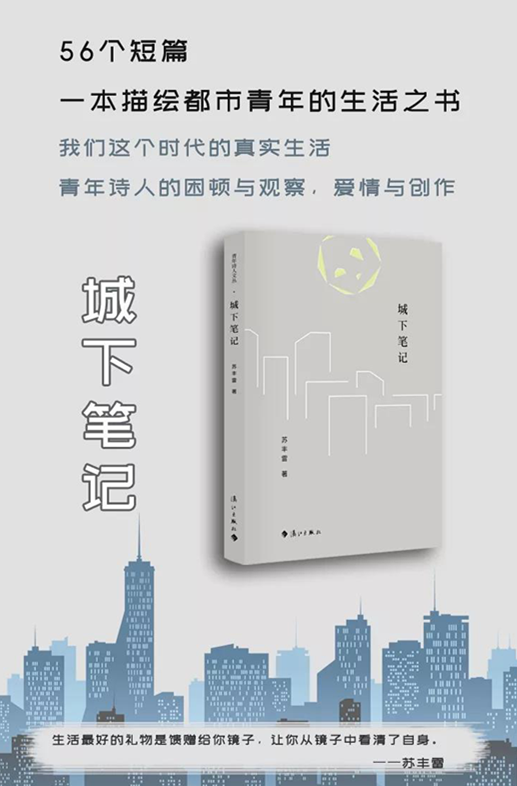
【选读】
无所适从
昨天是星期六。整天的活动结束之后,与同事一起整理活动未用上的物资,并统计入库,这样,这次活动的成本就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来了……忙到差不多晚上九点多。我们一起走向地铁,进地铁后,我们就分手了,不同的方向,他们向东,我向北。当我一个人在地铁里时,一阵悲伤袭来。我打量周围的陌生人,他们与我隔着比太平洋还宽的距离。年轻的情侣也引得我想到我过于长久的孤单。然而我又害怕这孤独中包含的唯我独尊的自由会遗失掉。我既渴望又恐惧爱情。我感到无所适从,双手握住地铁里的横杆,颇显出不耐烦。一个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向外看,这就是收获——无所适从……
车厢深处,一个年轻男子的歌声飘来,伴着吉它的弹奏。一个青年歌手。他在那边弹唱。深情款款。他的行为宣告着,他愿意为了艺术而选择哪怕最底层的生活。他抓住了艺术的本质。即便如此,混迹于地铁,他依然在锻造艺术。他为地铁里的人歌唱,唱他们的心之声,他并没有糟蹋艺术。他现在在我附近歌唱。现在,我可以一边集中注意力听,一边扭过头打量这个年轻人。他很专业。他专注地唱着。我不如他,我的生活方式不如他的生活方式彻底,我在妥协,而他在决绝。我始终无法以我渴望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他已经统一。我始终身心两分,像拙劣的演员一样,我从最远的地方往回走,我甚至有些迷路了,我因到达不了我渴望的地方而焦头烂额,而他在那儿闭着眼睛走进了自我之中。他沉思周在,培育一种观照,而我看到他而感到一种不能抵达的悲伤。我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将十元以下的零钱全部给了他。有不少,我也没数。他专注于他的这首歌,声线美妙,他用歌唱的时长,即多唱了一首歌来表达对我给他小费的感谢——这是他表示感谢的方式。结束之时,他低声说了句谢谢。他的艺术在被检验,而那些小费就是一种检测的尺度。在巨大的虚无中,他收获几缕回声,那就不是绝对的虚无了。所有的歌只为知音而唱。“我只要一个读者,好跟他聊聊!/我只要一个大夫,在悲惨的楼梯上和他对话!”曼德尔施塔姆如是悲诉。我并不在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兑成弓与箭。
2012.5.13
出于人道
百无聊赖地行驶在回住所的路上,骑着我那辆廉价的自行车。每个工作日,我将自行车停在办公楼下,那儿只有两辆自行车,除了我的,另有一辆一直被锁在栅栏上,已经锈迹斑斑。将自行车从轿车的缝隙中推出,然后,习以为常地驾驭着它向某个点靠近。习以为常了这种生活,是无能为力突破,还是内心对于自我的坚定使然?
夜幕降临了。北京的下午六点左右。我向D村驶去。那儿,是贫穷之人的生活场。那儿,人流如织,但蒙尘如土拨鼠。我在人丛中穿梭。现在为时略早,下班的人流似乎还没到达这儿,那股潮水所形成的最大浪还得待会儿才能到达。我似乎除了骑车之外,还在用百分之二十的心思琢磨着某件事。正在这当儿,一个小孩,大概六七岁,像小时候在故乡山冈上遇到的兔子一样闪电般穿过路,窜到路另一边的“灌木丛”(此时此地,在路另一边停泊着一辆辆轿车、面包车)中去了。我本能地刹住车,正是这本能的刹车让我没有撞上小孩。他侥幸稍稍从我的前轮前“逃”走了(虽然他根本没有要逃的意思)。我不由得破口大骂了一句。当这骂声本能地从我的生命急冲而出时,我发现骂人并非一定出于恶意。但我的骂声最该听到的人没有听到。那小孩根本没注意到刚才的危险。他在急速穿过马路时,根本忘记了他是在穿过一条时间之流,在这时间之流中,裹挟着丰盛的物质,也许是一辆质量较大的轿车、面包车,也许是一辆有时候冒冒失失的、横冲直撞的小三轮车,也许是一辆滚动于忧伤之中的自行车。他穿过去了,只是侥幸如剑快速地从水中划过, 并让自己没沾上滴水。这是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傻小子, 这是个还处在童年的神话保护中的小孩。他还在自我的“钟罩”中。
我驶过去了,驶出二十米,又折返回来寻找那个小孩。是他。而不是他。是他。是那个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围绕着一辆面包车疯跑,在玩逮人的游戏。那边还有一个小女孩, 站着一动不动。她注意到了我。我转而叫住那年纪大一点的男孩。想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让他转告那个小孩,因为他是这几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但是,他也闪得很快,我不知道他听清我的话没有。那个小孩后来看了我一眼,是个相貌平常的男孩子。他仿佛明白了一点什么。我转而询问旁边一位做生意的妇女,问是否是她的小孩,她说不是。我请她转告那孩子的父母,让他们教育小孩子多注意安全。她则回复说,没用,那小孩太疯,根本管不住,没用。那妇女声音洪亮。我继续骑往住处。
出于人道。首先是如此。必得如此,才能安心。而有用与无用是之后的问题。像我这种人,有时候,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无限悔恨,但通常不会临机应变。这是我的性子决定的。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不能立即投入对某事的深入思考,而是在稍后。我总是迟缓于刚刚发生的事。我的沉思, 能够漫长而悠久,但我却不会临机应变。我是一个回忆者, 做不来在法庭上应变如流的律师。就刚才来说,在男孩望我的瞬间,我应该叫住他,跟他和气地说几句话,让孩子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其中的危险,但我没有。我迟钝地离开了。祝那个小孩迟早懂得一些道理,一生平安。
我多么擅于悔恨,而又多么匮乏于及时行动。记得多年前一个夜晚,我从车站走往住处。那时我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两个外国女人行走在路另一边的灰暗街道上。那还是未改造之前的街道,路是极端崎岖不平的。夜色很浓, 两个外国女人结伴不知去往何处。她们一前一后地走着。突然前面一个女人被什么绊倒,身体几乎以九十度直接跌倒于地。而我愣了一下,怔怔地望着她们。过了一会儿,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语言的障碍?),我竟自顾自往前走了。事后, 我越来越埋怨自己……
语言怎么能是障碍呢?现在我知道:只要过去,就是一种语言。出于人道,这已经够了。她或许摔破了哪儿,或许需要一个医生呢。我擅于悔恨,不擅于及时的行动。我像一驾笨重的老车,想在发生了什么事儿的地方停下来,但迟缓地忘记了刹车。当我越走越远,悔恨也越发丰盛,然而我忘记了走回去。我应该像今天一样回去。像今天一样回去,就是战胜自我,就是一种胜利。走回去,出于人道!
2012.3.8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