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上起,按顺时针方向)蕾切尔·库什纳、艾斯·伊度格扬、罗宾·罗伯森、黛西·约翰逊、理查德·鲍尔斯,和安娜·伯恩斯
艾斯·伊度格扬:
“我关注那些从残酷的环境中意外脱身的人,我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深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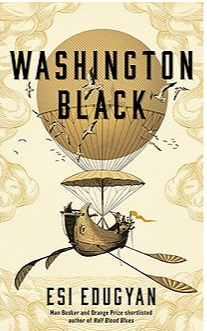
《华盛顿·布莱克》
我这本书的主人公名叫华盛顿,他是一名十一二岁、从事农耕劳作的黑奴。华盛顿生活在巴巴多斯的一个种植园,住在初到此地的克里斯托弗·怀尔德(别名蒂奇)的农舍里,后者是种植园主的兄弟。周围的一切让华盛顿胆战心惊,每一次跟白人交流都可能使自己遭到残酷的折磨,他确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在这里。但新来的蒂奇是一位为人体面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即要求废除奴隶制且参与废奴运动的人)。蒂奇的到来使华盛顿从辛苦的劳作中获得了喘息,他由此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够把才华奉献给世界。
“提斯伯恩继承人悬案(Tichborne Claimant)”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来源之一。十年前,我读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本书,里面对这个案子略有提及。当时,我以为那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都是他编造的。数年后,我才惊讶地在伦敦肖像美术馆看到了当年卷入此事的所有人的肖像画,这些画有血有肉,那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提斯伯恩继承人悬案”曾在英格兰的维多利亚时代闹得满城风雨,激化了工人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是贵族罗杰·提斯伯恩(Roger Tichborne),25岁时他遭遇海难,大家都认为他已不幸去世。他的母亲提斯伯恩夫人找人占卜儿子的下落,得到的答案是罗杰在世界的另一端换了个新名字生活。她在许多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几年后,她联系上了一个自称是她儿子的澳大利亚人。她对他几乎深信不疑,但还是打算找个自小就认识罗杰的人来做最后的验证。正巧,她的一位老仆人安德鲁·博格(Andrew Bogle)退休后在澳大利亚养老,他表示,若继承人的身份遭到怀疑,闹上法庭,自己愿意为被告方做主要证人。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博格(Bogle)”一词的意思是“幻影”。这正好对应着安德鲁·博格其人,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如幽灵般模糊不清。关于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奴隶身份,出生在白金汉和钱多斯公爵的属地——牙买加圣安德鲁斯的希望种植园里。后来,爱德华·提斯伯恩爵士(Sir Edward Tichborne)来此地短暂逗留,处理差事,离开时不知何故把博格一起带走了。从那以后,博格的相关资料便少之又少:他以爱德华爵士贴身男仆的身份走遍了欧洲;他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娶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扬(Elizabeth Young)的英国女人,并在她去世后再婚了;他遗产的数目完全由他与提斯伯恩家族的纠葛所决定。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存在感,人们对他的内心世界也一无所知。
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刚开始写《华盛顿·布莱克》(Washington Black)时,我本打算以博格的视角重现这个案件。但故事很快跑偏,从提斯伯恩身上延伸得太远,以至于在最后成书中,读者只能从一些微小的细节看出我当初创作背景的蛛丝马迹:罗杰的家庭背景和昵称,以及博格的成长故事。与扑朔迷离的庭审相比,我对博格的内心世界和立场态度更感兴趣,他从残酷的环境中被“解救”出来,去往了彻底颠覆自己先前认知的地方,这样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纷繁复杂、跌宕起伏呢?
蒂奇这个角色也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开明自由、品行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却在最后不假思索地背叛了那些他曾终其一生为之努力的理想。这看起来像是由这个充斥着不平等现象和残忍行径的严酷社会造成的悲伤结局。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美好的举动都始于黑暗。
这本小说的主题非常丰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对自由的探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组成的;以我们的能力,能够为自己和他人谋求到多少的自由;自由价值几何。华盛顿对自由最早的理解来自他的第一个保护人和朋友——大齐特(Big Kit),她教导华盛顿,对奴隶来说,只有死去才能自由。她在计划泡汤后又把自由的定义改得柔和了些:自由,她说,就是具备选择不去工作、选择保持沉默以及最重要的、选择不被他人所束缚的能力。华盛顿后来挣扎着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他在探索世界和寻找理想时,心中一直坚守着这个对自由的定义。虽然身躯没有被束缚,但自由却仍然难以把握。自由意志、人格尊严,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人们渴望得到这些,就像渴望得到爱一样,但许多时候,它们与爱一样来之不易。
蕾切尔·库什纳:
“想要创作艺术品,必须拥有承担真正风险的决心。艺术品本身必须比它的创作者更有灵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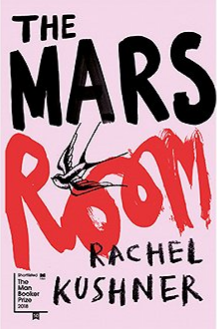
《火星房间》
当我刚开始写作《火星房间》(The Mars Room)时,我在下面这句话里玩起了双关:“我带了一把鲁格尔手枪(Luger)去彼得·路格牛排餐厅(Peter Luger)。”
这是之前我听有人被问到以下问题时给出的一个答案:“你为什么被捕?”
路格是布鲁克林的高端老字号品牌餐厅,而鲁格尔则是一种手枪,它们恰好都叫“luger”。我为什么喜欢这句台词呢?因为它很有意思。悲哀的是,这是典型的美式幽默,尽管鲁格尔手枪产自德国。我曾目睹他人被戴上手铐、被抓现行、被定罪判刑,以及被押入警车、看守所和监狱,这句话正来自这些场景。人们在这些情景下总喜欢说些大话。对于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来说,取材于真正事件的内容,总归比小说作者自己凭空编造的东西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和理解。那些人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下需要吹吹牛皮。他们那些夸张的言谈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信,我有一个朋友称之为“艺术加工过的真相”。他们之所以撒谎,是为了让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可相当不好惹。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就算在双手抱头趴在地上、被警察踩着脖子的时候,也要拼着命辱骂对方几句。他一点也不在乎。如若想在这种场景下取胜,那你就得先做好输得一败涂地的准备。这位仁兄曾经越过狱,后来准军事特警队出动,他才在我另一个朋友的屋顶上被围捕。这些忍者神龟般的超级特警高声让他束手就擒,他们全部把枪瞄准了他,随时准备行动。我的这位朋友自然又进了监狱。后来,他死在了狱中。但在那一刻,在屋顶上面对这么多人时,他只是吸了一口烟,说:“老天,你们电视剧看多了吧。”
但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它们只是我的创作背景。我借用了当事人的说话风格和人设来为我的书进行艺术渲染。我把小说写得幽默风趣,否则我便无法使它读起来真实可信。我不需要那个“luger”的双关语笑话来为我的写作增色,但我笔下的角色、全书的秘密核心人物科南(Conan)会在意图为自己脱罪时说出这样的台词。
我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来掩藏现实世界中那些肮脏和美丽的秘密。书写完后,尽管我认为自己成功地在其中加入了幽默元素,却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已久,如今已迫在眉睫——这本小说没涉及什么争议话题,没有太多讨论度,里面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而且这本书也不该在娱乐类别上架。我希望这本小说能成为一份艺术品。它并不具备别的作用,它不能抚慰读者心灵,让读者义愤填膺,或是助读者“获取知识”。艺术要神秘得多。康德曾发表过“(美学判断)具有目的性而无目的”这样的观点,尼采曾说要“超越善与恶,宝贝儿”——当然,人家原话里没说宝贝儿。而我要说:人们在创作艺术品必须出于纯粹的创作目的,并且拥有承担真正风险的决心。艺术品本身必须比它的创作者更有灵气。我在创作完成后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书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远胜于我:很多人承认,那些被判刑入监的人是因为他们打出生起就运气不佳,而命运的不公就在于,坏运气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个人的人格,销蚀他的朝气。这并不难理解。
但很少人愿意去看这个话题的反面,即幸运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幸运。人们都喜欢把自己归到优秀的一类去,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优秀视作顺理成章,不愿承认那是运气的功劳。但这不过是错觉。在这个阶级分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的人生走向大多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你并不优秀,你只是幸运罢了。这并不代表你是失败的,只是你的人生很可能会因为一念之差走上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个恼人的事实可能是你读完我的书之后得到的感受,虽然我并没有刻意让我的书产生这样的效果,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理查德·鲍尔斯:
“我的小说很快便创作完成,仿佛故事的碎片就摆在我的面前,我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拼成完整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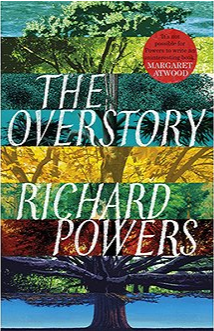
《上层》
我是硅谷心脏——斯坦福大学的一名英语系教授。这个地方车水马龙,钞票满天飞,这里汇集了谷歌、苹果、英特尔、惠普、eBay、脸书、网飞、特斯拉等涵盖各个领域、能带来世界性的改变的大公司总部。硅谷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科幻小说里最完美的乌托邦。
硅谷西边坐落着圣塔科鲁兹山,人们砍下山上的茂密红杉用来建设旧金山。每当对未来的预估让我透不过气时,我便会上山,把自己掩藏在残存的美利坚过往气息里。
我漫步在圣塔科鲁兹山上新长成的红杉树林里,陶醉在这看似与世隔绝之圣地的清幽风景和清新空气中,恍惚间忘却了自己面前这些庞然大物以树的年纪计算其实还只能算是小孩子。有一天,我偶遇了一棵真正古老的参天大树,不知为何它在悠长的历史中竟从未被砍伐。当时我的感觉,就像看到了一群海豚中有一头美丽的蓝鲸与它们并肩而游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棵树比房子宽,若是横倒下来比足球场更长,至于年纪,大概跟基督教的历史差不多长吧。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片森林被砍伐之前是怎样一幅光景。这个巨大的天然资本贮藏库——开启新生命和无尽多样性的引擎——为了建设旧金山,还有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就这么被破坏了。尽管森林的一部分如今又开始变得繁茂,但那些曾经雄伟得多、丰富得多、纷繁得多的东西已经永久地失去了。
道别那棵长寿树回到硅谷后,我的人生有了很大改变。我开始痴迷于阅读与树和森林有关的所有我能得到的资料。我惊讶地发现,曾有四片繁茂的原始森林覆盖着美国的土地,但在欧洲人踏上这片大陆之后,约98%的树木惨遭砍伐。我还在书中读到,历史悠久的加州红杉树,以及美国国内少得可怜的老森林里的百年老树依然在经历被砍伐的命运,目的是建设所谓更加美好的明天。这部可悲可叹、几乎无人问津的大戏已经演到了最后一幕,而我却从未看到任何文学作品对此事表现出应有的重视。我至今已创作了11本小说,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地球上的三万亿棵树,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们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的小说很快便创作完成,仿佛故事的碎片就摆在我的面前,我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拼成完整的图案。书里的人类角色基本都是我的熟人和我在书中读到的人的混合体:在故事中,九个主要角色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树木从无意识状态中唤醒,或者为它们植入了自我意识。后来,他们都卷入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战争,人类反抗着命定的结局,却错误地认为这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下。当你开始仔细观察树木时,你会发现它们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生物,他们的行动纷繁复杂,且都有内在的含义。近日,一项历经数十年的研究发现,树木实际上经常进行社交活动,它们会通过空气以及底下的真菌网络进行交流。我们人类其实也是这些社交网络的一部分,我们与它们相互改变着对方,同时我们又深深依赖着它们。可以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树木的应允才得以实现的。
我在《上层》(The Overstory)中的目标是把树木当成人类来对待,相较于那些主角是人类自己的故事,这本小说追溯了更为久远的过去,故事的格局也更大。我们人类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我们自己足够有趣、至关重要,值得得到所有的关注,我们把其他生物都视为附带资源,等着我们来支配。而事实的真相是,所有生物的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是时候好好了解我们的邻居,回到现实了。
安娜·伯恩斯:
“我无法在我的作品中刻意要求什么。除了我的角色以外,我对接下来的文字走向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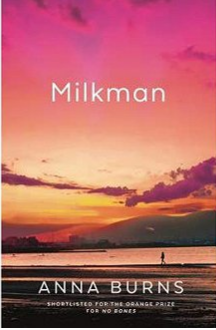
《送奶工》
最近有人对我说:“我不想问你你的书里写了些什么,我只希望你告诉我,你想让你的书做什么。”他在这句话的末尾稍稍加重了语气,而我心里在想,我才刚刚在派对上认识这个人,他倒还真能问。我答道:“我不想再讨论我的书了。我已经讲得太多了。我的大脑现在需要拉上帘子休息一下。”我说的是实话,但同时也在暗示他,“请别再问了,我需要休息,停下。”
过了一会儿,等到没有人掐着秒表让我争分夺秒地回答问题,也没有人打算把我的答案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时,我对他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这问题看似怪异,出人意料。要知道,先前人们问的、以及我估计人们会问的关于《送奶工》(Milkman)问题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没有给角色起个名字?”“为什么每一页都是大段大段的话?”“书里写的真的是你吗?”“你已经搬到了英格兰,为何还要写爱尔兰的故事?”“说到你书里出现的这种语言……”我想清楚了——现在封闭我大脑的帘子已经拉开——那个男人实际上是在问我:“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写这本书的?”对此我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我之所以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它想要被写出来。
我这么回答并不是在回避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送奶工》的雏形始于我的一点小心思,但这些心思在我尝试动笔后便迅速泡汤了,我本打算把手头在创作的一本小说的几百字赘余内容添上几笔,看能不能把它们化成一篇短篇小说。最后那短篇小说自然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我的新作品《送奶工》。我的重点是,我无法在我的作品中刻意去设计或者要求什么,我对接下来的文字走向一无所知。
当然,除了角色以外。我的角色通常都会自己来到我的面前,在极少的情况下,当我实在走投无路、贪心不足、想要掌控一切、担惊受怕、时间紧迫以及想炫耀卖弄的时候,我才会忽视他们的意愿,按自己想的来写。他们不喜欢我这么做,我也不怪他们。再说,他们要是想到自己出场只是为了听从我的指示行动,大概也会感到震惊和好笑的。我笔下的角色会告诉我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希望我怎么做。他们允许我踊跃猜测他们的意图,他们人好,并不介意这一点。他们让我保有这份幻想,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对我的大胆猜测表示不满,也不会嘲笑我、阻拦我,或是对我的安全感缺失综合征步步紧逼。但是,他们同时也对我丝毫不在意。
当写作接近尾声时,我再一次意识到,我那些帮助推动情节发展的精妙猜测和富有见地的假设全都被我的角色无视了。在我创作期间,他们会允许我留下各种各样的文字,但当一本书写到结局时,他们便会把那些不合意的片段统统删除,那些部分会被扔进垃圾桶。有时候,我在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会发现,他们冲出了我的电脑,在我的客厅里把我最新塞进书里的精巧想法和珍贵内容消灭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是冷酷无情的,他们杀死了我的宝贵文字,然后耸耸肩,让我快快翻篇。如果你身处我的位置,你需要拥有强健的体格,以及极高的宽容度,以便在跟这些家伙一起工作时能够理性对待自己的欲望与忧虑。
罗宾·罗伯森:
“我只能把这个洛杉矶丢失的心脏的地理状况,通过无数照片和数百部电影重新拼凑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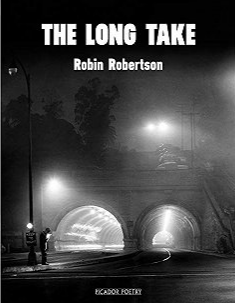
《长镜头》
我曾经出版过九本书,包括五本诗集和一本诗歌选集,此后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创作的十字路口。在扩写了一份历史编年册、开创了苏格兰民间叙事体后,我决定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我的才华: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描写抒情诗小天地之外的其他对象。我几乎一直生活在伦敦,但从未写过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记得当初刚从苏格兰东北部的小城镇搬到伦敦时,我感觉自己就像这个大都市的局外人,现在我想重新唤醒这段记忆,追溯当时的感受。当时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非常两极化:它是逃亡的最佳目的地——在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你可以隐姓埋名,同时拥有无限机遇;但它同时也伤痕累累——在这里,你会时常感觉超负荷、面临贫穷问题,同时,这座城市环境脏乱、犯罪丛生。
我看过很多反映社会黑暗的电影。这类气质独特的电影把背景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伦敦再合适不过了:我的迷惘、我的欲望和我的忧虑都留在了这里。尽管我与本地人来自同一片大陆,说着相同的语言,但此刻我却是一位异乡人。这些电影的许多主创都是与周围环境相当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包括流亡异国、从纳粹德国逃到好莱坞的导演和电影摄影师。他们的电影风格鲜明,视角独特,拥有清晰的社会政治起源,他们的电影可以贴上这样的标签——我的书中有个角色对其做出了同样的评价——“德国表现主义与美国梦的碰撞”。
当我确定我的新作品将以城市为主题时,我内心已经知道它们必须得是美国的城市,也知道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应该设定在二战后的十年间,那正是这个国家的关键时期。大萧条重创了美国梦,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被迫加入二战,这使得美国梦又遭到狠狠一击。战后的美国伤痕累累,暴露无遗,共产主义和核威胁闹得国内人心惶惶,而政府的腐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社会和种族分化则让人感到迷惘。这个国家曾经对“来自各地的芸芸众生”报以同情,他们参与建设了这个国家,而现在,这个国家却开始对这些“局外人”流露出畏惧和怀疑。二战结束时,美国已建国170周年,它早已走上了下坡路。从此刻开始——通过我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叙事线接下来将会这么走:未来60年内,这个国家将会经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最后——现任总统的就职。
在二战后十年的时代背景下,我设置了一个名叫沃克(Walker)的角色,他是来自新斯科舍(加拿大省份)的一名退伍士兵,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他在战争中所见和所做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开始寻找他丢失的一切——体面、爱,和一个让自己有归属感的社群——但沃克只找到了一碰就碎的幻象、转瞬即逝的希望,还有孤独。他只有在踏上洛杉矶的街道时——这座城市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且市内的拆毁与重建工作几乎永无止境(“就像一场快进的战争”)——他才能有家的感觉:他能在这里找回自己。
我花了四年时间来查询相关资料和写作《长镜头》这本书。我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包括美国历史,以及诺曼底登陆战成功的原因(我特别关注了北新斯科舍高地战士的经历),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了电影上,通过影片来认识那个时代——我总共看了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的大概500部电影——我从中了解了当年的风格、人物说话的语气以及所使用的语言,我还知道了许多地理方面的细节。在我看来,我必须亲身领略当地的风景才能写出切实的文字,我可以到加拿大布雷顿角岛的因弗内斯县漫步,也可以去曼哈顿和旧金山的老街上溜达。但我在书里提到的位于洛杉矶的邦克山,却已不复存在。这个坐落在市中心之外的高地曾经是上流社会的居住区,后来,它被腐败的房地产开发商盯上,到了50年代末期,占地130英亩的社区住房遭拆迁,这座小山也被夷平,海拔下降了100英尺。自查理·卓别林的时代开始,邦克山除了作为8000名居民的家园以外,还一直被当作免费而露天的电影拍摄地,因为附近安妮女皇的房子破旧有年代感,颇有意趣,而且隆起的小山——再加上它的景观、台阶和隧道——为电影的取景带来了绝佳兴味。这片区域的当代地图基本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只能把这个洛杉矶丢失的心脏的地理状况,通过无数照片和数百部电影重新拼凑完整。我跟我书中的主角一样,都在寻找方法来修复这个世界,所以我看了电影,把这个世界缺失的部分画了下来。我给自己做了张地图。
黛西·约翰逊:
“我不认为写作可以借助魔力——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挖掘一个深埋于地底的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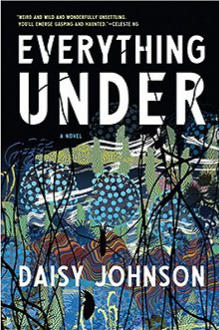
《地下世界》
我开始动笔写《地下世界》(Everything Under)的原因已很难追溯。为什么这个想法从其他众多的想法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在我的大脑中扎根生长、岿然不动呢。当时我正在创作一本小说集,也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书《沼泽》(Fen)。我渴望写一些篇幅更长的东西,给自己带来不同的挑战。我开始痴迷于“重述”这种手法。所谓重述就是毁灭原作,然后让新故事从它的废墟中诞生,我非常喜欢这种创作模式。神话故事一直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变形、美学和暴力元素令我心醉沉迷。我的朋友近期正通过女性主义的角度重述俄耳浦斯的故事——那个好弹奏七弦琴,后来去冥界营救亡妻的音乐家——但我知道,我想重述的故事比这黑暗得多。
我看中的神话故事里充满了暴力和恐怖元素,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一边不断受到惊吓,一边被拖拽到那个无可避免的命定结局。这个故事里有许多等待填满的空档,比如那些从未开过口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我也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它们都填上。我读了莎拉·霍尔(Sarah Hall)、凯莉·林克(Kelly Link)、克莱尔·瓦耶·沃特金斯(Claire Vaye Watkins)和卡伦·罗素(Karen Russell)的短篇小说作品,我欣赏他们大胆离奇的描写,书中的正常内容似乎都染上了怪异的因子。我对“神秘离奇”的元素进行了深入思考,思考“家”这个符号——一个看似舒适的地方——是如何变得危险和禁忌的。我喜欢那种毁灭即将来临,每个人心底的阴暗都开始滋长的末世小说。我找到了几本跟我的想法类似的书,并随身携带:埃维·怀尔德(Evie Wyld)的《所有的鸟儿,歌唱》(All the Birds, Singing)、彼得·赫格(Peter H?eg)的《斯米拉小姐的“雪之感”》(Miss Smilla's Feeling for Snow),以及海伦·奥耶耶美(Helen Oyeyemi)的《白色的是巫术》(White Is for Witching)。
我能感到故事的灵感在我的体内喷涌欲出。我一直认为,一部作品最初的创作阶段令人既忧虑又兴奋,因为所有的想法全都堆砌覆盖到了一块儿。
我曾经尝试过写小说,但并不成功。我感觉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收获,正在摸索着走上正确的道路。初稿不行,修改过的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的稿子还是不行,要么是背景设置有问题,要么是角色的表达方式不合适。我的小说索然无味。我写得很快,然后又删除了几乎全部内容。我感到绝望,但同时我也更好地了解了这本书的实质内容,我正在努力把故事从一团混乱中理出来。
在一个夏天,我和我的伴侣租借了一条运河平底船,在牛津的河流中畅游。河底的水生植物相互纠缠,十分茂密。我推开水闸,看着涌进去和溢出来的河水。我看见一头死羊露出的半个身体,脑中马上开始想象,也许这浑水底下潜伏的根茎和枝条实际上是拥有自主意识的生物。我已经花了好几年写作《地下世界》,故事的背景设定也已经大改过三四次,但一直感觉不到位。在船上的第一个夜晚,河底,也可能是水面的水生动物发出的噪声让我无法入眠,寒冷浸透了我们的整条船。回家后,我再次开始重写这本书,这次写的是同住船上的母女俩看见一个男孩顺河而行向她们走来的故事。
我不喜欢认为写作时可以借助魔力或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写作就是单纯的努力工作而已,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挖掘一个深埋在你周围的盒子。《地下世界》这本书讲述了记忆的脆弱之处、语言对我们本性的影响,以及我们在乡村荒郊的生存方式。这是一本关于家庭和女性之间友谊的书。这是一本与我同起同住、并肩作战将近四年的书。如今让它离开我的怀抱,并且接受它不再属于我的这个事实,真是让我感到既美好又害怕。
2018年布克奖已于10月16日公布结果,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凭借长篇小说《送奶工》获奖。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