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体》英文版出版之前,作者刘慈欣为英文读者写了一篇介绍《三体》和中国科幻小说的文章。
《三体》和中国科幻小说
——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一种,以及可能的地球中最好的一个
几年前,一部科幻小说在中国面世,它有一个奇怪的标题:《三体》。
这部小说一共有三卷,整部书的标题是《地球往事》,第一卷《三体》(注:英文版正式译名为《三体问题》)之后的两卷分别为《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国读者更习惯把整部作品称为《三体》。

刘慈欣《三体》中文版封面
科幻小说在中国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文类。评论界一直把这个类型当作是青少年文学的一个分支,对它没有多少兴趣。《三体》的主题——外星人侵入地球这个题材并不少见,但关于它的讨论却很少。
因此,当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并引发大量争论时,每个人都为之惊奇。人们在平面媒体和网络上对《三体》的讨论是空前的。
举几个例子。中国科幻小说的主要受众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但《三体》却得到了IT企业家的注意。在网络论坛上和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就书中的各种细节(比如对费米悖论的一种解释——“黑暗森林”理论,还有外星人对太阳系的降维攻击等)展开争辩和讨论,用它们来比拟中国互联网公司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接着,《三体》引起了长期被现实主义文学所统治的中国主流文学界的注意。《三体》就像是突然闯入人们视野的怪兽,令文学评论家们迷惑不已,但却又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这本书甚至对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也产生了影响。一位宇宙学家兼弦论物理学家李淼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体中的物理学》。许多航天工程师都迷上了《三体》,中国航天局甚至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虽然在我的书中中国航天局被塑造成保守、狭隘的形象,一位极端激进的军官甚至要借助暗杀多人的方式才使新的思想得到采用)。这些反应可能对于美国读者并不新鲜(比如《星际迷航中的物理学》,NASA科学家也经常与科幻作家合作),但在中国却是闻所未闻的。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压制科幻小说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网络上,有许多读者为《三体》创作歌曲,还有很多读者渴望有人把它拍成电影,有人甚至不厌其烦地用其它电影的片段剪接成《三体》的短片。新浪微博上有大量用户的ID来源于《三体》中的角色,他们用书中人物的口吻对时事进行评论,拓展了小说中的故事。基于这些虚拟ID,有人开玩笑说“ETO”已经准备就绪了(ETO,地球三体组织:小说中地球叛徒组成的三体侵略军第五纵队)。中国最大的电视台CCTV曾经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科幻小说的访谈,有一次在现场的上百名观众突然喊起了小说里面ETO的一句口号:“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两位电视主持人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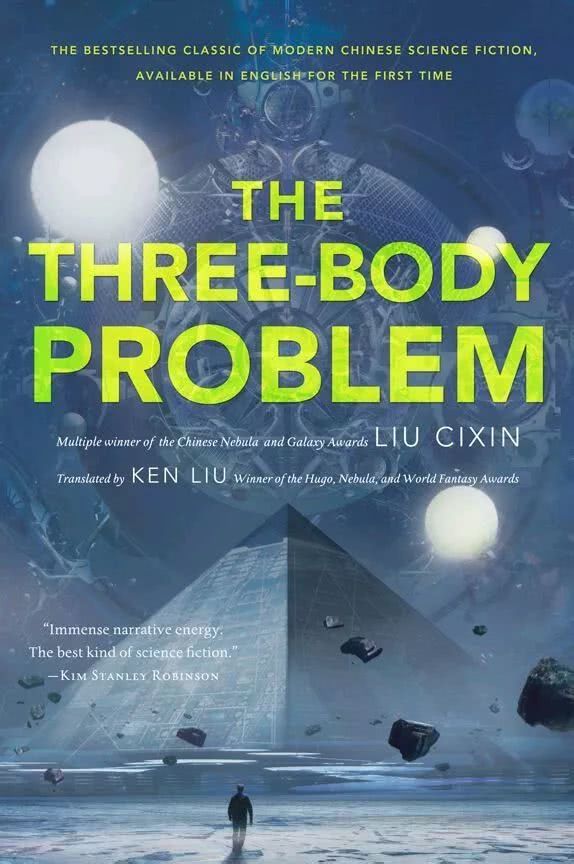
当然,这些事件也仅仅只是中国科幻小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新近发生的事。
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在那时已经摇摇欲坠。当时的中国学者接触了西方科学技术,对它抱有很大的好奇,并把它看作是把这个国家从贫穷、孱弱和全面落后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希望。当时出版了许多普及和思考科学的著作,包括一些科幻小说。失败的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写过一部名为《新中国未来记》的科幻小说,其中写到了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个图景直到2010年才成为了现实。
在中国,科幻小说像大多数文类一样服务于现实的目的。在它诞生之初,梦想中国有一天强大起来、摆脱殖民掠夺的中国人用它来宣传他们的理念。在清末民初的科幻作品所设想的未来中,中国往往是一个强大、富裕、先进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尊敬而不是被压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小说成为了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主要创作对象是儿童。大多以技术设想为核心,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人物简单,文学技巧简单甚至单纯。很少有故事在火星轨道之外展开,大多数都发生在离现在不远的时代。在这些作品中,科学技术总是正面力量,科技带来的未来总是一片光明。
考察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早些年,对政治和革命的热情渗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空气中似乎都洋溢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味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能会期待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读到各种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描写。但事实上却连一部这样的小说都找不到。实际上不存在以共产主义为主题的小说,没有一部小说为推广这一概念,勾勒过哪怕最粗略的图景。
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始初见成效,西方科幻对中国科幻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来。中国的科幻作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争论科幻小说到底应该是姓“文”还是姓“科”,最终以文学派的胜利告终。这场争论对中国科幻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中国迟来的胜利。科幻小说终于摆脱了作为单纯的科普工具的命运,开始能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一次复兴。新作者们和他们的新理念和上个世纪已经没有多少联系,随着中国科幻的多元化发展,它的特质中“中国化”的元素正在淡去。当代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小说越来越相似。比如在中国科幻作品中可以容易地找到与美国作家写过的风格和主题相类似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中国科幻作品中的科学乐观主义几乎完全消失了。当代科幻反映出的对技术的态度更多是怀疑和忧虑,这些作品展现的未来是昏暗而不确定的。即使光明的未来时有出现,也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大灾难。

《三体》葡萄牙语版和希腊语版封面
《三体》出版的时候,中国科幻小说市场焦虑而消沉。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长期空白造成了读者群体的小众化。科幻小说爱好者们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孤岛上的野人一样受外人误解。为了吸引圈外的读者,作者们感到自己必须放弃原教旨主义的“科幻核心论”,转为强调这个文类的文学性和现实性。
《三体》的一、二卷中体现了一些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第一卷有很大篇幅发生在文革时代,第二卷中的中国未来仍然处于与现在相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三卷出版前夕我的出版商和我本人都没有对它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把第三卷放在现实背景下,我的笔触必须伸展到遥远的未来和太空中遥远的角落。按常理推断,中国读者是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我的出版商和我的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第三卷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也许最好放弃吸引非科幻迷读者的努力。于是,我写了一部“纯”科幻小说,这部小说我写得甚是畅怀,因为我自认为是个硬科幻爱好者。这样,我为我自己写了第三卷,写的尽是多维宇宙、二维宇宙、人造黑洞、小型宇宙之类的东西,还把时间线拓展到了宇宙热寂的时刻。
然而,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正是完全为科幻爱好者创作的第三卷,使得整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体》的经验使得科幻作者和评论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科幻和中国。他们意识到他们忽略了中国读者思维方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新一代的读者不再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把视野局限在狭小的现在,而是转向了未来和更宽广的宇宙。中国的现状有点像美国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未来,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科幻小说发展与繁荣的肥沃土壤。
科幻小说是关于可能性的文学。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也是无数个可能性中的一种。对于人类,一些宇宙比另一些更好。而《三体》展现的是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一种,是所能想象的最黑暗、最残酷的宇宙图景。
不久以前,加拿大作家罗伯特?索耶访问中国,当他讨论三体时,他把我选择这一可能世界中最坏世界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的特质。作为加拿大人,他声明自己对人类和地外文明的关系持乐观观点。
我不认同这一分析。在上世纪的中国科幻作品中,宇宙是友好的,大多数地外文明以朋友或导师的形象出现,它们拥有上帝般的耐心和宽容,为我们,一群迷失的羊群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例如,在金涛的《月光岛》中,外星人安抚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在童恩正的《遥远的爱》中,人类与外星人的爱情生动而庄严。在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中,与性情温和、道德高尚的外星人相比,人类是如此的堕落,以致于外星人被吓得逃离了地球,尽管他们拥有先进得太多的科技。
但反观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宇宙中不像现代的加拿大,倒更像500年前欧洲移民到来之前的加拿大土著人。当时,由不同民族组成并代表至少10个语族的上百个部落,共同居住在从纽芬兰省到温哥华岛的加拿大。对他们来说,与作为高级文明的西方人的接触,更接近于《三体》中所描绘的那样。由加拿大土著人作家乔治斯伊拉兹马斯和乔桑德斯所著的书《加拿大的历史:一位土著人的观点》,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叙述。
我在《三体》中描写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一种,是希望我们能努力使地球成为所有可能的地球中最好的那一个。
(*英文原载TOR.COM,原标题:TheWorst of All Possible Universes and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Earths: Three Bodyan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译者:清水白石)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