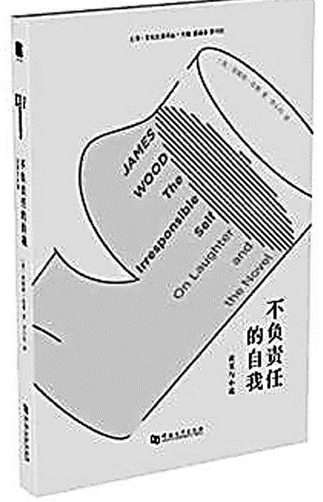
《不负责任的自我》 作者:(美)詹姆斯·伍德 译者:张新木 上河卓远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在《不负责任的自我》一书中,詹姆斯·伍德收入了发表在几个重要报纸杂志的评论,他以“论笑与小说”作为此书的副标题,极其敏锐地看到了小说和喜剧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小说是悲喜剧,笑中带泪,或泪中带笑。
尽管有些著作,在一般眼光看来,似乎无法和喜剧联系起来,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和柯勒律治的作品;而有些向来被视为喜剧的作品,如拉伯雷的小说,却被詹姆斯·伍德认为“喧闹而非好笑,催眠而非动人”。如此一来,令人纳闷的是,他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选取评论的对象?
詹姆斯·伍德认为,小说的兴起,使喜剧为之一变。小说兴起前,喜剧的美学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准,即对丑陋或缺陷的无情嘲笑,宗教中的喜剧性场面往往与此相关;小说问世后,戏谑之余,却包含着对可笑者的同情宽恕。在他看来,小说正是属于“宽恕的喜剧”。叙事者在笑中含泪地讲述着人物的遭遇,而非冷眼旁观横眉冷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固然因匪夷所思的疯狂行径时常令人喷饭,但他对幻想的执念至死方休,最后徒劳无功,却也令人不禁洒下泪来。相比之下,拉伯雷的《巨人传》并不是詹姆斯·伍德所谓的“宽恕的喜剧”之典型,因为它通篇充斥着对教士和权贵的嬉笑怒骂,而同情的维度却付之阙如。据此,詹姆斯·伍德暗示《巨人传》仍属于旧的喜剧美学类型里。
詹姆斯·伍德在书中多处强调,“不负责任的喜剧”是宽恕的喜剧的后裔变种,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神奇创造”。他已经把个人喜好充分披露出来,在《不负责任的自我》的篇幅布局中也可以窥见端倪。和布鲁姆一样,伍德也充分肯定莎士比亚的包罗万象,为西方文学的重要标杆,可用以衡量古今文学,他把“不负责任的喜剧”的源头追溯到莎剧。因此,除了开头涉及莎剧和堂吉诃德外,中间部分评介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谢德林、巴别尔、维尔加等,几乎全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用这样的敏感和细致,注意他不合逻辑的人物和他们不合逻辑的推论,会产生一个很有活力的悲喜剧世界。”詹姆斯·伍德在评论维尔加时写道。这句话同时也适用于他所推崇的其他几位作家,他们的作品同属“不负责任的喜剧”。作为“不负责任的喜剧”的小说,故事里的人物往往包含着“不负责任的自我”,他们总是有些荒诞的行径和言论,却总是一本正经地相信自己可以为这一切负责,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就是这种一本正经的执着劲儿,令人由衷地发笑。
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是一部悲喜剧。主人公波尔菲里冷酷无情、平庸吝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伪善。他唯一的真诚就是彻底的伪善,这种伪善在他身上根本无需伪装,他只相信自己的善良是真实的,而不知道他其实早已丧失了自我,他以彻底的唯我论丧失了自我。这样的伪善者颠覆了以往的伪君子形象,以往的伪君子是自知其伪善和恶毒,他们明知自欺欺人并百般掩饰。令人恐怖的是,波尔菲里丝毫未察觉其自欺欺人之处。波尔菲里让人厌恶,却也让人捉摸不透,他使人发笑,也令人哀伤。主人公就像一个失去头颅的人,却毫不知情地横冲直撞,旁观者会一边笑其鲁莽,同时又同情他的可悲命运。
詹姆斯·伍德推崇作家的“细致和敏感”,唯有如此,作家笔下的世界才是富有活力的。正因如此,他对大家一贯叫好的巴别尔颇有微词。在他眼里,惜墨如金的巴别尔过于敏感,却不够细致,以至于人物形象有时极度夸张,反而干枯。伍德“希望他少一些戒备……多一些慷慨,用他复杂的斑点多抹几笔他的人物”。
在一个批评沦落的时代,詹姆斯·伍德因其勇气、学识与才华,无愧于他的批评家身份。他时而给经典名著来一番“鸡蛋里挑骨头”,有时又给被遗忘蒙尘的杰作拭去厚厚的尘灰,他更敢于对炙手可热备受好评的当代作家浇个“透心凉”。最初,我们会震惊于他颠覆性的评判,但跟随他雅致的文笔迤逦而行,见识他对细节恳切的剖析后,我们不得不掩卷深思,重新反思自己昔日根深蒂固的看法。
我们将于《不负责任的自我》一书中见识詹姆斯·伍德的批判的锋芒,他严厉却不失风度。在今天出版界腰封横行的时代,詹姆斯·伍德让我们擦亮眼睛。詹姆斯·伍德的严厉和锐利特别地体现在他对扎迪·史密斯、汤姆·沃尔夫、乔纳森·弗兰岑与拉什迪的批评。前面三位风头正健,创造力也极其旺盛,夺得许多重要文学奖;而拉什迪已经进入文学殿堂,被众多名家视为天才和大师。纵然如此,却依旧逃脱不了詹姆斯·伍德的痛斥和嘲讽。
詹姆斯·伍德直言“汤姆·沃尔夫的小说是简单的标语牌”,他的人物只是巨大醒目的标签,肤浅却没有内容,而显得不像真实存在的人;热衷于创作“社会小说”的弗兰岑,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社会资讯和评论,处处表明他的社会关切,但在伍德看来,他炒的“这些冷饭似乎有点馊了”。扎迪·史密斯和拉什迪则被伍德看成“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写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物、戏谑的桥段,及连篇累牍的废话,人物的塑造却经不起推敲。伍德把拉什迪的写作贬为“漫画式写作”,认为他根本不精通现实主义的写作,他不过是“多年来一直被幸运地吹捧为魔幻现实主义”。显然,伍德认为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物,空有辞藻和篇幅,才是对文学真正的不负责任。这样致命的批评,到底有无道理?
留给我们的疑问是,詹姆斯·伍德是否因自身沉溺于写实主义的趣味,变得保守,而无法认同后现代看似支离破碎缺乏节制的写作?但说到底,他敢于为趣味而战。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