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 世纪的德国,康拉德把“宇宙如书”改造为世俗的观念。1350 年,此人把托马斯的百科全书《物性论》译成德文,并取名《自然之书》。库萨的尼古拉袭用了中世纪哲学的隐喻学。他指出,有些圣徒把宇宙看作有文字的书。不过,对他而言,宇宙是“内在词语的外现”。因此,感觉的事物可以视为“书”,作为导师的上帝就通过它们向我们宣示真理。在争论中,信徒证明自己比学者高明,因为他掌握的知识并非得自学校,而是上帝“用自己手指写就的”“上帝之书”。它们“随处可见”,故“也在这片市场里”。人的心灵也被称为书籍:“的确,心灵就像智慧之书,其中展现了作者的每一个意图。”

1481年《自然之书》中的版画
归根结底,我们发现,宇宙或自然如书的观念起源于布道词,后为中世纪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所吸收,最后才进入日常用法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宇宙之书”常常经过世俗化改造,也就是使之远离本身的神学起源,然而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我再举几个例子。
在瑞士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看来,书籍隐喻有个基本作用。他把成文的书“上帝自己公布、书写、宣示、创作”的书两相对照。医生的书肯定是病人。自然似乎也被设想为涵盖一切、完美无瑕的书籍汇编,“因为它们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捆扎起来,然后从他的图书馆里挂出来”。“自然之光使启蒙成为可能,使自然之书得以理解;没有自然,哲学家也好,自然科学家也好都得不到启蒙。”苍穹是“另一本医书”,其中彰显着“苍穹的意义”。最后,整个地球也是一本书或一座图书馆,“我们用双足翻动它的书页”,当然,使用时必须得“虔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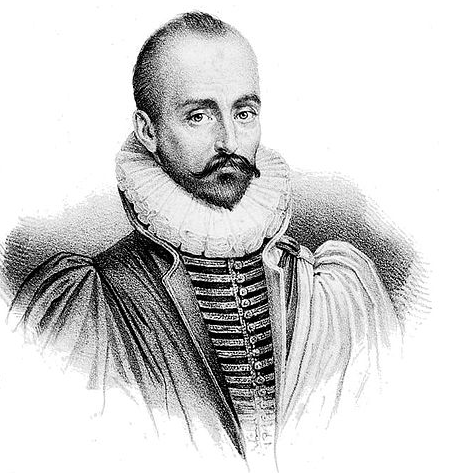
蒙田
这些书籍隐喻为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所吸收。蒙田提出,宇宙之书是可识辨的历史与生命真谛的缩影:
大千世界……像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好好照照,以便认识自己。总之,我希望它是我学生的教材。

笛卡尔
更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的一段话:
一旦我的年龄够大,不必再受家庭教师的管束,我就要彻底抛开书本;我决心,只专注那些能在自己内心或宇宙这本大书中找到答案的学问,用青春的余晖去游历,去拜访各国朝廷和军队……
培根保留了书籍隐喻的神学概念:“我们的救世主说道:‘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此,我们面前摆着两本书,如果想避免误入歧途,就要好好研究研究。”康帕内拉知道“两本书”——《圣经》的文书与自然的活书。书籍隐喻也成为他反对经院哲学的利器。

欧文
着名讽刺诗人欧文反其道而行之,把“宇宙之书”的主题改造成另一种简练的形式。他称自己的书是宇宙:
这本书是宇宙;哈斯金,人类是其中的诗句:
在那里,你也能像在世间一样,找到几个好的。
自然之书篇幅宏大。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昆虫部分。在《箴言》中写道:“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另一处还写道:“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上帝的智慧尤见于最渺小的创造物(当然,《约伯书》通过两种猛兽——河马与鳄鱼,表达了相反的思想)。英国哲学家布朗将《圣经》中的上述思想,融入其《医生的宗教》:
诚然,有哪种理性不是得自蜜蜂、蚂蚁、蜘蛛的智慧?是哪位智者教它们做理性都无法教我们做的事情?粗鲁者惊异于自然界的庞然大物——鲸鱼、大象、骆驼;这些,我承认,是自然界的巨人,是她的宏伟之作。不过,在那些细小的发动机中,蕴藏着更奇妙的数学原理;身为自然界渺小的居民,它们的礼数更明确地彰显其创造者的智慧......我永远也不满足仅观察司空见惯的奇景,譬如海水的涨落、尼罗河的泛滥,譬如铁针向北偏转;我还设法寻找并再现那些更明显却受忽视的自然物,这样的研究即便没有跋山涉水,我也能在自己的宇宙学中完成。我们随身背负着自己并未用心寻觅的奇迹:我们身上蕴藏着整块非洲大陆及其妙物;我们是勇往直前、喜欢冒险的物种;同样的知识,会学习的人提纲挈领得真知,不会学习的人皓首穷经难觅闻。
因此,有这样两本书让我一点点收集我的神性;一本是落成文字的上帝之书,另一本是他的仆从——自然——的书;后一本是普遍的公开的手稿,所有人触目可及:在此书从未见过上帝的,可以在彼书发现他的身影……当然,异教徒比我们基督徒,更清楚如何解读这些神秘的文字;相比之下,我们不但不关心这些普通的象形文字,而且不屑从自然的花朵中吮吸神性。
布朗爵士的同辈人夸尔斯在其虔诚之作《寓意画集》里写道:
宇宙是一本对开的书,
上帝杰作均用大写字母印刷:
每个创造物都是书页,每种效果
都是漂亮的文字,完美无瑕。
1667年出版的弥尔顿《失乐园》
这个隐喻亦见于多恩、弥尔顿、沃恩、赫伯特、克拉肖的作品。由此,它成为诗歌的普遍特征。精确自然科学的创立者,赋予了书籍隐喻一种重要的新含义。伽利略谈及宏大的宇宙之书时指出,古往今来它一直摆在我们眼前,但若我们不熟悉其中的字迹,就无法阅读。“它是用数学语言书写的,里面的文字是三角、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自然之书已难读?——显然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当中渗透着最卑微者的意识。借助光学仪器,人类可以用新的眼光审视动植物王国。斯瓦默丹通过显微镜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1737年,布尔哈弗结集出版了这些研究成果,并为其取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书名——《自然之书》激发布朗爵士的《箴言》段落(见上文),也深深铭记于他的脑海。另一方面,狄德罗重新启用了蒙田的用法。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对于那些伟大的知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获得的。它们并非得自马克–米歇尔·雷或其他地方印刷的书籍,而是得自宇宙之书。这本书我们阅读时,一刻不停,漫无目的,三心二意,从不置疑。我们从中读到的内容大多无法书写,因为它们太精致,太巧妙,太复杂;不论如何,它们赋予人类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敏锐性格......哦!如果我们只知书本,不闻其他,就会变得愚蠢而平庸。同生活的需要与状况相比,那些只是高深作品中,各种原理写下的可怜的东西。听听这亵渎神明的话:相比那些传授诡计、心计、政治手腕、高深道理的着作,拉·布吕耶尔和拉·罗拉什富科实在是极粗俗极平庸的书。
化身东方圣贤的伏尔泰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对哲学家而言,阅读上帝摆在我们眼前的巨着,没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了......”。卢梭借爱德华勋爵之手写道:“您还将收到一些书,可以丰富您的馆藏;不过,这些书里哪有什么新鲜货?哦,沃尔玛!您若想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只要学会阅读自然之书即可。”这时,卢梭用他那改变世界的言辞,赋予了这句老生常谈(该意象已然如此)新的面貌。
第一版的《新爱洛漪丝》
在卢梭的时代,“自然之书冠群书”这句朗朗上口的格言也进入了诗歌理论。让赫尔德和歌德大受启发的英国前浪漫主义者,发起了这场至关重要的变革。1759 年,英国诗人爱德华·杨发表了《原创计划》;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莎士比亚并非满腹经纶的学者,他掌握了“自然之书与人类之书”。伍德将荷马阐释为原创的天才。1773 年,伍德着作的德译本在法兰克福问世,并给少年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伍德的书中,我们看到,荷马仅研究伟大的自然之书。因此,英国前浪漫主义的诗学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诗学,均采用同样的书籍隐喻,其影响遍及思想史的多个关键时期。歌德的《书简》中也出现了“自然之书”:
瞧,自然是一本鲜活的书,
人们可知其含义,尽管常常误读;
在你心中有个愿望,真诚而强烈:
愿一切快乐可以永存世界,
愿阳光永照,愿大树永矗,
愿梦境永留,愿海滩永驻,
在你的心里把它们一一搜集......
“自然诗”的概念经狂飙突进诗学,进入大格林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
我们可以把自然诗称作单纯活动的生命本身,一本鲜活的书,上面写满了历史;人们可以从其中任意一页开始阅读和理解,然而却从未读完或理解完。艺术诗是生命的杰作,一开始它就是哲学的。
在格林的笔下,《圣经》的“生命之书”,亦即维克多派神秘主义的“鲜活之书”,摆脱了宗教色彩,并与英国前浪漫主义诗学理论合而为一。在这一摇摇晃晃的基础上,产生了19 世纪日耳曼文学专家所欣赏的中世纪诗歌概念。德国的中世纪研究,在浪漫主义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但此后它只吸收了情感中的热情要素,并没有后来构成德国浪漫主义崇高而持久价值的历史知性的升华与意识的觉醒。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施莱尔马赫以及穆勒,尽管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在新精神(因而也是在历史新概念)的指引下走到了一起。而格林兄弟、乌兰兄弟都没有参与其中。诺瓦利斯的话让我们从了无新意的书籍隐喻(在大格林的笔下,这演变为对书的贬低),走到了更高的境界。他说:“书籍是历史实体的近代类型,但也是至关重要的类型。它们很可能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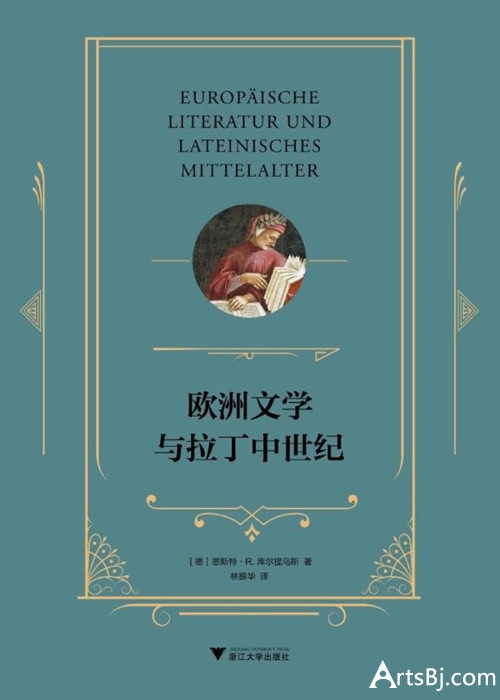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德] 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着,林振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2月),文中外文注释已省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