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以“小说阅读”为主题的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作家、评论家采取互评的方式,从具体作品出发,审视彼此的创作对于社会历史的折射,就创作理念和技巧展开交流。在此,小编为大家节选了四位大陆作家对于台湾“70后”作家的评述,与读者分享。
高翊峰:“模糊世代”的文本试验
刘大先 | 文
如同陈芳明所说,高翊峰小说的出现,是一个新的“模糊世代”的展开。“台湾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威权体制的式微,动员戡乱的总结,从前的许多批判典型逐渐远逝。整个文学生态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思想上、心灵上的禁忌也慢慢遭到剔除。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各种艺术疆界都受到突破。” 在一个类似于“没有任何凭借的开放社会”中,高翊峰之前的文学遗产包括向外的乡土文学和内倾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已经渐次失效,或者至少被认为已经失效。高翊峰所面对的是后现代的语境,尤其在台湾那样一个后殖民岛屿之上,其经验更加驳杂,他需要另起炉灶。但是,陈芳明也无法给予他的写作一个命名,因为这是一种尚在进行中的文学试验,有着魔幻式的语言创新外观,但终究没有确立一种明确的美学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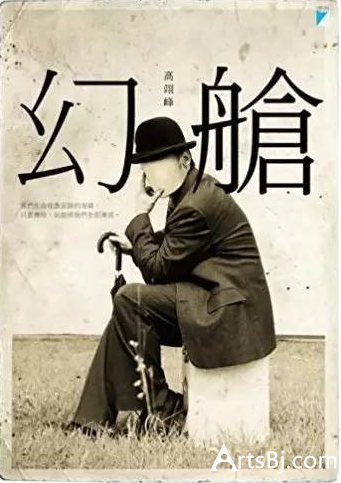
高翊峰《幻舱》
有意味的是,高翊峰在谈起自己的写作,同样也用了“模糊”这样的概括:“我不断问,那个藏在文字里的自己,到底想要捕捉什么?一度,我深深相信,每当那个我想捕捉的事物愈清楚,不安与恐惧就愈庞大。所以,我只能把(欲捕捉的)范围缩小,再缩小,再再缩小一点,或许,就有可能发现一些早先一直蒙蔽我的晃动物体。” 在写作的探索过程中,他找到的途径是聚焦于“一个点”,然后将那个“点”推到极致——无论它是某个肉体的感觉、瞬间的情绪,还是突然的感触、游离又变幻的念头。这使他的大多数作品如同一个长镜头的特写,以细致、绵密、缓慢又略带冷涩的语言呈现一个淡化情节而突出细节尤其是细节感受的“点”。物理世界极其狭小,感官世界又无限放大。这种经验与感受显然是从外部世界的退缩,但也并非进入到心理幽深的层面,而是集中于生理表层,他似乎不经意间接续了“新感觉派”的一些技法和理念,但可能走得更远。
高翊峰身处的“模糊世代”无疑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貌似背反却又同谋的大时代背景,在这种矛盾交错中,可能惟有极端化地处理才有可能显示出这个时代身处岛屿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精神特质,这让他又有别于现代主义脉络中的新感觉派。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高翊峰的写作风格诡异,无论题材与语言,还是叙述速度与情节空间,都有一种准邪典(cult)气质。他的文本很难构成顺畅舒爽的阅读体验,而往往在人为放大的细节、细致入微的感受、浓墨重彩的环境描写、有意延宕的进展节奏中让读者感到痛苦、沮丧和煎熬。这不由得让我将它与亚洲极端电影(Asia Extreme)联系到一起,事实上他的文字描摹和结构中也不自觉地显现出影像叙事的潜在影响,比如闪回、淡出淡入、特写、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方式。

高翊峰《乌鸦烧》
回到现实中来,如果将高翊峰的写作置于艺术史发展的脉络、当下地缘政治场景与新媒体技术现实的之中,就会发现也存在着限度。首先,现代主义式的内倾,一旦走向极端,它的公众接受度岌岌可危。事实上,原本就身处碎片化的语境之中,可能主观意图反抗,反倒客观加深了压抑机制本身。其次,异见式的叛逆如果沉溺在心理与想象之中,不免会延续20世纪中叶以来左翼知识分子的失败宿命。最后,新媒体与消费造成的景观社会和符号场景使得“真实”已经变成“超真实”,这个时候进一步往超现实主义的方向走,也许只是落入了一种无形中的窠臼,而“超真实”的现状在高翊峰的作品中是搁置的。新感觉派、超现实主义这些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在“晚期现代性”和“流动的时代”中如何找到焕发生机的可能,“极端写作”怎样突破模式,进而连接文学的介入式行动功能,这也许是高翊峰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高翊峰的文体,是敦促进一步思索与奋斗的开始。
禁忌,无禁忌
——今日语境下阅读陈雪小说
李蔚超 | 文
20世纪90年代,台湾岛上那些艳帜张举的同性恋小说合力上演了“世纪末的颓废与华丽”。与“张派传人”朱天文的警心寓言《荒人手记》,李昂《禁色之爱》的酷烈乖张,以及篡夺“男”性情欲主动之位的邱妙津相比,陈雪的一系列女同性恋小说显得哀婉羞矜,怯然如良人淑女——真有几分“文如其人”,陈雪其人谦和柔婉,好似一位随时要向人鞠躬问好的日本妇人。面对僭越太一上帝和人间伦常的情感和身体欲望,陈雪困惘而怯畏,她惊惶诈乱,欲拒还迎,她仿佛就是从她的小说中出走的人物:“面对阿猫炽热的情爱和模糊的性别,我简直束手无措,我甚至无法处理自己对她萌生的热情和性欲,只觉得好羞耻……”于是,同创造并提醒我们“阁楼上的疯女人”存在的前辈女作家们相似,写作之于陈雪,更是一种分散主体性的自我周旋,一种与习得父权文化内化于心的自我反思和教化的抗衡,一如陈雪一再迷惘地借人物之口独白,“企图透过写作来挖掘潜藏的自我”。如今,当世界范围内性别平权议题被广泛讨论并接纳时,我们应该怎样审视曾经因撰写边缘经验、禁忌之恋、挑战伦理而被视为先锋艺术的同性恋小说?反身回望几十年间台湾的同性恋书写,论者不禁慨叹“从充斥着罪恶感的自责自鄙,到坦然地自得自炫,其间的沧海桑田之变,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 “触目而惊心”的说辞不小心暴露了论者自身的心理不适和审美震惊,论者的情感结构暂且不表,然而,我们的确面临着这样的难局,震惊消退之后,我们无须侧目或窃语之后,我们要如何安放曾经“出走的夏娃”?小说是否存放着奇观之外的审美经验有待我们发现?于是,今天重读以擅撰禁忌之恋主题的陈雪,便有了新的诉求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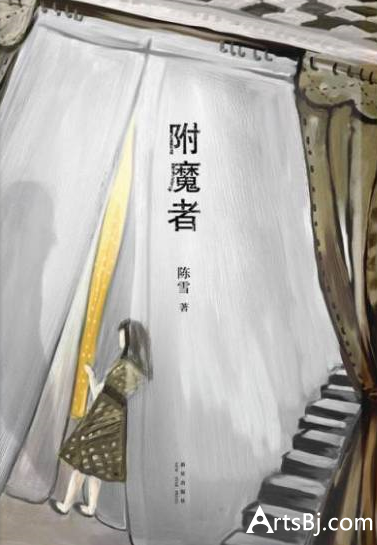
陈雪《附魔者》
在陈雪早期的小说中,故事往往开始于一个女性的安稳静好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另一个诱惑的女性的出现,看似安稳圆满的生活裂缝、破碎和重铸。在惯用第一人称女性叙说模式的小说中,我们阅读陈雪如同窥视她的隐私或阴私。
由此说来,我读《附魔者》——这部被骆以军视为陈雪走向圆熟的重要之作,反而读出寻常的(或曰不寻常的)“老实”与“本分”。这是少女与两位年差十余载的叔叔之间情天恨海爱恋纠葛的故事,是不伦而“罪恶”的爱情,可是今天我们对于不伦之恋——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有着十足丰盛的经验。
在陈雪早期成名之作《蝴蝶的记号》中,小说结尾处不无深意地让原本愤而出走的丈夫回归,并理所当然将主人公小蝶与她的同性恋人驱赶出家门,小蝶与恋人站在“伊甸园”门外徘徊而犹豫,叛离伊甸园放弃妻子的“合法”位置,也就意味着放弃作为母亲和女儿的权利,遑论为人师长的社会权利。30岁的陈雪对此无法回应,她只能质询和自我麻痹,只好沉醉于“梦”中——“我只想好好地睡一觉”,小蝶说。

陈雪《迷宫中的恋人》
1995年,陈雪出版了《恶女书》,台湾学者杨照在《何恶之有》一文中不无遗憾地说:“在陈雪笔下,每一段女同性恋情欲都是充满罪恶感的。这种罪恶感其实诉诸的是背后未明说的社会制约”。时过20余年,陈雪在《迷宫中的恋人》中借着“病”谈论“爱”,却也依然未见杨照孜孜以盼的书写女性同性情欲时“理直气壮存在的合法性”,与之相反,主人公一再宣称自己已经失去了与伴侣之间的情欲冲动,“悔愧”仍是小说《迷宫中的恋人》核心关注的命题.
说到底,陈雪的小说也不过是关于“爱”诸多形式之一种而已。《人妻日记》之书写情欲流入日常,还原其爱的本质,《迷宫中的恋人》剥离“疾病的隐喻”,赎还女性真我。陈雪可能摆不出决裂的革命姿态,她哀婉柔弱,怯然如良人淑女。然而正是她小说中柔弱平易的力量,让决绝叛离父权藩篱的瞬间拥有了一种可能——过渡到天长地久的永恒。
自然、肉身与现代文明的处境
——甘耀明小说读札
梁鸿 | 文
甘耀明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一位老人、一个男孩、一片森林,有着独特灵性的和感知的男孩,他和另一个世界形成对接,使得现实世界有了相对应的存在,扩张了现实世界。《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中那个喜欢兰花、保护兰花的男孩,他喜欢那生机勃勃、有着自己生活和美的森林,在那里,植物和动物是纯粹的,为了兰花,它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森林是活生生的,万物充满灵性,有着绚丽而惊人的美。而人类的贪婪破坏着美和灵性。小说里,动物和人之间那场惨烈的大战展示了人类的残暴和无知,它让我们感受到疼痛,感受到美的毁灭和人性的毁灭。《葬礼上的故事》中的阿婆,携带着家族的历史,面对天空和大地,不断地叙说。阿婆就像是地母的化身,能够与大地沟通,和白云交谈。整部书就像讲故事,幽默,带着生活的韧性和对苦难的化解,这也恰恰体现出生命内部的张力。《邦查女孩》中的帕吉鲁,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患不语症的男孩英俊善良、充满力量,但却沉默不语,他不知道怎么发声,也很难理解熙熙攘攘的社会,但是当他回到森林中时,他却灵活自如,犹如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绳索,充满自由之感,这里有他的灵魂、情感和生命,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古阿霞,这样一个追寻爱情的女孩子才产生了真正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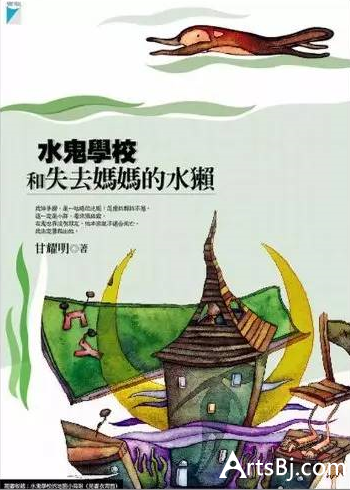
甘耀明《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
小说里的森林充满原始的力,神秘广大,黑暗涌动,它和帕吉鲁、伐木工,和那个山顶孤独的村庄之间并非是索取和被索取的关系,而是完全同在的关系。它们互为存在、互相珍惜、互相感知。在这里,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独立的存在,拥有自己的性格和需求。
与此同时,甘耀明并没有把森林、自然独立于现代社会之外,而是把它作为其中一部分来书写。在这一村庄里,古阿霞在为建立学校而争取资源,们们面临着种种矛盾和痛苦,面临着生存压力,他们希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等等。
耀明使我们再次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体系下,人越来越被孤独于自然情境之外,既聪慧傲慢,又渺小可怜,我们拥有了种种超越性的科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力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孤独感和异己感也越来越强。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人类的肉身包含着地理、气候、植物和土壤,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所感受的愉悦并非只是它们美,而是它们也呈现了我们的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我们的样态之一。我们都是从其中被孕育出来的,万物平等,万物互相包含,我们有天然的共通的地方。只不过,随着人类的发展,这一共通的地方被我们自己隔绝掉了,我们找不到彼此之间互相感知的频率,我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哲学认知。我们在知识层面去理解自然,接触、认知自然,但却很少从情感层面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给我们打开这一通道,让我们重新看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梦境即历史,或文明的虚妄
——伊格言小说论
徐刚 | 文
在伊格言这里,梦境当然首先意味着一种绝妙的技术媒介,一种引入新颖科幻奇观的文本契机。如人所知的,围绕梦境大做文章,发挥奇思妙想,让人大开眼界,这是《盗梦空间》《阿凡达》一类好莱坞电影给予我们的启示。《噬梦人》当然也并不避讳这种浅显的娱乐性,并也力图在这种娱乐之中顺势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比如在VR、AR大行其道的今天,“梦境娱乐”作为“虚拟现实”的最新产品,对于AV产业形成的致命冲击,就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在这新的时代,技术理性与消费文化有了完美结合的契机,这也是资本向人类梦境“殖民”的“伟大历程”。小说还饶有意味地写到一种“梵之梦境”的药物,“人们在这些蜂巢状的胶囊小室之中,可以安心沉睡、心无旁骛地享用这些色泽鲜艳的、迷人的‘梵’之梦境……”由于科技的昌明,再加之“梦即一切,梦即万有”的“神圣”理念,未来某一天,“以梦境作为形式的‘神的体验’”或许真的会被当做娱乐的极致而广为贩卖,这种“精神鸦片”注定让所有的人欲罢不能。在此,“梵”犹如“忘忧之国”一般,成为“娱乐至死”时代的最大隐喻。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伊格言来说,梦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与记忆及历史之间的隐喻关系。或者可以说,在他那里,历史即梦境,认同即面具。这就不得不谈到《噬梦人》里的K了。这个周旋于人类联邦政府与生化人解放组织之间的双面间谍,“始终未曾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份”。他原本以为,只是“决定成为谁”的问题,没有“原来是谁”的问题,只是促使那决定浮现的“意志”的问题,没有“本质上”归属于何种族类的问题,只有“意志身份”,没有“本质身份”。小说之中,记忆与身份的问题永远纠缠着K,让他如卡夫卡《城堡》里的K一样彷徨于无地。这位人类与生化人解放组织殊死搏斗的棋子,一个不折不扣的试验品,无处逃遁的“第三种人”,有着“伪造的身世”,一个“赝品般的人生”,以及不切实际的梦想——“成为一个人类”,这都意味着他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快乐的”,那里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古典时代的自然风光,以及恋人那“涟漪一般清浅的笑”。而生化人一出场即是成人,他们没有童年,童年的被剥夺是一切乡愁的缘由。而在《零地点》中,玲芳对于文明的绝望,更是使她宁可退回到人类的原始时期,“我宁可在这里,自己种蔬菜种番薯,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交换他们自己做的生活用品……我要照顾他们,让他们在这里用最清简最单纯的方式养活自己。”那才是“他们应有的文明”,“对他们而言正确的文明”。

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那是个“社福法规和医疗法规都不健全的时代。”然而正如林群浩对小蓉所反驳的,“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了”。这种对话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小说中肆意弥漫的反现代的浪漫情愫,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4月21日6、7版,有删节。
(编辑:王怡婷)








